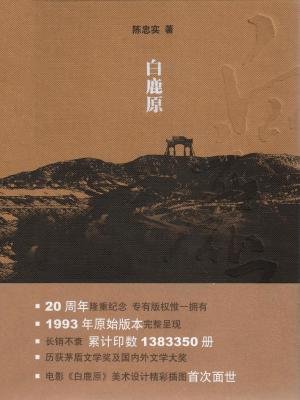白孝文終於從大姑父朱先生口裡得到了父親的允諾,准備認下他這個兒子,寬容他回原上。
白孝文開始進入人生的佳境,正春風得意。保安大隊升格為保安團,原先所屬的兩個支隊遞升為一營和二營,團丁正在擴編中。孝文被直接擢升為一營營長,負責縣城城牆圈內的安全防務,成為滋水縣府的御林軍指揮。他告別了那個書手的桌案,開始活躍在縣城裡的各個角落,操練團丁,檢查防務,處理各種事務;他的威嚴的臉眼被縣城的市民所注目,他的名字很快在本縣大街小巷市井宅第被傳說;被人注目和被人傳說本身就是一種榮耀,顯示出這個有一雙嚴厲眼睛的人開始影響滋水的社會政治和生活秩序……
白孝文很精心地設計和准備回原上的歷史性行程,全部目的只集中到一點,以一個營長的輝煌徹底掃蕩白鹿村村巷土壕和破窯裡殘存著的有關他的不光彩記憶。正當他一切准備就緒即將成行的最後日子,縣裡發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土匪頭子黑娃被保安團擒獲,這是他上任營長後的第一場大捷,擒獲者白孝文和被活捉者黑娃的名字在整個滋水縣城鄉一起沸沸揚揚地被傳播著……回原上的時日當然推遲了。
營救黑娃和嚴懲黑娃的各種活動都循著各自的渠道隱蔽而緊張地進行,只有白嘉軒的行為屬於公開。白嘉軒正在准備接待大兒子孝文的回歸,突然收到孝文派人送來的一封家書,略述捕獲匪首、公務緊迫、只好推遲回原的日期。白嘉軒送走送信的團丁,轉回身來就把褡褳掛到肩上准備出門。孝武走進門來問:“你背褡褳到哪達去?”白嘉軒說:“縣上。”說著就把那封信交給孝武。孝武看完後舒一口氣:“這下可除了個大害!”轉過臉猜測著問:“你去縣上做啥?”白嘉軒說:“探監。看看黑娃,給送點吃食。再問問你哥,把黑娃放了行不行?”白孝武驚訝得轉不過彎兒,愣愣呆呆地問:“你說你去探監?給黑娃還送吃的?你想托人情釋放那個土匪?”白嘉軒平穩地說:“就是的。”白孝武憋紅了臉:“你的腰杆給他打斷了你忘了?你忘了我還沒忘!”白嘉軒說:“我沒忘。”白孝武說:“那你還看他救他?”白嘉軒說:“孔明七擒七縱孟獲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這回就能學好。瞎人就是在這個當口學好的。”白孝武說:“你救黑娃讓原上人拿尻子笑你!”白嘉軒堅定不移地說:“誰笑我是誰水淺!”
白嘉軒趕天黑先來到白鹿書院。朱先生以少有的激情贊揚他搭救黑娃的行動:“以德報怨哦嘉軒兄弟!你救下救不下黑娃且不論,單是你有這心腸這肚量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樣寬廣深厚永存不死!”說到具體事,白嘉軒讓姐夫朱先生設法把孝文叫到這裡來,因為孝文還沒有經過正經恢復父子關系的程序,所以得先擱在書院見面,如若自個找到保安團就有投拜兒子的倒茬子影響。
朱先生著一位同仁到縣城給孝文送信。孝文於天黑後才匆匆趕來,一見父親就跪下了。白孝文聽到父親要救黑娃的話咯咯咯笑起來:“爸你盡是出奇之舉!你一提說黑娃,我還當是催我快快處置了那個禍害哩!沒想到你……”白嘉軒又說著如同對孝武講過的道理:“瞎人只有落到這一步才能學好。學好了就是個好人。”朱先生插話發揮著白嘉軒的思路:“殺了可就少一個人了。”白孝文不作正面拒絕,軟軟地說:“上邊已經批示就地槍決。土匪不是共匪,不需再三審問殺了算了。你們說啥也不頂用,我根本沒有殺他放他的權力。”白嘉軒急切地說:“那讓我先到監裡看一回總可以嗎?”白孝文笑笑說:“看不成。誰也不准看。十二道崗道道都是倆人把守,蠅子也飛不進去——防他的土匪弟兄劫監。”白嘉軒一下子涼下來默然無措。白孝文說:“爸,你心好我知道,可這事比不得族裡的事喀!你回去吧!槍決黑娃以前,我給他說知道明,你想探監還想救他。讓他小子死到陰司再琢磨他對住對不住你!”
隨後就變成大拇指芒兒和保安團白營長共同設計營救黑娃的密謀。方案有二,由孝文在檢查崗哨查巡防務時捎給黑娃一根鋼钎,讓他自己挖摳磚縫的石灰自行逃脫;再一個辦法需大動干戈,組織一次游街示眾,由鄭芒領土匪相機劫持黑娃。倆人都認為第二個辦法屬於下策,只能作為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動。芒兒說:“見不著我的二拇指都不算數,太太得跟我到山上逛幾天風景,我會照顧好她的。”
第二天傍晚,白孝文就把一根細鋼钎塞給了黑娃。黑娃接住鋼钎時,那雙死絕的眼睛爍出一道利光。白孝文當晚剛回到東街住屋,後半夜時又有人敲窗欞。他開了門,黑暗裡瞅不准面孔。那人說:“我給你捎來一封信。”白孝文心裡緊縮起來,進屋到燈下拆開信封,原以為是土匪頭子鄭芒捎來的,不料卻是鹿兆鵬的親筆信,同樣是求告他設法留下黑娃性命。白孝文看罷信揚起頭來。送信人往燈前挪了兩步,嗤的一聲笑著問:“你還認識我不?”白孝文驚恐地叫起來:“韓裁縫?”韓裁縫說:“請你給個回話。”白孝文緊張地說:“你給鹿兆鵬說,讓他甭胡攪和,他越攪和黑娃死得越快。韓裁縫你也是共黨分子?今日要不是在我屋,我就把你扣起來。”韓裁縫沉穩地笑笑:“咱倆一對一你不是我的對手,拾掇你不用槍只用一把剪子就夠了。”白孝文也強撐面皮:“有禮不打上門客,你走吧!下次再這樣我就不客氣。”韓裁縫說:“鹿兆鵬也很重義氣。黑娃不過跟他鬧過幾天農協,後來不隨他了,可他還是想救他一命。你給個回話我就走。”白孝文冷靜下來重復一遍剛才的話:“你共黨甭胡亂攪和。你越攪和黑娃死得越快。還要啥回話呢?你走吧!”
黑娃越獄逃跑的消息比緝獲黑娃在縣城引起的轟動還要大。那個由黑娃掏開的牆洞往幽暗的囚室裡透進一個橢圓形的光圈,被各級軍政長官反覆察看反覆琢磨,卻沒有一個人懷疑到白孝文身上,因為黑娃是白孝文率領一營團丁抓獲的。白孝文按照早已籌算好的辦法,嚴厲地拷打站崗的送飯的團丁,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接近死囚室裡的黑娃。道理很簡單,拷問越嚴厲,他自己就越安全,終於打得一個送飯的團丁忍受不住而招了假供。白孝文請示了保安團張團長,就著人把奄奄一息的屈死鬼團丁拉出去埋了,這件事才漸次從記憶中消失了。
又一天夜深人靜時分,白孝文猛然聽到窗根下太太的隱聲呼叫,他急忙開門後,又差點兒被什麼東西絆了個筋鬥。他把太太扶進門來,到燈下一瞅,太太完好如初,才甚為欣慰,卻仍然忍不住說:“你受苦了。”太太淡淡地說:“他們還算義氣。”送太太回歸的土匪先翻牆後開街門已經走掉。白孝文去查看了一下街門木閂,回到房門口就瞅見絆過腳的一只袋子;拎起來一看,竟是一只完好的山獸皮筒子,到燈下解開扎口,裡面裝著滿滿一筒子硬洋。太太說:“黑娃回去以後,他們對我恭敬得很,黑娃給我磕了三個響頭。”白孝文說:“黑娃要是回不去,你就回不來了!”太太說:“黑娃讓我捎給你一句話,說他跟你的冤仇一筆勾銷。”白孝文心裡一震,瞬即深深地舒一口氣,捕獲黑娃的昂揚和釋放黑娃的緊張全部消失,更要緊的是冰釋了一樁無以化解的冤結。他與小娥的那種關系,黑娃早放出口風要殺他以祭小娥。至此,白孝文弄不清在這個事件中獲得多少好處了。他從櫃子裡拉出一瓶酒說:“喝一盅為你接風壓驚。”倆人干抿下一盅酒,白孝文以徹底卸除負累後的輕松舒悅的口氣說:“我們得准備回原上的事了!”
為了做得萬無一失,白孝文於次日演出了一場辭官戲。他換了一件長袍禮帽的便裝,把附有營長軍階標志的軍服整整齊齊折疊起來,徑直走進張團長的屋子,雙手托著軍服,把腰裡那把短槍摘下來擱在軍服上頭,一齊呈放到桌子上,向張團長深深鞠了一個大躬。張團長瞅著他虔誠的舉動,莫名其妙地問:“你這是干啥?”白孝文說:“枉費了你的栽培。嚴重失職——我引咎辭職。只能這樣。”張團長晃一下腦袋,很不滿意地說:“你怎能這樣?是小娃娃脾氣,還是書生意氣?”白孝文更加真誠:“無顏面對本縣百姓。”張團長說:“沒有人責怪你嘛!岳書記侯縣長都沒有說你失職嘛!”白孝文難受地搖搖頭說:“我自己無地自容!”張團長笑了:“我剛把你提起來,等著你出力哩,你可要走?好吧,按你這說法,我也得引咎辭職!”白孝文沒有料及這行動會引起張團長的敏感,於是委婉地說:“說真話,我是想承擔責任,旁人就不再對你說長道短……”張團長受了感動,就站立起來,把手槍拿起來,在手心拋顛了兩下交給孝文,說:“快把袍子脫了,把團服換上,咱倆出去散散心。這毬事把人攪得雞飛狗跳牆!”白孝文湧出眼淚來了。
陰歷四月中旬是原上原下一年裡頂好的時月。溫潤的氣像使人渾身都有酥軟的感覺。揚花孕穗的麥子散發的氣息酷似乳香味道。罌粟七彩爛漫的花朵卻使人聯想到菜花蛇的美麗……
白孝文攜妻回原上終於成行,倆人各乘一匹馬由兩個團丁牽著。白孝文穿長袍戴禮帽,一派儒雅的仁者風範。太太一身質地不俗顏色素暗的衣褲,愈顯得溫柔敦厚高雅。在離村莊還有半裡遠的地方,孝文和太太先後下得馬來,然後徒步走進村莊,走過村巷,走到自家門樓下,心裡自然湧出“我回來了”的感嘆。弟弟孝武恰好迎到門口,抱拳相揖道:“哥你回來了!”白孝文才得著機會把心裡那句感嘆傾泄出來:“我回來了!”及至進入上房明廳,父親沒有拄拐杖,彎著腰揚著頭等待他的到來,白孝文叫了一聲“爸”就跪伏到父親膝下,太太隨即跪下叩頭。白嘉軒扶起孝文,就坐到椅子上。白孝文又領著太太給婆白趙氏叩拜,然後便引著太太和兩個弟弟、兩個弟媳相見相認。白趙氏把兩個重孫推到孝文跟前:“這是你爸。”孩子羞怯地往後縮。白孝文伸手去撫摩孩子的頭時,倆娃跑到白趙氏身後藏起來了。白嘉軒對孝武說:“把飯菜端上來,咱們今日吃個團圓飯。”剛說完,又記起一件事來:“孝文,你領上你屋裡人,去拜一下你三伯。”
拜謁祖宗的儀式安排在午飯過後。因為長幼有序,白孝武不能主持這個儀式,只是做著具體事務,而由白嘉軒親臨祠堂主持。白鹿兩姓的成年男女,一聽到鑼聲,便早早擁進祠堂,看那個回頭的浪子重歸的風采,不便出口的興趣更在他的新娘子身上。白孝文領著太太在孝武的導引陪同下走進祠堂大門,便瞅見那棵又加粗了的槐樹,腦子裡頓然浮現出由他主持懲罰小娥和由弟弟主持懲罰自個的情景。他心裡一陣虛顫,又一股憎惡,然後移開眼睛,徑直走過院子,跨上台階,走近敬奉著白鹿宗族始祖及列代祖宗的祭桌前站定,那幅從屋梁上吊垂下來的宗譜,密密麻麻填寫著逝者的名字,下面空著的紅線方格等待著後來的人續填上去。白孝武點燃了兩支注滿清油的紅色木筒子蠟燭便退到一旁。白嘉軒佝僂著腰站在祭桌前,面對眾人發出洪大如鐘鳴的聲音:“祖宗寬仁厚德。不孝男白孝文回鄉祭祖,乞祖宗寬容。上香——”白孝文從香筒裡抽出五根紫香在蠟燭上點燃,雙手插進香爐,退後一步和太太站成齊排兒,一道長揖後跪拜下去,太太也作揖叩首三匝。白嘉軒又誦響了下一項儀式:“拜鄉黨——”白孝文和妻子轉過身面對祠堂裡外擁塞得黑壓壓的男女鄉親,抱拳作揖,鄉黨們也作揖相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