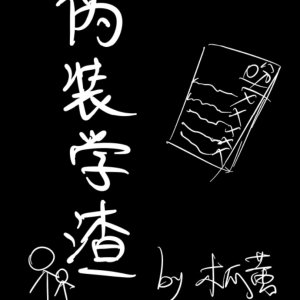封霄靜靜注視著她。
此時站在他眼前的田安安,和躺在他懷裡的時候非常不同。從最初認識到如今,她大多時候都是十分乖順的,沒有棱角也沒有尖刺,嬌柔得像只被豢養的貓咪,幾乎從來沒有露出過這種目光。
困惑,憤怒,壓抑,更多的是倔強。
諸多交織的情緒點亮了這雙清澈的眸子,折射出一種比過去的溫順嫵媚更加奪目的靈動,群山連綿的輪廓和透明涓細的水流都在她身後,她的神色鎮定而平靜,這是在面對他時前所未有的。
這是第一次,封霄覺得女人生氣的面容也十分美麗,也是第一次,他想看她更加憤怒並劍拔弩張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
男人修長的五指摘下眼鏡,隨後便點燃了一只雪茄,帶著幾分探究意味地目光落在她像牙色的臉蛋上,他勾起唇角沉沉一笑,淡淡道:“不喜歡又怎麼樣?”
不喜歡又怎麼樣?
他問她不喜歡又怎麼樣,以這種恣意而傲慢的神態,以這種散漫而滿不在乎的語調。
安安心頭一沉,目光中憤怒的光芒卻愈發地熾烈。一直以來,她像只寵物一樣被這個男人禁錮在身邊,沒有話語權,沒有反抗余地,在這個黑色的世界裡,她根本就沒有自由也沒有最基本的人權。
她想,這種慫不拉幾的忍耐終於到達極限。
這只隨時出於發情狀態的美利堅泰迪,以絕對專橫的手段侵占了她的身體,臥槽,現在居然還變本加厲,試圖染指她偉大聖潔的社會主義小粉紅靈魂?做他的青天白日夢!耍她很好玩兒麼,還特麼什麼男女朋友,下輩子都不可能!
田安安心中怒火翻湧,蹭蹭的怒氣直直衝向腦門兒,體內的洪荒之力也已經蓄勢待發。她對上他深邃黯沉的雙眼,沒有躲閃也沒有逃避,坦然而鎮靜,“封先生,雖然我知道,在你面前要求地位平等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認為,起碼你還是要尊重一下我的想法吧?”
男人沉默了幾秒鐘,回答時的聲音極度平靜,“我當然會給予你尊重。”
“……”sowhat?所以就是莫名其妙地讓人誤會她是你老婆?你這麼不講理你媽知道麼?
“只是尊重的範圍和內容,全部由我決定。”他繼續道,
“……”握!草!
田安安已經逼近抓狂的邊緣,她實在不明白,這個男人怎麼可以專斷強權到這種地步。這也再次有力地佐證了她的觀點,那就是她和他的價值觀差距實在太大了,這是民族文化和社會環境造成的結果,是人類和泰迪的種族間隔,是大自然的規律,這輩子都無法逾越的鴻溝!
安安白皙纖細的雙手在身側用力握拳,竭力使自己冷靜冷靜,合了合眼重新睜開,她笑了一下,“封先生,我想我必須再這裡跟你清楚明白地解釋解釋。”說著頓了頓,她步子微動走到左側的沙發前坐了下來。
封霄兩指間的雪茄安靜燃燒,他淡淡看著她,修長的左臂隨意地搭在沙發靠背上,從容不迫好整以暇。
盡管隔著一段距離,兩個人沒有任何肢體的觸碰,可是田安安依然覺得渾身都不自在。他的抬眸,勾唇,甚至是輕敲煙灰,任何細微的動作都能讓她心神不定。那道沉靜如湖的視線像一張巨網,無形之中就將她籠罩,束縛,不費吹灰之力地拿捏住她的每次呼吸。
掌心裡沁出了汗水,她的十指無意識地抓緊了裙擺,望著那個安靜淡漠的男人低聲道,“封先生,你的認知裡面似乎有一個盲點,那就是你並不明白男女朋友意味著什麼。”
他嘴角微微勾起,“洗耳恭聽。”
“……好吧。”她深呼吸再深呼吸,開始壓抑憤怒,耐著性子給他認真解說,“兩個人如果要成為男女朋友,首先是需要感情基礎的。”
男人淡淡嗯了一聲,不置可否,只是示意她接著說。
田安安見他沒有反駁,反而聽得很專注的樣子,瞬間膽子也稍稍大了幾分,連忙再接再厲,誠懇道:“其次,需要綜合考慮很多因素。”說著,她比出個白生生的手掌開始掰著指頭歷數,“像什麼成長背景,家庭條件,工作環境,朋友圈子,還有外貌啊,收入什麼的一大啪啦,你……明白什麼意思了麼?”
說完,她半帶期待地看向靠坐在黑色沙發上的高大男人。
遠處暮色中的山川線條成了他身後的背景,封霄一臉平靜,挺拔如畫的身軀微微前傾,將還剩一大截的雪茄在煙灰缸中熄滅,不置一詞。
看樣子是不明白。田安安癟嘴。
她無可奈何,只能再次平復一下躁動的心情繼續開口,“封先生,雖然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但是我還是決定為你犧牲一下,希望你真的要把我的話聽進去。”隨後,她開始就剛才提到的一系列因素,詳細地把他們兩人進了一個對比。
“成長背景,我們一個接受的是社會主義教育,一個接受的是資本主義教育,中美文化差異不是一般地大,呵呵。”她干笑了兩聲,然後繼續道,“再說家庭條件,我們家就是普通的工薪階層,和你們家……”她指了指周圍,“完全不是一個畫風。”
封霄靜默了幾秒鐘,然後微微頷首,“繼續。”
“工作環境和朋友圈子,這個我覺得可以直接略過,連對比都不用做了。”安安說得十分認真,“接下來是外貌。封先生您這個頭,層高矮點兒估計都快撞天花板了。所以我們倆連最最基本的體型和身高都不搭,你——這下總明白了吧?”
話音落地,她幾乎是屏住呼吸在等男人的答案。她希望自己的這番言辭沒有白費,就算不能帶來實質上的改變,只讓他不要再試圖侵略她的思想也是好的。
這一次封霄沒有令田安安失望。他眼簾微抬,漆黑的雙眸看向她,半晌之後竟然笑了,笑容裡甚至有些親切友善的意味。
不知為何,安安驟然遍體生涼。
她直視著那雙深邃的眼睛,天已經黑了,夜幕上頭沒有星光,他的眼睛卻比夜色更加暗沉漆黑。未幾,他沉靜無波的嗓音低沉傳來,“我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所以呢?
她眸光微動。
“你剛才的分析和說法都沒有問題。”他寥寥含笑,淡淡給出一個十分客觀的評斷,然後繼續道,“可是這些對我來說,都無所謂。”
田安安皺起眉,聲音霎時便沉了下去,“這只是對你。對我來說很有所謂,我很介意,非常地介意。”
“我知道。”他平靜地看著她,“所以你更應該讓自己盡快習慣,習慣我,習慣我做事的方式,習慣我的所有。”
這種邏輯簡直令人瞠目結舌。
安安驚呆了,瞬間的愕然之後,她內心的小宇宙已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就是這種讓人厭惡的感覺,他禁錮她的身體,現在還要控制她的思想,為什麼?憑什麼?他恣意妄為到這個地步,真覺得她人傻好欺負麼?對群眾進行無恥打壓是要報應的知道麼?
你!大!爺!
“……”田安安深吸一口氣吐出來,蹭地一下從沙發上站起身,抬眼,目光如炬地瞪向封霄,直接拒絕,“我不要。”
他勾了勾唇,“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見。”
她氣得肺都開始痛了,一雙明亮的眸子全被憤怒的火焰點燃,一連串忍了太久的字句連珠炮似的衝口而出:“你知不知道這種行為和做法真的讓人很反感?我招你惹你了,你要這麼對我?我上輩子是做了多大的孽這輩子才遇得到你!”
會客廳裡驟然爆發出這麼一道嗓子,剛剛折返回來的迪妃和徐梁皆是一驚。他們面色大變,杵在原地有些遲疑,不知道是該進還是該退。
這陣仗這聲勢,顯然,他們的先生和那個小丫頭在吵架。
徐梁臉皮子一抽,頭回對那個小姑娘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側目看了眼臉色同樣不好的迪妃,壓低聲音道,“怎麼辦?”
“能怎麼辦?”迪妃白了他一眼,接著便轉身准備遠離火藥味依稀彌漫的會客廳,提步邊走邊道,“不想死就離遠點兒。”
徐助理和田安安認識的時間長一些,對那小姑娘的印像不好不壞,聞言挑眉,一面跟著轉身,一面若有所思道,“當初在拉斯維加斯,先生出手救她,我還覺得有些奇怪。”
迪妃挑起唇角,“你什麼時候見過先生做善事?”
“沒有。”徐梁聳肩笑了笑,似乎覺得有點兒滑稽,“我根本想像不出來。”
“所以先生不會做善事。換一種角度來看,田安安是自己送上門兒的,怨不了任何人。”迪妃淡淡道。
徐梁聽後微微點頭,覺得這番話說得十分在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無論結果是什麼,都應該自己承受。他忖度著,心中又生出幾分感嘆來,說道,“可是很明顯,她內心是非常抗拒的。”
“抗拒又如何,不抗拒又如何,反正結果都一樣,先生不是一個在意過程的人。”
迪妃語調冷淡地說完這句話,接著回過頭,有些憐憫地掃了眼會客廳的方向,這才邁開大步走出了別墅大門。
會客廳中,內心非常抗拒的人已經完全爆發,所有的火氣都在這一刻迸射而出。田安安感受到了一股空前的迷之勇氣,她此時的膽子甚至比上回醉酒之後還要大,怒目,挑唇,冷笑,每個表情都極其到位。
她極其的生氣,這股怒火來勢洶洶,甚至連自己都不清楚是為什麼。她只是迫切地希望封霄這個名字從自己的生活中徹底消失,只是迫切地希望他能停止對她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打壓與掠奪。
“我就不明白了,你要什麼樣的女人沒有,怎麼就不肯高抬貴手放過我呢?”她疑惑而惱怒,頓了一下又繼續道,“就算你很喜歡睡我吧,那我拜托你不要影響我的正常生活好麼?我需要自由,不管是身體還是精神!”
然後極其鄭重地用他的母語復述一遍,一字一頓:“al!”
男人的視線幽暗深沉,他神色平靜,坐在沙發上任由她氣急敗壞怒火迸發,仿佛這些詞句和這場爭執都和自己無關。
田安安發泄完了,說完一番話,她的聲帶由於過大的響度而隱隱作痛,呼吸不穩,豐滿的前胸隨著每次呼氣吸氣緩緩起伏。
她怒衝衝地盯著她,起初還十分不甘示弱,漸漸的,她看見那雙漂亮暗沉的眼睛裡隱隱漫上了一絲笑意,詭異得觸目驚心。她手臂上雞皮疙瘩起了一層,不由毛骨悚然,半晌,她看見他竟然笑了,低聲道,“你生氣的樣子很漂亮。”
“……”臥槽臥槽臥槽。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啊這位大哥,說好的吵架呢!關注的點能不能別這麼奇怪!
安安由硬轉萎只在眨眼之間。
他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仿佛一根針,噗的一下就把她憤怒的皮球戳爆,她神色忽然變得十分古怪,別過頭移開眼,不去看他,清了清嗓子才沉聲道,“封先生,請你不要試圖轉移話題。”
半晌沒有得到回應,田安安狐疑地側目,只見男人不知何時已經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光整考究的西服外頭搭在手臂上,他上身只著黑色襯衣,頭發一絲不苟,威嚴沉肅,不必言語就能使人感到威脅。
安安看他脫了外套,幾乎被口水給嗆個半死,在她驚詫的目光中,他邁著大步朝她走了過來。
“……”後退幾乎已經成了條件反射,她喉嚨有些發緊,然而這次卻強迫自己站著,不許動,不要退縮。
晶亮的眼睛,硬生生看著他一步一步逼近。
很快,封霄到了眼前,和她隔得十分近,近到她能聞到他身上淡雅的清香,和她已經十分熟悉的男性氣息。近到她能看見那雙居高臨下俯視自己的眼眸深處,冰冷的暗潮。
“鬧夠了就去吃飯。”他的嗓音平穩,帶著幾絲寒凜的意味,從頭頂靜靜傳下來。
所以,他覺得剛才的所有話,都只是她在鬧麼?田安安更加憤怒,她仰著脖子,有種寸步不讓的意味,仰視著眼前比自己高大很多的英俊男人,道:“請你正視我剛才的所有言論,封霄先生。”
“我說,吃飯。”他面無表情,低沉地命令。
田安安咬緊牙關,雙手在身側用力收握松開,收握松開,好一會兒才深吸一口氣,轉過身,邁著沉重的步伐,地往飯廳的方向走去。
今天菲利亞准備的晚飯,是出乎安安意料的中餐。
她和封霄面對面而坐,由於剛剛起過一次爭執和衝突,兩人似乎都沒有交談的想法。她看了眼桌上精致清淡的菜肴,卻連一點胃口都提不上來,只是手持碗筷埋著頭有一搭沒一搭地進食。
難耐的死寂最終被一陣手機鈴聲打破。
田安安微微皺眉,拿出手機垂眼看,屏幕上赫然閃動著“母上”兩個大字。她心頭一驚,身子一動就准備到別處去接電話。
然而還沒等她站起來,對面一道低沉的聲音毫無預警地響起,語調漠然,不留余地:“哪兒也不准去。”
安安詫異地抬眼,落地窗外的天色已經濃烈如墨了,他就連坐姿都挺拔如畫,冷漠的面容俊美而凌厲,清冷的目光平平落在她臉上。
“……”這只泰迪對她的壓迫,已經變態到連接個電話都不能離開他的視線了麼?
安安覺得這個認知無比驚悚,她不敢再想了,趕忙埋下頭,有些不安地滑開了接聽鍵,沉沉道:“喂,媽?”
田媽的聲音很快從聽筒裡傳了出來,那一瞬間,田安安的鼻子都在發酸。也直到這一刻,她才發現世上真的只有媽媽好……
“丫頭,在瑩瑩家呢?”田媽一直以為這段時間她住在朱瑩瑩家裡。
“是啊……”田安安呵呵干笑了兩聲,指尖迅速將手機側面的聽筒音量調小,希望不被對面那個臉色喜怒難辨的男人聽見,繼續道,“在吃飯呢。”
“瑩瑩到底是什麼病啊?你帶她去醫院了沒?”田媽關心道。
“……哦,不嚴重,就是點兒小毛病,你不要擔心。”她喝了口湯隨口敷衍。
“那就好。那孩子一個人在b市,平時生了病也沒人照顧,你去陪陪也可以,不過得注意身體,不要沒把人家照顧好,自己也跟著病了,知道麼?”
她心頭一暖,連連點頭,“嗯嗯,媽媽我知道了。”
田媽嗯了一聲,然後就很快切入正題,她的語調較之前要上揚幾分,明顯心情雀躍:“媽媽跟你說,你方阿姨家的兒子從英國留學回來了,小時候還和你一起玩兒過的那個,記得不?”
安安皺起眉,狐疑道,“記得啊,叫顧青明,你提他做什麼?”
田媽媽笑了好幾聲,清清嗓子道,“丫頭,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大學都畢業快一年了,也是時候談個朋友了。”田媽頓了頓,續道,“青明那孩子我見過,個子高高的,斯斯文文,是你喜歡的類型。我都你方姨都說好了,明天晚上讓你們倆見面——嗯,相個親,看對眼了就好好處,了咱們一樁心事。”
“……”她一臉被雷劈了的表情,支吾著艱難開口,“媽,不急吧,我還沒到22呢……”
她媽的語氣瞬間沉了幾分,“你就說去不去吧。”
“……好的媽媽我知道了。”安安瞬間屈服於她媽的淫威之下。
田媽很滿意,又叮囑了幾句明天打扮漂亮點兒什麼的,接著就掛斷了電話。嘟嘟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安安稍稍怔了怔,隨之一咬牙,十分坦然地抬起了頭,看向對面神色漠然的安靜男人。
“封先生。”她喊了一聲。
封霄手上動作頓住,微微抬眼,冷漠的臉在背後夜色的映襯下如雕像一般沉冷。
胸腔裡的心跳在瘋狂地加速,她努力地維持表面的冷靜,然後低下頭沉聲道,“我媽給我安排了相親,咱們兩家人都知根知底,事情十有八.九會成……”她頓了下,右手死死握緊兩只筷子,繼續說,“我有個請求,如果以後我有了男朋友,請你無論如何,都不要再來打攪我的生活。”
田安安以前不知道,自己對封霄怕到什麼程度,而此時,她說完這番話後,竟然連看他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死一樣的沉寂。
立鐘的秒針游走著,偌大的飯廳裡只有指針異動的詭異聲響,對面的男人很安靜,安靜到讓她全身的寒毛都乍立起來。
良久之後,她終於率先耐不住了,抬起眼,目之所及,封霄的面容卻出乎意料的平靜。他眉目是舒展而平和的,甚至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慢條斯理地抽出濕巾揩拭嘴角,姿態優雅而閑適。
“……”
不知為什麼,他越是平靜,田安安越覺得不寒而栗。她埋下頭,胡亂地將碗裡的湯喝完,接著起身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封先生,我吃完了,你承諾過今晚會讓我回家,希望你不要忘記。”
半晌之後,封霄冰冷的嗓音在這個開闊的空間裡響起,簡單的幾個字,音調沒有絲毫波瀾,“抱歉,我不記得了。”
田安安一驚,眼睜睜看著男人緩緩起身朝自己走近,她很詫異,心中莫名升起一絲可怕的慌亂,瞪大了眸子道,“你竟然不守信用?”
“你不是也對我說了謊麼?”
他輕輕笑了,這笑容在安安眼中可怖到無以復加,幾乎是下意識的,她掉頭就想跑,然而還沒邁出一步,一股大力就拽住了她纖細的胳膊,在她的驚呼中,男人長臂一攬將她抱了起來,臉色陰沉地往樓梯走。
會死……
田安安冷汗都驚出來了,她覺得自己可能會死。
上到二樓時和徐梁迎面遇上,安安已經不敢掙扎了,她渾身僵硬地躺在封霄懷裡,聽見他步子不停地朝徐梁扔下一句毫無溫度的話,“給她的公司遞交辭職信。”
徐梁一怔,愣了下才說了個是。
“你要做什麼?”她眉頭用力皺緊,聲音幾乎在顫抖,“我不要辭職,你沒有權力剝奪我的工作!”
田安安頭暈目眩,還來不及開口,他高大沉重的身軀已經重重壓了上來。身上的連衣裙剎那間被扯成了破布仍在一旁,他十指的動作蠻橫得接近凌.虐,她吃痛,出於本能地蜷縮成一團,雙眸無比驚恐地盯著他。
封霄抬起眸子,沉靜地注視著自己身下雪白嬌小瑟瑟發抖的女人,唇角勾起一絲笑,指尖輕輕滑過她的臉頰和脖頸,“記得我說過什麼。”
“……”她臉色慘白,定定望著那雙漆黑的瞳孔裡映出自己的驚恐的面容。
“只有疼痛能使人記憶深刻。”他笑得森寒徹骨,有力的手臂毫不留情地將她壓制,沉聲道,“你屬於我,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希望今天能讓你永遠記住。”
沒有任何預警,干澀帶來撕裂一般的疼痛,幾乎令她尖叫出聲,然而隨之,他冰冷的唇落了下來,緘封住她顫抖的唇瓣,啃咬舔舐,蠻橫而狠戾,吸吮著她唇上湧出的血珠。
田安安幾乎被逼到絕境。
他的眼神熾烈而布滿陰霾,甚至帶著幾分壓抑的病態和瘋狂,有力的雙臂和身軀將她柔嫩的四肢狠狠壓在床上,野獸對待獵物一般折磨啃噬,她在他的唇舌下稍稍適應了幾分,一片迷蒙與昏沉之中,終於反應過來,這其實是一次懲罰。
這是第一次,他令她如此疼痛。
汗珠從他的額頭落下,滑過棱角分明的下頷,最後落在她不斷顫栗的雪白脖頸上。
不知過了多久,她開始哭泣,認錯,求饒,然而他的眸色卻愈發地幽沉狠戾,在她身上愈發蠻橫肆意地征伐。
兩只纖細的手腕被男人單手鉗制住,力道極大,疼痛不住傳來。安安的眼淚一直在流,自己都分不清是因為疼痛還是因為快樂,封霄低下頭,吻去她每一滴苦澀清澈的淚水,高大的身軀微俯,將身下嬌軟的小東西抱了起來。
一片迷蒙之間,田安安無助地抱緊他的脖子,感受到他在走動,然後將她抱到了衣帽間的落地鏡前。
封霄甚至沒有退出去,粗糲的指腹在她滿是淚痕的面頰上輕柔摩挲,然後扣住她脆弱的下頷骨,轉向了透明的鏡面。
她驚恐地瞪大眼,不敢相信鏡子裡渾身青紫紅痕交錯的女人是自己。
他低低地笑了,舌尖滑過白嫩的耳垂,“漂亮麼?”
“你一定是個瘋子……”安安顫聲道。
“告訴我,你是誰的?”他勾起她的下頷,目光灼灼地俯視她。
安安艱難地回答:“你的。”
“還敢忘記麼?”
她悶哼了一聲將他抱得更緊,聲線顫抖道:“……不敢。”
與此同時,他的動作終於緩和下來,薄唇在她汗濕的小臉上落下細密的吻,一路從額頭到下巴,然後抱著她重新回到大床。她在這種強勢卻輕柔的壓制下幾近崩潰,任他予取予求,甚至主動吻上他微涼的唇。
得到她嬌柔的回應,他眼色一深,將她完全鎖進溫熱堅韌的胸膛,埋首在她敏感雪白的肩窩處重重流連親吻。
田安安的思維越來越混亂,目眩神迷中她聽見自己的聲音突然響起了,低低的,柔柔的,靠貼在他的耳畔,“你……你是不是喜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