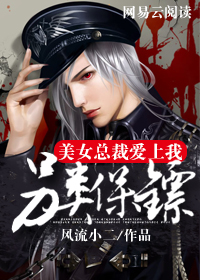“那地方可就多了,這小子整天四處跑,有時候在這個坊,有時候在那個坊,偶爾還會跑到外城去,你們要找他就只能在這兒等著了,今天他不在,明天,後天,總有一天會來的。”
白二郎忍不住問:“那要是一直不來呢?”
“那必定是卷著錢跑了,或是被人打斷了腿,動彈不了,你們呀,也就沒必要等了。”
三人:……
滿寶輕咳一聲問道:“大叔,那你聽說過小神醫嗎?”
“哦,你們是為了聽故事來的呀,早說呀,我知道這故事,”他笑道:“那小子有什麼新聞都是先跟我們說的,不過呀,我看這些事都是人家給了錢讓他傳的,多是編的,你們可別信,這要看病啊,還是得找老大夫,老大夫經驗豐富呀。”
三人:……
“說是邳國公府的小公爺落馬,傷得嚴重,太醫院的太醫們都治不好了,結果橫空掉下一個小神醫,把小公爺的肚子剖了,還抽了好幾個人的血給小公爺補上,就把快死的小公爺給救回來了。”大叔嗤之以鼻,“從沒聽說過救人要剖肚子的,還抽了別人的血給補上,而且那小神醫聽說才十來歲,太醫院那麼多太醫呢都沒用,指望一個小姑娘?”
滿寶忍不住豎起大拇指,“大叔你真厲害,不人雲亦雲。”
“那是,那小子整天守在這幾個園子和酒樓外面,一有詩會文會什麼的就衝到最前面,只要有人肯給錢,他就把人寫的詩文吹到天上去,我早看透了。”
白善問,“他平時都會在哪兒傳消息或收消息?”
“就這塊兒,還有附近的幾家酒樓,要是都沒有,那就是到別的坊去了。”
三人謝過,便一邊吃著東西,一邊四處逛著找那些大酒樓。
滿寶很好奇,街上的人是不是都不信這個傳言,於是找了不少人問。
“小神醫呀,我知道呀,就不知道她看病貴不貴,不貴的話,我還想帶我家老婆子去看一看呢。”
“我信啊,這外頭都傳遍了,計太醫因為治不好小公爺,被太子砍了一刀呢,結果那小神醫給治好了。”
“聽說她會輸血大法,就是把另一個人的血給抽給病人,我就好奇,那個人不會死嗎?”
“這血是怎麼從一個人的身體裡到另一人的身體裡的?”
其他人也很好奇,於是擠開滿寶三個,自顧自的熱烈討論起來。
滿寶被擠出人群之外,和白善懵懵的對視一眼,聳了聳肩後轉身離開。
白二郎又去買了一包糕點,一邊吃一邊追上他們,問道:“我們到底要去哪兒找呀?”
白善用下巴點了點前面道:“喏,前面。”
白二郎就往前看去,就見大山正坐在一塊石頭上繪聲繪色的在說些什麼,他身邊圍了不少的人。
滿寶從白二郎的紙袋裡捏出一塊點心來,一邊吃一邊道:“果然,循著人多的地方找去總能找到的。”
三人也不叫他,好奇的湊上去聽他到底是怎麼給她傳流言的。
“現在街上傳的什麼小神醫剖腹那都是假的,你們別聽他們瞎說,那是以訛傳訛知道嗎?”
三人:……
滿寶和白二郎一起轉頭去看白善。
白善在倆人的目光下沉默的看著正蹲在椅子上說得正歡的大山。
大家一起搖頭。
“是綿州人,綿州和益州特別近,在進京前,這位小神醫就跟濟世堂的大夫和太醫院出去的範太醫學醫術了,知道範太醫嗎?”
“知道,知道,茶樓裡說書,偶爾會提到範太醫,聽說他就能給人開膛破肚。”
“沒錯,這小神醫的醫術就是跟他們學的,可不是有句話,叫什麼青比藍更好嗎?這小神醫就比範太醫還要強點兒,聽說她在益州城時就給季相大人家的小孫子治過病,所以這京城的太醫院也是知道她的。”
眾人紛紛頷首。
大山道:“這小公爺從馬上掉下來,計太醫說治不好了,鄭太醫也說沒把握,這才沒辦法請了小神醫去,巧了,這小神醫進京以後也是在濟世堂坐堂。”
“這小神醫真有這麼厲害?”
“神童啊,你想啊,國子學的公子們厲害吧?”
“當然厲害了,祖宗厲害,哈哈哈哈……”
“可這小神醫的師弟,他爹可不是三品官兒,他就能進國子學,你們說厲害不厲害?”
眾人一聽,以為白善是從幾千人裡考進去的,怔了一下後連連點頭道:“厲害,厲害。”
“可他是師弟,這小神醫才是師姐,那師姐不是比師弟更厲害嗎?”
眾人一想也是,“那她真抽了人的血補給小公爺?那被抽的人……”
大山壓低了聲音道:“你們知道她抽的是誰的血嗎?”
大家也不由放低了聲音,低聲問:“誰的?”
“就是和小公爺打馬球把他打落馬的杜家國公和小公爺的,還有一個,”大山神秘兮兮的道:“太子殿下的!”
滿寶他們不知何時也蹲到了人群外面興致勃勃的聽著,白二郎都小聲的對白善道:“他說的比你好聽多了。”
白善都不得不承認。
“外頭現在傳的,什麼把人抽干了血給小公爺補血,那都是假的,小神醫的師弟的同窗的書童告訴我,這血啊也分為好幾種,每個人的血都有點兒不一樣,大致可以分為四種,得找到合適自己的血才能抽血。”
“這抽血也有講究,身子太弱的人不能抽,有病的人的血不能抽,每次抽還不能抽太多,真的失血太多,可以換著抽,多抽幾個人嘛。”
眾人打抖,問道:“這血要怎麼抽出來了呀?”
“直接拿刀一抹就成了,我好奇的是這血是怎麼灌到另一個人的身體裡的,是不是讓他喝下去?那人要是昏迷喝不了怎麼辦?”
大山有點兒傻眼,白善沒告訴他這個是怎麼灌的呀,他也只愣了一下就揮手道:“這是大夫吃飯的本事,那她能告訴我們嗎?”
“不能,不能。”
“就是,所以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