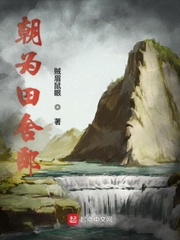下一瞬,他就看見滕玉意帶著婢女離席而去。
藺承佑琢磨一番,決定先靜觀其變,喚人把鎏金鴻雁銀匜拿來,淨了手給阿芝剝胡桃吃。
這時外頭忽有幾名僕從匆匆過來,一部分徑直去寶翠亭找淳安郡王,另一部分卻過來尋藺承佑。
藺承佑見是幾位國舅身邊的常隨,蹙了蹙眉:“出什麼事了?”
領頭那個名叫寶忠,一向是劉府最得力的管事,此刻他臉色極為古怪,附耳對藺承佑說:“傍晚小人奉國丈之命去迎接南詔國的顧憲太子和那幾位外地官員的女眷,碰巧半路遇上了,小人們便在前帶路,哪知穿過一座林子時,後頭那幾輛犢車一下子不見了,顧憲太子唯恐是鬼祟作怪,自己帶護衛在原地找尋,讓小人趕快回來找世子殿下和郡王殿下。”
藺承佑詫異莫名,此地是皇伯父和伯母御幸之所,年年都有僧道隨行,不遠處還建有一座皇家寺院,寺中梵音不絕,即便附近有鬼祟游蕩,也往往避之不及,況且來時路上他也瞧了,方圓左右都“干淨”得很,怎會突然冒出鬼祟。
他霍然起身:“人在何處?”
阿芝納悶道:“阿兄,出什麼事了?”
藺承佑摸摸阿芝的腦袋:“前頭有人找阿兄,阿兄去瞧瞧。”
***
滕玉意回到月明樓,把事情原委告訴了杜夫人。
杜夫人雖然覺得荒謬絕倫,但小涯劍遠不如當初在紫雲樓澄亮是事實,她上回見識過這劍斫殺妖邪的本領,心知阿玉離不開此劍,當即與滕玉意商量起來,若說是為了女孩子的貼身物件向男子討要浴湯,別說丈夫絕不會同意,淳安郡王也會覺得受冒犯。
於是托人給丈夫帶話,只說桂媼的某位親戚重病不治,要丈夫幫忙向淳安郡王討點浴湯做藥引。
坊間為了治病常有古怪之舉,有人自割雙耳做藥引,有人取了馬尿來喝,比起這些荒誕不經的藥引,一罐浴湯算不了什麼。
杜裕知聽了果然深信不疑,回說既是為了救命,只等散了筵,他立即開口向郡王殿下討要。
滕玉意聽到回話才放心,杜夫人把滕玉意摟到懷裡,心裡暗暗嘆息,玉兒想是前陣子嚇壞了,好不容易有把護身的劍,自是千珍萬重唯恐出岔子。這孩子自懂事起,無論遇到何事,總是習慣自己一個人應對,長到這麼大,還是頭一回求到姨父姨母身上。
她心軟得一塌糊塗,摸了摸滕玉意烏黑的頭發說:“這下可以放心了,一切交給姨父姨母。等到討到了浴湯,姨母再與你姨父說明原委,你姨父心裡很疼愛你,不會怪咱們騙他的。今晚昌宜公主和阿芝郡主在場,各府的小娘子也在,你離席久了會顯得失禮,先回席再說。”
滕玉意在姨母懷裡膩了一會,戀戀不舍走了。回到水瀑邊,淳安郡王卻已經不在寶翠亭了,詫異地用目光找尋,不止淳安郡王,連藺承佑也不見了。
她悄聲問杜庭蘭緣故,杜庭蘭搖了搖頭:“想是前院有什麼事,郡王殿下和藺承佑被叫走了。”
忽聽笙鼓喧嘩,第一輪酒令開始了。眾人玩了一個多時辰,別說沒看到藺承佑和淳安郡王返回,連那幾位外地官員的女眷也遲遲不見入席。
這下不只滕玉意覺得古怪,連杜庭蘭也有些驚訝,杜紹棠起身離了男席,坐到兩位姐姐身邊,疑惑地說:“都戌時中了,再晚就該散席了。”
滕玉意讓春絨去找端福打聽出了何事,端福卻回說只知道藺承佑和淳安郡王出了府,同行的還有幾位國舅,但究竟出了什麼事,他也不知。
昌宜和阿芝少了哥哥和皇叔的陪伴,便有些意興闌珊,又玩了一會,懨懨地下令散席了。
貴女們聽了,只好回各自的院落歇憩。
杜紹棠送兩位姐姐回了月明樓,因為不便進內院,只送到院門口就走了,上了二樓,杜夫人尚未歇息,迎出來道:“總算散席了。你姨父還未睡,姨母馬上讓桂媼遞話。”
滕玉意搖頭:“淳安郡王被人叫出去了,聽說還未回來。”
杜夫人愣了愣:“何時才能回?都這麼晚了……老爺若是夜半去拜謁,未免太唐突。”
滕玉意心裡油煎火燎,小涯發了那通脾氣後便再無動靜,照這個情形看,小涯未必能等了。
換作往日她絕不會坐以待斃,但小涯要的不是別的……對方不肯沐浴的話,神仙也弄不來浴湯。
她絞盡腦汁想對策,因為太出神沒接穩春絨遞來的蔗漿,杯子裡的甜液一下子灑落在身上。
“呀!”
杜庭蘭一驚:“當心黏到腿上,快把衣裳脫下來。”
杜夫人說:“今晚也不會再出屋子了,直接換寢衣吧。”
滕玉意卻擔心浴湯能不能順利取來:“我還得等消息,拿件干淨襦裙換上吧。”
碧螺到行囊前隨手一拿,結果又是晌午滕玉意剛換下的蓮子白襦裙。
滕玉意皺眉:“怎麼又是這件?快換件別的。”
“明日才是正式壽宴,奴婢晚間才把娘子的幾件衣裳熨過了,橫豎這件娘子明日不會穿,先將就一下吧。”
滕玉意只好接過裙裳穿了。藺承佑早在被蒲桃酒弄污衣裳就把他那件換了,再說已經深夜了,這裙子穿在身上料也不會有人留意。
屋裡正亂著,樓下的院子突然傳來喧嘩聲,桂媼出去打聽,過了一會回房說:“樓下來了好些夫人和小娘子……聽說是那幾位外地官員的女眷,今晚也要在月明樓安置。”
滕玉意一喜,照這樣說,會不會淳安郡王和藺承佑也回來了。
她忙令春絨去前頭打探消息,杜夫人把簪環插回發髻上:“國丈府對這幾位女眷這般重視,想必是朝中重臣的妻女,我們房裡還亮著燈,不過去問候一聲的話,未免有些失禮。走,去瞧瞧。”
拉過女兒和滕玉意瞧了瞧,還好兩人衣飾齊整,三人下了樓,花廳裡燈光如晝。
榻上坐著好些女眷,滕玉意抬頭望去,竟大多數不認識。
左邊坐著一位夫人和一對孿生姐妹,夫人大約三十多歲,面容威嚴,身段瘦削。
那對孿生姐妹與母親生得很相似,身型卻比母親足足豐白一大圈,配上銀盤般的圓臉、細長的鳳眼,倒比母親相貌更端麗些。兩人約莫十五六歲,裝扮一模一樣。
滕玉意又看右邊那對母女,女孩身上披了件水色披風,裡頭隱約露出鵝黃色襦裙,額間貼了水粉色的花鈿,唇邊也點了兩團紅色的胭脂,生得秀美絕倫,姿色遠勝那對孿生姐妹。
滕玉意越看越覺得這少女面熟,李淮固?
李淮固依在母親懷裡,眼裡還含著淚,抬頭看見滕玉意,先是一怔,隨即綻出驚喜的笑容:“阿玉。”
滕玉意一訝:“李三娘。好久不見。”
“阿娘,是滕將軍的女兒。”李淮固驚喜地扶著母親起身,又欣然對滕玉意說,“我還以為你不認得我了。”
滕玉意欠身給李夫人行禮:“怎會認不出,也就四五年沒見,你跟小時候模樣差不多。”
李淮固握著滕玉意的手仔仔細細打量,又低頭看她身上的裙裳,不住點頭稱嘆:“這衣裳真好看。早就想去找你了,但我才到長安,今日一整日都在趕路,路上還在想,不知能不能在壽宴上見到你,怎知真讓我見著了。”
李夫人與杜夫人見過禮,含笑凝視滕玉意:“這孩子越生越好看了。你阿爺可好?府上可好?”
滕玉意一一回了。
李夫人比對著自己女兒和滕玉意,笑嘆道:“這麼一比,還是阿玉強點。”
李淮固微微一笑,矜持地問杜庭蘭:“蘭姐姐,你是不是沒認出我?
杜庭蘭噗嗤一聲笑起來:“早就認出你了,我記得你眼下有顆小小的朱砂痣,你瞧,它還在這兒呢。”
說著溫柔地點了點李淮固的臉頰,李淮固眼波裡笑意漾開,一左一右拉住滕玉意和杜庭蘭:“今日太高興了,你們住在哪間房?我與你們同住吧。”
杜庭蘭遲疑了一下,滕玉意卻歉然道:“哎呀,怕是不行。房裡只有三張床,都這麼晚了,姨母她老人家不便挪動衾被……”
杜夫人和李夫人笑著搖頭:“今日太晚了,有什麼話改日再說吧。這些孩子,一見面就膩在一處。”
李夫人又引她們到榻前,指了指那位瘦削的夫人:“這位是淮西節度使彭將軍的夫人,這是彭家大娘、彭家二娘。”
滕玉意笑容微滯,先前她在席上因為惦記小涯的事並未細聽,原來晚到的女眷裡竟有淮西節度使的妻女。
她前世並未與彭家的女眷打過交道,此刻仔細端詳彭氏母女,腦中像被掀開一塊塵封已久的布,一下子湧出來好多早已淡忘的碎片。
記得前世駐守淮西道的是名將彭思順,彭思順病逝後,接掌兵權的是彭思順的長子彭震,彭震狼子野心,不久之後便集結鄰近蕃道發動了兵變。
前世阿爺之所以率兵出征,正是為了剿平淮西之亂。
……可是……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太對,按照前世來推算,彭思順早在去年就過世了,等到阿爺出征之際,淮西道、淄青、山東南道已作亂半年多了,儼然有愈演愈烈之勢。
但她這陣子從未聽說淮西有叛亂,而且從彭夫人和彭小娘子的裝束來看,也不像在服重孝的樣子。
莫非彭思順還活著?
滕玉意思緒紛亂起來,該不是自己的記憶出了差錯,否則為何今生有這麼多與前世不同之處。
彭夫人對杜夫人說:“……這是我們大娘,名叫花月。二娘麼,名喚錦繡。”
兩方見過禮後,各自回到榻上落座,幾位夫人輕聲寬慰:“彭夫人李夫人受驚了……所以竟是路上遇到鬼祟了麼?”
李夫人臉色發白:“突然刮來一陣怪風,犢車就走不動了,外頭有女人在哭,拍打窗棱想進來,那情形簡直嚇死人,還好成王世子和郡王殿下及時趕到,不然還不知會怎樣,”
彭夫人畢竟出身貴要之家,此時已經鎮定了不少,苦笑道:“當時看到一道銀鏈子打過來,我們只當又是鬼祟,哪知周圍的鬼影一下子全都不見了,才知有人相救……都說成王世子師從清虛子道長學了一身好本領,今日算是大開眼界了,這小郎君好俊的身手。”
李淮固垂下眼睫,神色寧靜不知在想什麼。彭花月和彭錦繡似是想起當時情形,嚇得再一次縮在母親身後。
正聊著,管事過來說廂房裡的寢具已經安置好了,時辰不早,還請彭李兩家的女眷回房安歇。
滕玉意隨姨母和表姐回了二樓,碧螺已經打探消息回來了,說淳安郡王才回府,方才桂媼已經托人給杜老爺帶話了。
三人舒了口氣,滕玉意催杜夫人和杜庭蘭歇息:“姨母,阿姐,你們先睡,我一個人等消息就是。”
***
藺承佑一行在門前下了馬,把馬鞭扔給侍從,徑直回了飛逸閣。
顧憲邊走邊與淳安郡王說話,無意間一轉頭,就見藺承佑仍若有所思擺弄手裡的小荷包。
“女鬼都被你收進荷包了,還有什麼不對勁麼?”
藺承佑:“我怎麼覺得,這鬼像是被憑空投在此處的。”
顧憲哦了一聲:“何謂‘憑空’?”
藺承佑把荷包往懷裡一塞:“這鬼凶厲無比,死前必定懷著極大的怨念,它不似那等漫無目的的尋常游魂,飄蕩到此處總要有個緣故,可剛才我問它從何而來、為何在此作祟,它竟一概不知,像是被人抽掉了幾魄,存心引到此處似的……”
淳安郡王詫異道:“存心如此?那人目的是什麼?”
三人默了一下,指不定是奔著車裡的那些女眷來的,一邊是彭震的妻女,另一車是李光遠的妻女,這二人……
一個是雄踞一方的強蕃,另一個是頗蒙聖寵的新貴,京中有人因為嫉妒而生事,倒也不奇怪。
淳安郡王思量著說:“還好車裡都是將門之女,膽子不算小,若是一下子嚇得神志失常,那可就麻煩了。”
顧憲想了想:“說起車裡的女眷,那位李娘子當真沉穩聰慧,當時承佑一到就問出了何事,大多數女眷都嚇得口齒不清了,只有她還能勉強說清來龍去脈。說起來也夠險的,女鬼回來撲襲李娘子時,還好承佑帶著一根能長能短的法器,否則也不能及時把人救下。”
剩下的話不必說,今晚只有承佑一個人會道術,為了救人勢必要追出去,在外耽擱久了,不但對李娘子名聲有損,承佑也麻煩。
這時院子裡有位管事迎過來說:“郡王殿下總算回來了,先前小人出去布置宵夜,回來房裡就多了些香囊、團扇、香餅、詩箋……看著像女子之物,不知該如何處置?”
顧憲訝道:“該不是對王爺示愛吧?”
管事垂首表示默認。
顧憲笑起來:“沒想到長安娘子跟我們南詔國的女孩一般直率大膽。承佑,你房裡該不會也堆著一大堆吧。”
藺承佑正要接話,管事又說:“國子監的杜博士有事求見,殿下見還是不見?”
淳安郡王一怔,若非急事,也不會這麼晚來拜謁。他點點頭說:“快請杜博士進來。”
顧憲便自行回廂房了,藺承佑原本也要回房,想了想,忽又負手跟上淳安郡王。
淳安郡王奇道:“你不回房歇息麼?”
藺承佑隨他進了房間,徑直在一旁榻上撩袍坐下,笑道:“我餓了,到皇叔這討點宵夜吃。”
不一會杜裕知隨下人進來,簡單寒暄幾句,就直率地稟明了來意。
淳安郡王驚詫莫名,然而沉下心來一想,杜裕知一向是京中最正直最有傲骨的文臣,若非急等著救命,絕不至於厚著臉皮深夜過來討浴湯。
他震驚片刻,咳嗽兩聲道:“既是為了救人,杜公不必覺得難為情,我正要沐浴焚香,杜公在此稍候片刻就是。”
杜裕知自是感激不盡。
淳安郡王一走,房裡就只剩藺承佑和杜裕知了。
杜裕知拘謹地飲了一口茶,不經意一抬頭,就見藺承佑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杜裕知早知道藺承佑頑劣不羈,當即戒備地掃了他好兩眼,確定他不像要刁難自己的樣子,這才重新坐直身子。
可就在這時候,藺承佑和顏悅色開了腔:“敢問杜公,貴府那位老媼的親戚是突發急病麼?”
杜裕知茫然思索起來,來時還未聽說有此事,直到晚間妻子才突然令人傳話,嗯,應該是突發急病沒錯。
“回世子的話,正是急病發作。”
藺承佑:“頭一回聽說用浴湯做藥引,可知是哪位醫工下的方子?”
杜裕知搖頭:“這……杜某也不知,只知急需藥引救命。”
藺承佑笑了笑,沒再接著往下問。
杜裕知暗松了口氣,就聽耳房門響,淳安郡王像是怕杜裕知久等,很快就沐浴完出來了,將手中的水囊遞給杜裕知,正色道:“也不知夠不夠,我令人在浴斛守著,若是不夠,杜公只管令人傳話。”
杜裕知肅容接過浴湯,千恩萬謝告辭了。
這時管事領人送宵夜,淳安郡王讓管事去鄰房邀顧憲,又對藺承佑說:“你不是早說餓了,這會倒不見你動了。”
藺承佑把茶盞擱回案幾,笑道:“不成了,我才想起還有點事要交代阿芝身邊的人,還得出去一趟,皇叔你們吃吧,不必等我,我回來就歇了。”
***
滕玉意在房裡等了一陣,遲遲不見姨父派人回話,干脆坐在桌前,從鏤空牙筒裡取出一根牙箸,蘸了水寫寫畫畫。
杜庭蘭在鏡台前卸了簪環,走過來一瞧:“在寫什麼?”
滕玉意若有所思把那個“三”字抹去,托腮嘆道:“今日見了李淮固,我倒想起不少小時候的事。”
杜庭蘭一向心細如發,也思忖著坐下:“我記得李淮固小時候靦腆多了,今日看她說話,倒是比從前沉穩不少,聽說她阿爺如今也是一方要員,想來這幾年沒少在阿爺身邊歷練。”
滕玉意歪著頭想了想,李淮固的父親擢升比前世快多了,如果她沒記錯,她前世死的那一年,李光遠還只是阿爺淮南道轄治下的蘇州刺史,沒調任浙江,更沒兼任浙東都知兵馬使……
今日這一見,才知李淮固的父親已是小有名氣的藩臣了。
不過經過這幾樁事,她早已習慣這一世的事與前世的記憶不同了,只是內心深處,仍隱隱覺得有點不對勁……
這時外頭忽有人敲門,滕玉意等不及,親自去開門,果然是碧螺回來了。
碧螺微微喘著氣:“不好了,中門全都落了鑰,聽說御宿川出了怪事,幾位國舅怕昌宜公主和阿芝郡主受到驚嚇,下令在女眷的院落外嚴加看管,選的都是一等護衛,嚴禁各院串門。奴婢沒法托人傳話,也不知道杜老爺在前頭如何了。”
杜庭蘭啊了一聲:“這可如何是好。”
滕玉意心亂如麻,走到暗處輕輕敲了敲劍柄,劍身幾乎只溫熱了一下,就冰冷如水了。
“來不及了。而且白日我同端福說好了,他晚間會在月明樓東北角牆外的中巷裡等消息,只要姨父取到東西,碧螺就會給端福送話,現在中門一鎖,兩下裡都得不到消息,我得趕快去傳話,省得端福和姨父一直苦等。”
說著摸了摸懷裡的禿筆,隨意找了件披風披上了,杜夫人和杜庭蘭見狀忙說:“你別去,讓碧螺她們去。”
滕玉意說:“碧螺不會翻牆,我多少懂點招數。再說院子裡人多眼雜,中間又隔了窄巷,端福性子謹慎,如果不能確定是我,未必肯現身,假如碧螺高聲叫嚷他的名字,定會引來護衛,所以還是我去最快。”
她不容分說掩上門,下樓尋到東北角,果見牆外有一株柳樹,低聲就要喚端福,恰巧外頭窄巷裡一陣整齊的腳步聲快步走過,想是護衛巡防。
滕玉意斂聲屏息,等牆外回歸安靜,兩手向上一攀,悄悄爬上了牆頭。
她自從練了桃花劍法,身姿就比從前輕捷許多,回來後又跟霍丘學了不少招數,爬牆完全不在話下。
攀到牆頭坐直身子,她迅速朝四下裡一看,居然一個人也沒有,莫非端福方才為了避人躲開了?
正猶豫著是跳下去還是翻牆回去,就聽不遠處有腳步聲走來,是個男人,而且只有獨自一人。
滕玉意二話不說就要往回跳,那人卻冷不丁叫了一聲:“王公子。”
滕玉意身子一晃險些沒掉下去,竟是藺承佑。
她坐穩身子扭頭朝下看,就見藺承佑在巷中負手仰頭望著她。
她心中驚疑不定,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世子?”
藺承佑笑了一下:“你在找端福麼?”
滕玉意想了想,干脆跳入巷子裡:“世子瞧見端福了?我有事要找他,哪知各處都落了鑰,婢女送不出話又不會爬牆,只好我自己來了。”
藺承佑懶洋洋舉起一樣東西:“你在等它吧?”
滕玉意怔了怔,藺承佑手裡的是一罐水囊,而且他似乎為了證實她心中的猜測,還故意在她面前晃了晃水囊。
滕玉意聽到水聲晃動,臉驀然一紅。
“你——”
“這是皇叔的浴湯。”藺承佑一哂,“下午你讓端福潛進飛逸閣,原來是為了偷浴湯,偷了我的還不夠,連皇叔的浴湯都騙。”
滕玉意窘得無地自容,左右瞄了兩眼,打著哈哈笑了笑,然而從臉頰到脖頸,皮膚幾乎一霎兒就變紅了,被月光一照,活像染了胭脂似的。
藺承佑睨了幾眼,莫名覺得眼熟,咦,她身上穿的布料竟跟他白日那件襴袍一模一樣。
他挪開視線:“你一個小娘子,弄這麼多男人的浴湯做什麼?別告訴我是為了好玩,嘖,我都替你臊得慌。”
滕玉意原本還想好好解釋解釋,被他毫不留情指責一通,愈發恨不得鑽進地縫裡,瞪他一眼道:“當然是為了辦正事,緣故麼,下午我已經跟世子說明了,怎奈世子不信。”
藺承佑抱起了胳膊:“為了供養你那把劍?劍裡的器靈說的?”
滕玉意沒吭聲。
藺承佑譏諷道:“你就不會好好同我說麼,非要偷我的浴湯?”
滕玉意奇道:“如果我好好同世子說,世子就會把浴湯給我?”
藺承佑一噎,他見過無數道家至寶,頭一回聽說要男人浴湯供奉的,假如滕玉意照直同他說,他定會因為覺得荒謬斷然回絕。
他呵了一聲:“滕杜兩家那麼多男人,為何偏要偷旁人的?”
“因為只有你們的浴湯才算胎息羽化水,旁人的浴湯會損壞我這劍的靈力。”
“又是劍裡的器靈說的?”藺承佑哼笑一聲,“行吧,你既然偷到了我的,為何還要找皇叔討要?”
滕玉意:“下午世子在溫泉池裡沐浴,水裡不小心摻雜了旁人的浴湯,器靈不肯洗。”
藺承佑撫了撫下巴,好個矯情的器靈。想到她又一次暗算他,他就氣不打一出來,假裝在他面前絆倒,暗中卻把一整囊的蒲桃酒灑到他身上。
滕玉意瞧他一眼,低頭行禮道:“我不該令人偷世子的浴湯,這是我的不是,我自願向世子賠罪。我這劍剛從彩鳳樓回來就不行了,事情來得太急,我也想直接跟世子討要,可是又……又……實在說不出口。我也是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
藺承佑一哼,說得好可憐見。
滕玉意把小涯劍取出來給他瞧:“世子瞧瞧吧,我的劍靈快要死了。”
藺承佑:“器靈死不了,充其量靈力大幅減弱。”
滕玉意一愣,死不了麼?她沒好氣地說:“世子手邊的法器數不勝數,損壞一兩件對你而言算不了什麼,可是小涯劍既然認了我做主人,我就得好好護著他,在我手裡別說損壞靈力,渴一點累一點都是不成的。”
藺承佑摸摸耳朵,自從與她打交道,沒少見識她身上這股軸勁,對身邊的人和物看得極重,簡直比他還要護短。
滕玉意說完那番話,理直氣壯向藺承佑攤開手:“世子問完了吧?淳安郡王既然已經把浴湯給我姨父了,這東西就是我的了,世子可以把東西還給我了嗎。”
藺承佑沒吭聲,話是問完了,看她手中黯淡的劍光,的確也撐不了多久了。
然而他心裡還是覺得不對勁,滕玉意令人偷他的浴湯,卻讓姨父當面向皇叔討要浴湯,莫非她之前就打聽過皇叔的為人?所以確定皇叔一定會給?
想當面問問她究竟是怎麼想的,又覺得好像沒必要。
而且,他一想到滕玉意用皇叔的浴湯泡她的貼身小劍,心裡就說不出的古怪。
罷了,先把這法器救“活”再說,至於她又一次暗算他的事,稍後再跟她清算。
他把水囊遞給她:“拿著吧。”
“多謝世子。”滕玉意高興地伸手去接,誰知還未接到手中,水囊就摔倒了地上,瓶蓋一松,囊中的浴湯瞬間淌了一地。
滕玉意一呆,急忙蹲下來去撿,可終究遲了一步,囊中的水很快只剩個底了。
滕玉意抓著水囊看了一晌,再抬頭時,杏圓的眼睛裡已然有了淚花。
“藺承佑!”她咬牙切齒從齒縫裡擠出一句話。
藺承佑望著水囊發怔,鬼知道他剛才在想什麼,居然沒拿穩水囊,眼看滕玉意一下子氣哭了,他竟有些無奈,以他的身手,若說自己不是故意的,別說滕玉意不會相信,連他自己也覺得說不通。
滕玉意氣得臉都白了,依她看,藺承佑就是故意的,這樣做無非氣她下午暗算過他,但她如果能當面討要來浴湯,何至於出此下策。
看樣子小涯的靈力是救不了了,即便小老頭活著,也會變成一件毫無法力的廢品。她心中恨得不行,虧她前幾日還覺得藺承佑是好人。錯,此人何止性情囂張,簡直可惡至極!!!
“藺承佑——”她眼淚在眼眶裡打轉,胸膛劇烈起伏著,要不是尚存最後一絲理智,真想抓花他的臉。
藺承佑像是猛然回過了神:“我的浴湯是不是也能用?”
滕玉意眼睫上還掛滿淚珠,怒容卻一滯。
“我賠你就是了。不能要溫泉池裡的,只能要浴斛裡的對不對?”
滕玉意喜出望外,哪還顧得上生氣,忙含淚點點頭:“是的,不過得快點。”
“你在此處等著,我先前做了安排,短時辰內不會有人來此巡查,我稍後就來。”
藺承佑邊說邊向後退了幾步,一個鷂子翻身,身影消失在屋檐上。
滕玉意望著空蕩蕩的窄巷,心裡七上八下,藺承佑真願意把浴湯給她嗎,不會又打算坑她吧。而且來了這麼久,一直沒看見端福,她滿腹疑團,在原地干等了一會,唯恐被人撞見,翻牆回到月明樓的院牆裡,直到再次聽到腳步聲,才把腦袋探出牆角,確定是藺承佑,她悄悄從牆上跳下來。
藺承佑換了衣裳,鬢角還是濕漉漉的,臉上掛著水珠,眉目精致絕倫,一從屋檐上跳下,就衝滕玉意招手:“你身手不行,翻牆當心水灑出來,就在這兒供奉吧。”
滕玉意看他手中端著一個酒甕,足足比淳安郡王的水囊大上一倍,到了他跟前,還沒開口說話,先聞到他身上清馥的香氣,似竹非竹,清幽絕俗,自小她也算見過不少名貴香料,從沒聞過這樣好聞的澡豆。
藺承佑揭開甕蓋,裡頭果然盛著一大甕清透的浴湯,輕輕把甕身放到地上,湯面受震,泛起一團團細小的漣漪。
兩人望著浴湯,都有些不自在,末了還是藺承佑臉皮更厚,主動開口說:“把劍放進去吧。”
等了片刻,小涯劍毫無動靜,藺承佑狐疑地說:“器靈怎麼跟你說的?是這樣供奉的麼?”
滕玉意思忖道:“小涯只說要用胎息羽化水洗身子,論理泡進去就可以了。”
話音未落,水面劇烈地蕩漾起來,只一個錯眼,小老頭就從劍裡鑽出來了。
“喲吼!”小涯歡快地攪動浴湯,“哇哇哇哇哇哇!太舒服啦!老夫活過來了!”
他邊說邊往水裡猛地一鑽,旋即又探出身子,原本青灰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又紅又亮。
“咦嘻嘻!哦吼吼!好舒服,真痛快!”小涯舀了大把浴湯使勁搓自己胸膛,口中怪笑聲不斷。
“這湯真香,嘻嘻嘻嘻嘻,老夫從來沒有泡過這般正宗的胎息羽化水,藺承佑,你小子不錯!你好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