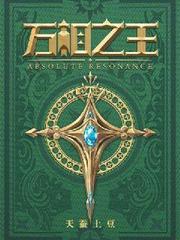楚望生瞪大眼睛看著鏡子中的自己,仰天狂笑起來。
“狗奴才,你立功了,立大功了,去,到賬房領五兩銀子,就說是本少爺賞你的。哈哈哈!”
“謝少爺,謝少爺!”楚小書歡喜的眉開眼笑,免費贈送的丹藥,不但治好了自己,還治好了少爺,平白得了五兩銀子的豐厚賞賜,天上掉餡餅,不過如此了吧!
楚小書歡天喜地的跑出門去了。
婢女捧著銅鏡正要放回原位,冷不丁的就被楚望生拽過胳膊按在床上,楚望生抓起一只枕頭墊在婢女小腹處,淫笑道:“急什麼,本公子憋了這麼多天,一肚子火沒地方宣泄,今兒個好好臨幸你。”
楚望樓從書房出來,往西府走,行了幾步,碰到小人稟告說三公子楚望生傷勢已經痊愈。他便折道朝楚望生宅子走
庭院深深,曲徑百折,沿途丫鬟僕人,無不恭恭敬敬稱呼一聲:“大爺!”
楚望樓心情似乎有些沉重,臉上沒有往日那般令人如沐春風的笑容,使得一些自詡美貌的婢女打消了秋波暗送的心思。楚府上下眾所周知,大少爺楚望樓很優秀,在牧野城青年俊彥中是佼佼者。他不但在修煉上天資橫溢,性情上也幾乎完美無缺,溫和又不失威嚴,懂兵法韜略,熟讀聖人經典,最關鍵的是他身上極少有尋常紈绔子弟那種縱情聲色的氣息。這樣一個豪門嫡子,將來注定是平步青雲,不可限量。
楚望樓十八歲及冠那年,雲氏給他娶了一個平妻,正妻位置始終空懸,後來便隨父親楚長辭進去軍隊,一來培養嫡系人馬,二來歷練歷練。牧野城中不知道有多少豪門請媒人登門,想把府上千金嫁入楚府。
很少有人知道楚望樓其實風流成性,只是他從來不吃窩邊草,除了雲氏不喜之外,主要還是想在楚長辭面前塑造一個不沉迷美色的形像。再者楚望樓對投懷送抱的女人提不起興趣,府上唯一讓他心動的兩個女子,一個是水族落魄千金,一個是三妹楚浮玉。
楚望生這兩年步步緊逼,一半就是得了大哥楚望樓的授意。至於後者,純屬是心中齷蹉的思想,夜深人靜的時候念想一下。前幾日聽到楚望舒殺了個回馬槍,從拓跋春竹手中救中楚浮玉,他驚怒之余,還有一絲不能與人言的慶幸。
楚望樓走入這棟雅致寬敞的小院,見到了容光煥發的胞弟,正坐在屋中悠然品茶。額頭有一大塊紅痕,除非之外不見傷疤。
“大哥!”楚望生驚喜交加。
楚望樓點頭示意,坐在桌邊,凝視著楚望生的額頭,嘖嘖稱奇。
“還不給大少爺上茶!”楚望生轉頭吩咐面色潮紅,媚眼如絲的婢女。
楚望樓久經花場,一眼便看了出來,意味深長的看著婢女聘婷身影。
“大哥若是喜歡,只管送你便是。”楚望生嘿嘿笑道。
“非我所愛,食之無味。”楚望樓搖搖嘆息。
“大哥莫急,水玲瓏那小賤人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楚望生握緊茶杯,神色狠辣:“他楚望舒一個庶子,憑什麼跟我們鬥?自以為有幾分身手便可以耀武揚威?爹爹說過,誰笑的最好不打緊,誰笑到最後才是關鍵。就像沙場征戰,我可退百裡千裡,一退再退,只要能得勝果,一切都不重要。”
楚望樓沉吟不語。
婢女端著熱氣騰騰的茶返回,楚望樓接過茶杯,笑容溫和的點點頭。
婢女羞紅了臉,眼波柔媚。
楚望生不耐煩的揮揮手:“出去!”
“母親那邊可有什麼計策?”楚望生低聲道。
“不知!”
楚望生不滿的叫了一聲大哥!
楚望樓失笑道:“後宅的事情母親從不讓我們過問,有言在先,男子主外,女子主內,不過顧此失彼。所以我是真的不知道。”
“干脆派人把那小子干掉。”楚望生臉色陰毒的做了個抹脖子的動作。
“母親似乎也有此意,只說時機未到,因為他極少出府,即便楚府也走不遠。再者我們沒有適合的人手,軍中好手不能用,母親的意思我能猜到幾分,前幾日聽翠竹說母親寫了封密信,傳書青木城。我猜測應該是請雲氏派遣高手相助。”
“也可能是跟大舅商議你與夢言表妹的婚事。”楚望生揶揄道。
楚望樓眉頭一皺,腦海中浮現那個刁蠻跋扈的身影,心中不喜。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雲氏又是青木成顯赫大族,於情於理他都不能抗拒。也罷,男人三妻四妾,什麼女人沒有?一個正妻名分而已,給她就是。
“前日我在府中碰到了水玲瓏,說出來你或許不信,我猜她還是處子。”楚望樓喝了一口茶,悠然道。
楚望生目瞪口呆。
楚望樓捏著茶蓋,輕輕拂過杯沿,沉聲道:“不說這些,邊境出事了。”
楚望生愣了愣:“什麼事?”
“三天前,周邊的幾個蠻族聯手侵犯邊境,來勢洶洶,打了邊軍一個措手不及。今日千裡加急的公文才剛剛送入城中,父親午時就要趕赴戰場,主持戰事。”
“這幫蠻子瘋了?寒冬腊月的打什麼戰。”楚望生目瞪口呆。
楚望樓嘆了口氣,“父親讓我留在城中籌備軍資,重點提到要搜羅丹藥,想必前線受損頗大,藥材緊缺。待會兒我要親自跑一趟玉華閣。”
門外忽然刮進來一陣大風,帷幔翻飛,檻窗震動,天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暗了下來,墨雲翻滾,片刻後,院裡劈裡啪啦一片水點子,一場冬雨洶洶來襲。
楚望生目光注視著雨水淅淅瀝瀝的沿著檐角滴落,像飄搖不定的珍珠簾,被寒風一刮,又飛花碎玉似的歇歇打入。
他忽然笑道:“這雨大風急的天氣,三姐今晚怕是出不去了。”
楚望樓“嗯”了一聲,低頭喝茶。
“你說她就這麼恨嫁?整日拋頭露面跟那幫家伙飲酒作樂,生怕別人不知道她有多美多迷人?這下倒好,楚府三小姐艷明遠播,嘖嘖,娘親怕是暴怒如雷了吧。就她這樣還想嫁個好人家?”楚望生哂笑。
“她不是恨嫁,是不想嫁。”楚望樓頓了頓,放下茶杯,“不妨和你說些內情,你聽過就好,別跟母親去說。母親本意是想把她許給拓跋家的嫡長子做平妻,我前幾日有件事求拓跋春竹,就跟她說母親是要讓她給拓跋大少爺做妾,她果然慌了,答應晚上出席酒宴幫我說服拓跋春竹。其實我跟拓跋春竹的交易就是她。”
楚望生又一次目瞪口呆。
“所以她就開始自暴自棄了?真想做那人盡可夫的婊·子?”
“沒有,後來被楚望舒攪黃了。她也不是要自暴自棄,她這是在自污,壞了自己的名聲。效果確實也不錯,拓跋府再也沒有提過這門親事。”
豪門世子飲酒作樂,一般都是找青樓女子作陪,或者家中妾室,小門小戶的庶女偶爾會參加,但次數極少。因此楚浮玉放蕩之名,在牧野城上流圈子已經頗為響亮。哪家公子哥要在府上邀請好友飲酒作樂,都會派人來楚府投請柬,邀楚浮玉出席。既有面子又不需要花錢,豈不是比請那些勾欄裡的庸脂俗粉更來的劃算?
“娘親自然大怒,但這事兒還沒有告訴父親,因為她知道這是楚浮玉無聲的抗爭。告訴了父親,也只會怪她沒能力管教子女。”楚望樓笑道。
楚望生眼珠轉動,不知在想什麼。
“你這傷疤消失無蹤,想必是用了玉華閣的生肌丸吧?你倒是有幾分先見之明,玉華閣生肌丸是個好東西,不過供貨量不多,父親想為兩千親兵備一份丹藥而不可得。正發愁呢。你怎麼買到手的,這落下傷疤就不好看了。”楚望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