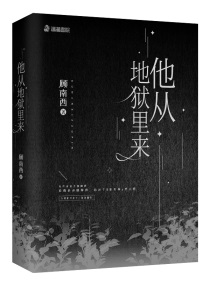他的目的是把官鶴山和沈清越一鍋端掉,而且還要置身事外,不髒自己手。
果然,玩計謀,誰玩得過戎六爺。。。
七月八號,雲淡風輕。
中午一點,大明酒店。
助理張莽敲門進來:“沈先生。”
沈清越手傷還沒好,但石膏已經拆了:“准備得怎麼樣了?”
張莽回話說:“都准備好了。”
中午一點十六分,顧起和阮姜玉從酒店房間出來,直接坐電梯到了負一樓的停車場。
阮東沛夫妻已經在車裡等了。
顧起幫她開了後座的車門,自己沒有上去:“我有件急事要處理,你和爸媽先過去,在教堂那邊等我。”
她上車:“好。”
顧起轉身,去另外一輛車。
“少澤。”
他回頭。
她把頭探出車窗,對他說:“我在教堂等你。”
他什麼也沒說,折回去,在車窗外吻她,用力又粗暴地吻她。
他到死也不會忘了那年拳擊台上的她,張揚得像暗夜裡的魔鬼,而他被魔鬼挖走了心。
魔鬼還不要他的軀殼。
他轉身上車,沒有再回頭。
車開出了酒店,楚未看了一眼後視鏡,已經看不到人了:“五爺,為什麼不帶她一起走?”
明明那麼那麼喜歡,明明把她當成命,又為什麼不要命呢?
顧起聲音低落到沒有力氣:“她不會跟我走。”
楚未沒愛過人,不懂情情愛愛那套:“那就綁著她走。”
楚未七年前就跟著顧起,看著他一步一步擴大版圖,一步一步讓罌粟花開滿紅三角。
他是很多人眼裡的魔,也是很多人眼裡的神。
他們五爺想要的,什麼要不到。
顧起終究還是回了頭,望著後面:“她會殺了我。”
“那就砍掉她的手和腳。”
“我舍不得。”
他說他舍不得。
五年前。
他給了宋稚假的時間和地址,讓國內的警察撲了空。
她那麼聰明,什麼都猜到了,她沒有逃跑,闖進他的地盤裡,與他對峙:“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他的辦公室在頂樓,那裡是維加蘭卡最高的地方,是權利的最頂端。
他說:“半年前。”
她走近他,目光逼視:“為什麼不殺了我?”
為什麼不殺?
他甚至把知道她身份的人都滅口了,為什麼不殺她?為什麼還放她在枕邊?為什麼還把最心愛的槍送到她手裡?
顧起抬起手,按在她胸口:“宋稚,你有沒有心?”
她拿出槍,槍口指著他心髒的位置。
她身後,十幾個人同時拔出槍,全部對准她。
顧起下令:“放下。”
唯一敢開口的只有楚未:“五爺——”
“放下!”
楚未咬了咬牙,把槍放下了,十幾個弟兄也跟著放下了槍。
宋稚手裡的那把槍是顧起送她的,他最喜歡的一把,槍柄上刻了gq兩個字母。
她大聲告訴他,她有沒有心。
“**年一月八號,鎮守雲市邊境的七名緝毒警全部被****。**年五月二十三號,喬真景隊長一家被****,**年九月十七,兩名一線臥底被你們強行****,**發作後****。”
這只不過是他數不清的暴行中的三件而已,也許不是他做的,但也是他底下的人做的。
宋稚問他同樣的問題:“顧起,你有沒有心?”
如果有,一定是黑的吧。
她手指扣住扳機。
“砰!”
“砰!”
兩聲槍響,幾乎同時。
宋稚的那槍打在了顧起胸膛,偏離心髒三釐米。楚未的那槍原本對准的是宋稚的腦袋,顧起拉了她一把,子彈擦過她頭部,也打在了他胸膛。
“五爺!”
那次,顧起丟了半條命,從此退出國內市場。
宋稚頭部受傷,成了植物人,躺了四年,醒來後卻沒了記憶。
下午兩點四十分。
白玉港在帝都與珠市的分界線上,緝毒隊的人上午就過來潛伏了,等了四個小時,卻沒有半點風吹草動。
偽裝成漁民的老朱坐不住了:“楊隊,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楊成章把漁網撒出去,動作有模有樣:“稍安勿躁,接著等。”
宋稚沒有拿到最新的交易信息,到底行動有沒有暴露,還得不到確認,只能先按原計劃進行。
下午兩點五十五分,阮姜玉接到了電話。
楊成章這下可以確認了:“我們的人裡的確有對方的臥底,行動暴露了,交易地點不在白玉港。”
行動暴露了,那她也暴露了。
阮姜玉掛掉電話,把頭上的白紗蓋上。
教堂裡沒有別人,她一個人坐著,在等他。
黑海位於建州境內,離帝都市內有一個半小時車程。
下午兩點五十八,離黑海三千米遠的橋上,停了一輛賓利,純黑色的車身,車窗緊閉。
沈清越靜靜地等著,手指落在座椅的真皮墊子上,有一下沒一下地敲著。
三點整,他的手機響起。
他看了來電後接聽。
“沈先生,顧五爺已經到了。”
顧五爺敢親自出馬,那就說明不會有警察。
沈清越掛掉電話,吩咐主駕駛的張莽:“開車。”
一刻鐘後,賓利抵達了交易地點——黑海五號碼頭的一輛游艇上。
顧起靠坐在一個木箱子上,指尖夾著一根煙,已經燃掉了半根:“你遲到了。”
沈清越帶了二十幾個人,他走在最前頭,拄著導盲杖:“抱歉,路上堵了。”
他怕顧起唱空城計詐他,所以故意晚來了一步。
顧起把煙扔在甲板上,用腳碾碎,頭上的鴨舌帽壓得很低,帽子上繡了一柄槍,帽檐的陰影落在眼睛裡。他穿著黑色襯衫,袖子挽著,手臂的肌肉張馳有力。
“驗貨吧。”他說。
沈清越回頭使了個眼色。
得了指令後,一個男人上前,打開木箱子,用刀子割破其中的一包,蘸了點,嗅了嗅。
這是紅三角目前能提煉出來最純的貨。
男人驗完貨,對沈清越點了點頭。沈清越吩咐下去,一手接貨,一手交錢,錢不是用現金,都是用鑽石。
整個交易用時不到十分鐘。
顧起下船之前,沈清越叫住了他。
“五爺,給你個忠告。”沈清越手裡的導盲杖敲著甲板,不輕不重,一下一下,“不要輕易把弱點放在一個女人身上。”
會敗得很慘。
顧起左手插著兜,側著身子,耳朵上黑色的耳釘在太陽下閃著光:“我也給你個忠告,不要輕易打我的主意。”
打他主意的人,不會有好下場。
沈清越載貨的船沿著黑海下游,駛向了茂東市的方向。
顧起沒有立刻離開白玉港,車在碼頭停了一會兒,他靠著車門抽了根煙:“把定位給穆裡發過去。”
方提打了個電話吩咐下去。
他們的貨裡藏了定位,這批貨可不是什麼人都要得起的,五爺更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招惹的。
方提掛了電話,上前:“五爺,飛機已經准備好了。”
顧起把煙掐了,單獨上了一輛車。
傍晚六點十八分。
載貨的船停在了茂東碼頭,沈清越下了船。
西山的夕陽正在往下落,把天邊染成了一片火紅,像畫家用水彩不均勻地潑出來了一幅畫,濃墨重彩,顏色艷麗而有層次。
碼頭上已經有人在等了,是個中年男人,他帶著一伙人,等候多時。
“沈先生。”
沈清越吩咐:“把貨安排下去。”
中年男人回話:“是。”
搬貨的人剛上船,遠處的燈塔突然亮了,毫無預兆。
隨後,傳來一聲:“putyourhandsup。”
是非常純正地道的英文。
話落,槍聲隨之響起。
有埋伏!
幾十個保鏢立馬上前,把沈清越擋住,為首之人說:“沈總,我們掩護你,你快走。”
是誰?
紀佳?顧起?還是戎黎?
“砰砰砰!”
槍聲打亂了沈清越的思緒。
來的是穆裡·克裡斯。
顧起說了,這貨誰搶到就算誰的,lyd絕不追究。
“沈先生。”張莽上前去給沈清越領路,“快走!”
對方人太多,各個都是強盜中的好手,殺人不眨眼,沈清越雇的人根本不是對手,他咬了咬牙,拄著盲杖倉惶而逃。
張莽提前准備了一艘小艇,是沈清越吩咐的。沈清越多疑且縝密,早就布置好了退路。
張莽先上去:“沈先生,你把盲杖先給我。”
天也快暗了,沈清越眼睛不好,根本看不清,他把盲杖遞給張莽,張莽再用盲杖給他引路,拉他上船,可他伸手剛要去抓住盲杖的時候,盲杖卻換了個方向,錯開他的手,拄在他胸膛上,用力一推。他往後趔趄,眼鏡掉在地上,灰蒙蒙的一雙瞳孔沒有焦距。
小艇上的張莽突然咧嘴一笑,把盲杖用力一擲,扔進了大海裡,他拍了拍手:“你還是留下吧,別浪費了我們顧五爺的一片心意。”
沈清越視線模糊,只看得到個輪廓,他眼角發紅,脖子上的青筋鼓著,血液在翻湧:“你是顧起的人?”
張莽吩咐小艇上的水手開船,然後扭頭揮了下手:“拜拜咯。”
小艇開走了,開得飛快。
顧五爺的人?
他當然不是,那他是誰的人呢?戎六爺嗎?更確切地說,他是金錢的奴隸,他是“錢”的人。
槍聲越來越急,越來越囂張。
“砰!”
子彈打進了沈清越的後背,他整個人栽進水裡。
六點五十七分,天已經暗下去了。
紀佳在lys電子的門口等了半個多小時,戎黎終於出來了。
她走上台階,迎上去:“等你很久了,戎六爺。”
戎黎手裡拿著個很亮的手電筒,他抬起來一個角度,把光打在紀佳身上,上上下下照了一番:“有事?”
“有件事想找你確認一下。”紀佳不拐彎抹角,就打直球,“從哪一步開始,是你的手筆?”
四周很暗,戎黎披著一身很漂亮的人類皮囊,像地獄裡的魔鬼:“從官四的那個小情人開始。”
紀佳算了算,那這盤棋至少兩個月前就開始了。
官四的那個小情人挑起了官四和沈清越的矛盾,戎黎把阮姜玉這個誘餌拋給她,她為了把官四弄出來,又把誘餌轉手給了沈清越,而這個誘餌最後成了顧起殺掉沈清越的動機。
她、官四、沈清越、顧起,全部都在戎黎的這盤棋裡,還有各方勢力的眼線、強大的情報網,全部都在這盤棋裡,然而戎黎他自己,一滴血都沒沾。
紀佳佩服佩服啊:“六爺不愧是借刀殺人的高級玩家。”
“給你個建議。”戎黎把手電筒往上提,照著紀佳的眼睛,“什麼都別做,不然顧起第一個要滅的就是你。”
畢竟這份誘餌是她給了沈清越。
漂亮。
紀佳無話可說。
戎黎打著燈走了。
紀佳接了個電話,阿明打來的:“佳姐,四爺說裡面的飯太難吃了,讓你快點把他弄出來。”
戎黎要端了lyh華娛,誰能阻止得了,阻止了這次也還會有下次。
是時候辭職了,紀佳最後幫前任老板售後一下吧:“跟他說,好好認罪,爭取減刑。他的財產我會幫他清算,讓他寬心,我會讓他在裡面吃香的喝辣的。”
晚上八點,lyh董事長因涉嫌非法交易被拘留調查一事上了新聞頭條。
lyn酒店破產才多久,lyh華娛跟著就出事了,圈內有傳聞,說是有人在搞錫北國際,接下來要遭殃可能是lys電子,或者lyg物流。
錫北國際的好日子要到頭了。
所有事情都按著戎黎的預設在進行,只有一件事出乎了他的意料,顧起沒有回斯蘭裡,也沒有回維加蘭卡。
戎黎只是想借顧起的手,端了沈清越的窩,其他lyd和緝毒隊的事,跟他無關。阮姜玉是這個棋盤裡的變數,她恢復了記憶,改變了顧起的軌跡。
晚上八點五十八分,顧起出現在了教堂。
------題外話------
****
今天還有一更,在晚上十點後
求月票~




![營業悖論[娛樂圈]](/uploads/novel/20240317/9985d76983fd97f0a81dceee3a72fc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