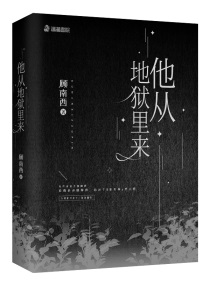大廳左側的走廊內,二毛指著地上的小虎吼道:“干他,出事算我的!”
一聲令下,數不清有多少腳丫子,多少拳頭,以及多少雜物,全都一股腦地砸在了小虎的身上。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禍!
這老話說的一點也沒錯,翻開新聞看看,有多少身居高位的官員,有多少生意做大的老板,都因為袒護那四處惹禍,缺心眼的老婆而翻車。
小虎對比普通人,他確實算是發跡了,但要真跟幕後大佬,甚至是徐勁波那個階層的人比,說到底還是個馬仔,是個小蝦米。但他不懂得收斂的道理,所以一著不慎,直接就炸了。
來追討賠償款的底層兄弟,心裡不知道窩了多少火,他們真的是往死裡打小虎,打他那張臭嘴。眾人只兩三波集火後,小虎就身體癱軟且變形地倒在了牆邊,一動不動。
這時,各樓層的安保部成員也衝了下來,烏泱泱的也有五六十號人,連地下停車場的人聽到信,也都衝了上來。
保龍集團總部大樓,高達三十六層,每層都有安保人員,所以此刻下樓的安保員,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人正在往這裡趕。
安保人員衝出電梯後,領頭一名穿著緊身西裝的青年,一看小虎被打倒了,連動都不能動了,立馬扯脖子吼了一聲:“踏馬的,反了你們了!給我揍,往死裡揍!”
安保成員拿錢干活,上面發話,他們不可能不聽。再加上來抗議的人群裡,也沒有人是攜帶違禁物品的,所以他們心裡沒障礙,拎著警棍就全都衝了上去。
兩撥人堵在一樓走廊口,劈裡啪啦地干了起來,尤其是後下來的那名西裝革履的青年,手裡拿著一把槍,喊得最凶:“媽的,給這幫癟三全給我打出去,往死裡揍!”
“就你硬是嗎?!”二毛穿過人群,抬腿一腳就揣在了西裝男的腹部。
“咕咚!”
西裝男趔趄著靠向牆壁,舉槍吼道:“你再踏馬動一下試試,信不信我崩死你!”
“來,來來,你不整死我,我都看不起你!”二毛伸手就扯對方的脖領子。
“亢!”
也不知道是西裝男面對上二毛有些緊張,還是他真的就敢開槍,總之二毛往前剛邁一步,槍聲就響了。
“噗!”
二毛左肋當場飆血,但好在對方的身體是被積壓在牆邊的,開槍的時候姿勢別扭,所以子彈是擦著二毛肋部射出去的,只讓他受了皮外傷。
但這一下也讓二毛急了,低頭看了一眼肋部,雙眼通紅地罵道:“你踏馬還真敢開槍是嗎?!”
“嘭,嘭!”
二毛兩拳打在西裝男的臉上,左手動作極為利落地壓住了他拿槍的手腕:“給我干殘他!”
話音剛落,蘇天南從後面衝上來,抬腿一腳揣在了西裝男的腹部。
二人合力,先將西裝男的槍搶了下來,隨即左右開弓,直接將其打倒在了台階上。
“你還敢崩老子?!”二毛從小就生活在海外,一路從底層干起來,那不知道經歷過多少事,就他這個歲數和段位,說是王者級的街頭鬥毆選手也不為過。
二毛踩著西裝男的胸口,伸手從腰間抽下皮帶,並將兩頭合在一塊,讓皮帶卡子一頭衝下:“拿槍牛逼啊!啊?!”
“啪!”
“啪!”
“!”
二毛靠在牆邊,小臂小幅度擺動,起碼往西裝男的頭部,抽了二十幾下,打得對方臉頰和腦袋皮開肉綻,鮮血嘩嘩地往下淌。
西裝男被打急眼了,拱著身體想要衝出去,但都被蘇天南連續扁踹給踹了回來。
“噗嗤!”
情急之下,西裝男一口咬在了二毛的腿上。
二毛疼得一收腳,氣急之下,抄起電梯口擺放的垃圾桶,衝著西裝男的腦袋就砸了下去。
“嘭!”
“嘭!”
“!”
外皮近乎於實心的垃圾桶,在西裝男的腦袋上砸了四五下,後者瞬間挺屍,一動不動了。
“我踏馬干死你!”二毛還要再砸。
蘇天南一把扯過二毛的胳膊:“別打了。”
二毛喘息著松了松領口,擺手吼道:“砸!反正也不給錢,把大廈的辦公室全砸了!”
大廳外圍,根本拉不住眾人的警員,最終在沒辦法的情況下,選擇了鳴槍示警。
三聲槍響在室內炸響,眾人短暫地安靜了下來。
“都不想活了是嗎?!你們這是在犯罪!”領頭警員拿槍指著眾人吼道;“都特麼給我蹲下!”
眾人扭頭看向了後側。
“我最瞧不上你們這幫狗!”蘇天南突然指著對方罵道:“我們申訴,你們不管;我們挨打挨罵,你們也不管!你們穿著那身衣服,卻過來給私企,給資本站崗!龍城司法系統有你們這幫蛆,永遠也好不了!!我認識一個勞工,他在錫納羅剛回來,就想辦個入籍,你們層層剝削層層卡,把他逼得家破人亡。老子要不是有家裡人壓著,我特麼早上錫納羅跟趙巍虎去干了,干死你們這幫蛀蟲!尺軍的人手裡有槍,有炮,他們一進龍城,你們就全眯著了,沒有一個敢站出來。”
罵聲在大廳內回蕩,警員們目光驚愕,甚至表情有些迷茫。
“滾!”
“再不滾,老子連你一塊打!”
“!”
走廊口人聲鼎沸,警員們沿著唾沫後退。
“咣當!”
就在這時,門外又衝進來二三十號人,領頭一人也是陸豐的兄弟,他快步奔跑向左側吼道:“誰打我家工人了?!媽了個b的,抄他家了!”
“呼啦啦!”
一群人衝進走廊,第二輪戰鬥繼續打響。
五分鐘後,保龍集團一二層多個區域全部被砸,那些還沒有趕來的安保人員,根本就沒露面。
再過五分鐘,勝利區警務司,區防暴隊的人全部趕到,將蘇天南,二毛等人憋在了主樓內。
二毛喘息著衝著一名兄弟問道:“錄完了嗎?”
“錄完了。”對方點頭:“從他們下樓罵人,我就開始錄了。”
二毛擺了擺手:“我出去,我跟他們走。”
話音剛落,那名剛剛被二毛暴打的西裝男,突然鼻孔竄血,渾身抽搐。
龍口區。
顧佰順端著茶杯,坐在辦公椅上,衝著一名中年說道:“礦難的事一出,保龍集團找到了碼工協會,讓章明幫忙聲援。”
“章明怎麼說?”中年問。
“他想聲援啊,賣監管會和保龍集團的人情。”顧佰順起身說道:“但我不這麼看。”
“那你怎麼看?”
“你真正讀懂蘇天御和余明遠的動機了嗎?”顧佰順問。
“不就是討要賠償款嗎?”中年皺眉回道。
“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還有一個原因。”顧佰順笑著說道:“他就是想碰瓷保龍!”
“碰瓷?!”中年驚愕。
“保龍資本越大,辦事越不是人,就越能體現出協會的重要性。”顧佰順扭頭看向窗外:“蘇天御不是要替一個同濟會發聲,他是要替龍城大幾十萬,上百萬工人喊話。”
“可是他現在說不了話啊?保龍已經封死了他所有能發聲的媒體通道。”
“不著急,往後看。”顧佰順搖了搖頭。



![營業悖論[娛樂圈]](/uploads/novel/20240317/9985d76983fd97f0a81dceee3a72fc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