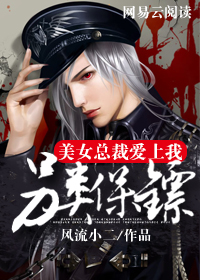此為防盜章蘇晉被人從刑部帶進宮,險些叫這光亮的雪色刺了目。
她已百日不見天光,大牢裡頭暗無天日,充斥著腐朽的屍味。每日都有人被帶走。那些她曾熟悉的,親近的人,一個接一個被處死。
一朝江山易主,青史成書。
身上的囚袍略顯寬大,凜冽的風自袖口灌進來,冷到鑽心刺骨,也就麻木了。
蘇晉抬眼望向宮樓深處,那是朱南羨被囚禁的地方。昔日繁極一時的明華宮如今傾頹不堪,好似一個韶光颯颯的帝王轉瞬便到了朽暮之年。
明華宮走水——看來三日前的傳言是真的。
內侍推開紫極殿門,扯長的音線唱道:“罪臣蘇晉帶到——”
殿上的人驀然回過身來,一身玄衣冠冕,襯出他眉眼間凌厲,森冷的殺伐之氣。
這才是真正的柳朝明。蘇晉覺得好笑,嘆自己初見他時,還在想世間有此君子如玉,亙古未見。
如今又當怎麼稱呼他呢?首輔大人?攝政王?不,他扶持了一個痴人做皇帝,如今,他才是這天下真正的君王。
殿上的龍涎香沾了雪意,凝成霧氣,叫柳朝明看不清殿下跪著的人。
“過來些。”沉默片刻,他吩咐道。
蘇晉沒有動。兩名侍衛上前,將她拖行數步,地上劃出兩道驚心的血痕。
隔得近了,蘇晉便抬起頭,啞聲問道:“明華宮的火,是你放的?”
他沒有作聲,蘇晉又道:“你要燒死他。”
柳朝明這才看見她唇畔悲切的笑意。曾幾何時,那個才名驚絕天下的蘇尚書從來榮辱不驚,寡情薄義,竟也會為一人悲徹至絕望麼。
柳朝明心頭微震,卻咂不出其中滋味。良久,他才道:“你作亂犯上,勾結前朝亂黨,且身為女子,卻假作男子入仕,欺君罔上,罪大惡極,即日流放寧州,永生不得返。”
蘇晉又笑了笑:“不賜我死麼?”
這一生荒腔走板行到末路,不如隨逝者而去。
囚車等在午門之外,她戴上鐐銬,每走一步,鋃鐺之聲驚響天地。
柳朝明看著蘇晉單薄的背影,忽然想起初見她的樣子,是景元二十三年的暮春,風雨連天,她隔著雨簾子朝他打揖,雖是一身素衣落拓,一雙明眸卻如春陽秀麗。
那時柳朝明便覺得她與自己像,一樣的清明自持,一樣的洞若觀火。
他只恨不能將她扼死在仕途伊始,只因幾分探究幾分動容,任由她長成參天大樹,任她與自己分道而馳。
如今她既斷了生念,是再也不能夠原諒他了。
“蘇晉。”柳朝明道,“明華宮的火,是先皇自己放的。”
蘇晉背影一滯。
柳朝明淡淡道:“他還是這麼蠢,兩年前,他拼了命搶來這個皇帝,以為能救你,而今他一把火燒了自己,拱手讓出這個江山,以為能換你的命。”
蘇晉沒有回頭,良久,她啞聲問:“為什麼,要告訴我?”
“你不是問,為何不賜你死麼?”柳朝明道,“如朱南羨所願。”
囚車碾過雪道,很快便沒了蹤跡。
天地又落起雪,雪粒子落了柳朝明滿肩,融入氅衣,可他長久立於雪中,仿佛感覺不到寒冷。
一名年邁的內侍為柳朝明撐起傘,嘆了一聲:“大人這又是何必?”他見慣宮中生死人情,曉得這漩渦中人,不可心軟半分,因為退一步便萬劫不復。
“尚書大人本已了卻生念,大人那般告訴她,怕是要令她置之死地而後生了。蘇大人在朝野勢力盤根錯節,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今聖上又是假作痴傻,若有朝一日,她得以返京,與大人之間,怕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他們相識五載,連殿上的帝王亦如走馬燈一般換了三輪,生死又何妨呢。
“若她還能回來。”柳朝明笑了笑,“我認了。”
蘇晉很小的時候打翻過一個青花瓷瓶。
那是她祖父最珍愛之物,是四十年前,他隨景元帝起兵之時,自淮西一欺世盜名的州尹手中繳獲的第一件珍寶。
景元帝隨手給了他,說:“若有朝一日江山在我之手,當許你半壁。”
她的祖父是當世大儒,胸懷經天緯地之才學,也有洞悉世事之明達。
後來景元帝當真得了江山,曾三拜其為相,祖父或出任二三年,最終致仕歸隱。
蘇晉記得,祖父曾說:“自古君權相權兩相制衡,有人可相交於患難,卻不能共生於榮權,朱景元生性多疑,屠戮成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看來這古今以來的‘相患’要變成‘相禍’了。”
後來果然如她祖父所言,景元帝連誅當朝兩任宰相,廢中書省,勒令後世不再立相。
那場血流漂杵的浩劫牽連復雜,連蘇晉早已致仕的祖父都未曾躲過。
蘇晉記得那一年,當自己躲在屍腐味極重的草垛子裡,外頭的殺戮聲化作變徵之音流入腦海,竟令她回想起青花瓷瓶碎裂的情形。
彼時她怕祖父傷心,花了一日一夜將瓷瓶拼好,祖父看了,眉宇間卻隱有惘然色。
他說:“阿雨,破鏡雖可重圓,裂痕仍在,有些事盡力而為仍不得善果,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蘇晉不知,事到如今,她只明白了祖父眉間的惘然,大約是追憶起若干年前與故友兵馬中原的酣暢淋漓。
舊時光染上微醺色尚能浮現於閑夢之中,醒來時卻不甘不忍昔日視若珍寶的一切竟會墮於這凡俗的榮權之爭焚身自毀。
蘇晉想,祖父之問,她大概要以一生去求一個解,而時至今日,她能做到的,也僅有盡力二字。
朱南羨疾步如飛地把蘇晉帶到離軒轅台最近的耳房,回頭一看,身後不知何時已跟了一大幫子人,見他轉過身來,忙栽蘿蔔似跪了一整屋子。
這耳房是宮前殿宮女的居所,未值事的宮女當先跪了一排,身後是一排內侍,再往後一直到屋外,黑壓壓跪了一片承天門的侍衛,其中有幾人渾身濕透,大概方才跟著他跳了雲集河。
朱南羨輕手輕腳地將蘇晉放在臥榻上,然後對就近一個宮女道:“你,去把你的干淨衣裳拿來,給蘇知事換上。”
那宮女諾諾應了聲:“是。”抬眼看了眼臥榻上那位的八品補子,又道:“可是……”
朱南羨覺得自己腦子裡裝的全是糨糊,當下在臥榻邊坐了,做賊心虛地遮擋住蘇晉的胸領處,又指著宮女身後的小火者道:“錯了,是你,你去找干淨衣裳。”
小火者連忙應了,不稍片刻便捧來一身淺青曳撒。
朱南羨命其將曳撒擱在一旁,咳了一聲道:“好了,你們都退下,本王要……”他咽了口唾沫,“為蘇知事更衣了。”
一屋子人面面相覷,一個也不敢動。
先頭被朱南羨指使去拿衣裳的宮女小心翼翼地道:“稟殿下,殿下乃千金之軀,還是讓奴婢來為蘇知事更衣吧?”
朱南羨肅然看她一眼,拿出十萬分慎重,道:“放肆,你可知男女授受不親?”
宮女噤聲,帶著一屋子女婢退出去了。
正好先頭傳的醫正過來了,見宮女已撤出來,連忙提著藥箱進屋,卻被朱南羨一聲“站住”喝得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好在門檻上跪了。
朱南羨又肅然道:“本王方才說的話,你沒聽見?”
醫正一臉惛懵地望著朱南羨:“回殿下,殿下方才說的是男女授受不親,但微臣這……”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榻上躺著的,大意是他跟蘇晉都是帶把兒的。
朱南羨一呆,心中想,哎,頭疼,這該要本王如何解釋?
思來想去沒個結果,朱南羨只好咳了一聲,更加肅然地道:“大膽,本王怎麼說,你便怎麼做,都是男的就可以不分彼此上手上腳了麼,趕緊滾出去。”
此話一出,醫正連忙磕了個頭,與一幫子仍跪在地上尚以為能上手上腳的內侍一齊退了出去,臨到耳房外時還聽到朱南羨慎之又慎地再交代了一句:“把門帶上。”
醫正連忙將門掩得嚴嚴實實,忍了忍實在忍不住,對垂手立於一旁眼觀鼻鼻觀心的宮前殿內侍總管說:“張公公,十三殿下這是……”
張公公一臉晦氣地看了他一眼。
醫正一驚,一手往耳房指了指,又壓低聲音道:“可老夫聽說,這榻上躺著的是京師衙門的一名知事啊。”
張公公一臉晦氣地點了點頭。
醫正的下巴像是脫了臼,再問:“殿下樣貌堂堂,品性純良,怎麼、怎麼染上這一口了?”
張公公一臉晦氣地說:“怎麼染上的且不提,要論就先論陛下與太子爺殿下知不知道這回事兒,若知道還好,要是本來不知道今日又知道了,且曉得您與雜家為這榻上這位瞧了病,廢了心,蔣大人還是想想咱們這胳膊腦袋腿兒還能余幾條吧。”
醫正聽了這話,淚珠子直在眼眶裡打轉,心一橫眼一閉,覺得不如撞死得了,當下就往門框上磕過去。
誰知腦門沒觸到門框,門便從裡頭被拉開了,醫正一個失穩,倒蔥似栽到了朱南羨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