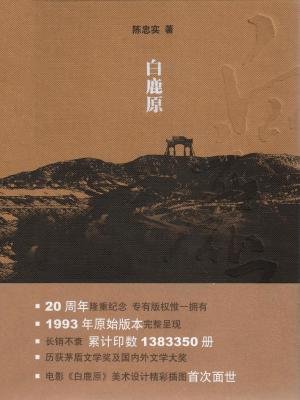鹿三早已取掉了葦席下鋪墊的麥草,土坯炕面上鋪著被汗漬浸潤得油光的葦席,散發著一股類似馬尿的汗腥味兒。他枕著鹿三的被卷,被卷裡也散發著類似馬尿的男人的腥膻氣息。他又想起老人們常說的雞毛傳帖殺賊人的事。一道插著白色翎毛的傳帖在白鹿原的鄉村裡秘密傳遞,按著約定的時間,各個村莊的男人一齊湧向幾個賊人聚居的村莊,把行將就木的耄耋和褯子裹包著的嬰兒全部殺死。房子燒了,牛馬剝了煮了,糧食也燒了,賊人占有的土地,經過對調的辦法,按村按戶分配給臨近的村莊,作為各村祠堂裡的官地,租賃出去,收來的租子作為祭祀祖宗的用項開銷……
騾馬已經臥圈,黃牛靜靜地扯著脖子倒沫兒,粗大的食管不斷有吞下的草料返還上來,倒嚼的聲音很響,像萬千只腳在鄉村土路上奔跑時的踢踏聲,更像是夏季裡突然卷起的暴風。白嘉軒沉靜下來以後,就覺得那踢踏聲令人鼓舞,令人神往了。
白嘉軒後來引為終生遺憾的是沒有聽到萬人湧動時的踢踏聲。四月初八在期待中到來。初七日夜裡,白嘉軒一宿未曾合眼。他把那個白銅水煙壺端到鹿三的馬號裡,倆人坐著抽了一夜煙。天剛麻明,鹿子霖領著田福賢堵在門口。田福賢說:“嘉軒,趕快敲鑼!給大聲吆喝,一律不要上縣,不要聽逆賊煽動。”白嘉軒冷冷地說:“那鑼我不敢敲。”田福賢說:“你是官人又是族長,怎不敢敲?”白嘉軒說:“傳帖上寫的明明白白,誰不去縣府交農具,誰阻撓去交農具,一律砸鍋燒房。我不敢。我怕砸了鍋燒了房。”田福賢說:“誰敢!真的有誰燒了你的房,我讓誰給你賠!”白嘉軒蔑視地說:“你吹啥哩!傳帖連縣長都敢反敢弄,誰把你個總鄉約當啥!”田福賢的臉臊紅了。鹿子霖也覺得被輕視了不大自在。白嘉軒說:“鑼和鑼槌在祠堂放著,要敲你們去敲。我今日個不敲。”這當兒村裡傳來三聲驚天動地的銃響,臨近村子也連續響起銃子的轟鳴。白鹿村一片開門關門門板磕碰的劈啪聲,雜亂無章的腳步聲在清晨寂靜的村巷裡回響,一個個扛著犁杖,夾著權耙掃帚的男人,在蛋青色的晨光裡躍進,匆匆朝村子北邊的道路奔去。白嘉軒站在門外的場地上說:“決堤洪水,怎麼掩擋?誰這會敲鑼阻擋……非把他捶成肉坨兒不可!”田福賢煞白著臉:“硬擋擋不住,咱們好言相勸或許可以?走吧!”白嘉軒推諉不過,跟著鹿子霖和田福賢在村巷轉著。村裡已經變成女人的世界,沒有一個成年男人了。沒有男人的村巷就顯出一種空虛和脆弱。白嘉軒心急如焚,那些被傳帖煽動起來的農人肯定已經彙集到三官廟了,而煽動他們的頭兒卻拔不出腳來,賀家兄弟一怒之下還不帶領眾人來把他砸成肉坨!白嘉軒情急之下就拉下臉說:“二位忙你們的公務,我失陪了。”說罷就走。田福賢跑上前來堵住說:“嘉軒,實話實說吧!有人向縣府告密,說你是起事的頭兒。我給史縣長拍了胸膛,說你絕對不會弄這號作亂的事。既然擋不住也勸不下,讓他們去吧!你可萬萬去不得。”鹿子霖則笑嘻嘻地說:“我根本不信嘉軒哥會跟那些人在一塊鬧事。走走走!嘉軒哥,到你屋裡坐下,讓嫂子給咱沏一壺茶。”
白嘉軒再也找不出借口,就硬著頭皮回到屋裡,心裡只希望賀氏兄弟領頭進縣城交農器了。但他尚不知,賀氏兄弟跟他一樣,此刻也被田福賢安排的幾位官員和紳士纏住而不得出門。這原是史縣長的精心安排。
時勢和機運卻促成了鹿三人生歷程中的一次壯舉。他扛著一架沒有安裝鐵鏵的犁杖,走出白鹿村就擁入從各個村子湧出的莊稼人當中,同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打起招呼。人往往就這樣,一個人的時候是一種樣子,好多人彙聚到一起又完全變成另一種樣子。臨近三官廟,從四面八方通三官廟的大道小路上,人群彙成一股股黑壓壓的洪流。三官廟小小的庭院早已擠得水泄不通,門外的場地上也擁擠著人群,齊腰高的麥子被踏倒在地,踩踏成爛泥的青苗散發著一股清幽幽的香氣。鹿三剛停住腳就聽到了一個可怖的流言,說起事的人被嚇破了膽不敢出頭了!又說起事的人收受了史縣長的賞金被收買了!最可怕的是說不願意收受賄賂的兩個頭兒被史縣長抓走了,現在正捆綁在城牆上示眾!誰也無法證實,因而也無法辨別其虛實,但舉事的頭目沒有出面卻是既成的事實。隨之最粗野的不堪入耳的咒罵不再對著收印章稅的史縣長,而是集中到雞毛傳帖的起事人頭上,但至今誰也搞不清究竟是那個村的張三李四王麻子煽起了這場事件。於是,紛亂而憤怒的莊稼漢們哄哄嚷叫著要去懲治起事的人。人群開始騷亂,朝來時的大道小路上倒流。鹿三心裡急得像火燒,卻終究束手無策。
這時候,從三官廟的院牆裡突然傳出了歡呼聲:“起事的人出頭露面了!”消息像風一樣卷過去,倒流的人又從大道小路上折回來。鹿三看見人群從三官廟的大門裡流水一樣湧泄出來,農具被踩斷的哢嚓聲,夾雜著被踩倒的人的慘叫,圍牆上不斷有人翻跳下來。一伙人架著一個光頭禿腦的和尚從廟門裡卷到場地中間。和尚踩著兩個人的肩膀,左手扶著舉到空中的一把木叉,右手在空中大幅度揮舞著那只插著白色翎毛的傳帖:“苛政猛於虎!灰狼啖肉,白狼吮血……”和尚有一副好嗓門兒,朗誦起傳帖,嗓音洪亮,抑揚頓挫,感情熾烈:“貪官不道,天怒人怨,黎民百姓無計無路,罷種罷收……”眾人鴉雀無聲。鹿三忽然羨慕起和尚來了。和尚誦完傳帖說:“我一人孤掌難鳴。各位父老再舉薦三個頭兒,帶領眾人進城交農具去!有哪位好漢自告奮勇站出來更好……”鹿三聽了大叫一聲:“白鹿村鹿三算一個!”話音未落,他立即被身旁的人抬了起來。鹿三站在陌生人的肩膀上,高高地俯視著烏壓壓的一片黑腦袋,忽然覺得自己不是鹿三而是白嘉軒了。直到死亡,鹿三都沒有想透,怎麼會產生那樣奇怪那樣荒唐的感覺。眾人又推舉出兩個人來,和尚隨之宣布包括自己在內的四個頭目為東西南北四路領頭兒。和尚吼道:“東原的人進東門,西原的人進西門,南原的人進南門,北原的人進北門。史縣長不收回成令,誓不回原。”嗷嗷嗷的吼聲混合著咒罵,人流像洪水一樣滾向縣城,土路上揚起滾滾黃塵,大道兩旁的麥子被踩踏得像牛嚼過的殘渣。
鹿三趕到城牆下,城門已經關死,吼聲震天。幾十個人抱著一根木頭撞擊大門,門板被撞碎,卻發現裡頭已經用磚封死了。鹿三喊著拆牆扒磚。人擁人擠,效率極低,有人把扒下的磚頭擲進城牆裡去,有的磚頭掉下來砸破了自己人的腦袋。這時候,城牆上響起鑼聲,一個人敲著鑼喊:“縣長向大家見禮!”一伙隨員簇擁著史縣長出現在城牆上,縣長跪下了,作揖叩頭。打鑼的人大聲宣布:“史縣長令,收蓋印章稅的通令作廢。請父老兄弟回鄉。”磚頭飛上城牆,縣長的隨員們耍雜技似的凌空逮住磚塊,保護著縣長。史縣長又帶著隨員們跟著敲鑼的人順城牆走了。鹿三倒不知該怎麼辦了,憋在胸間的怒氣尚未完全爆發釋放出來卻已宣告完結。沒有經過多少周折而順利地達到目的取得勝利,反倒使人覺得意猶未盡不大過癮。圍在城牆下的人立即把矛頭回轉過來,紛紛吼喊著現在該當實踐傳帖上的戒律,立即懲治那些沒有前來交農具的人,罵他們不冒風險而分享鬥爭的勝利果實比死(史)人更可憎。鹿三順從了眾人的意向,回原路上所過的村莊,凡是沒有參與交農的人家都受到嚴厲的懲罰,鍋碗被砸成碎片,房子被揭瓦搗爛(本應燒掉,只是怕殃及鄰舍而沒有點火)。有兩家鄉性惡劣的財東紳士也遭到同樣的懲治。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軒在街門口迎接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
四月十三日,白鹿鎮上貼出兩張布告,一張是罷免史維華滋水縣長的命令,同時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布告是由省府張總督親自簽署的。白鹿鎮逢集,圍觀的人津津樂道,走了一個死(史)人,換了一個活(何)人;死的到死也沒維持(維華)得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還難說。白鹿原人幽默的天性得到了一次絕好的表演機會。並貼的另一張布告的內容就不大妙了,那是逮捕拘押鬧事主犯的告示,其中包括鹿三在內的領頭進城的四個人,還有寫傳帖的徐先生,煽動起事的賀氏兄弟。圍觀的人看罷第二張告示的觀感是,摔了一場平跤。
白嘉軒比起事以前更難受。一個最沉重的憂慮果然被傳言證實了:他的起事人的身分早已不是秘密,而他幸免於坐牢的原因是他花錢買通了縣府;說他一看事情不妙就把責任推到那七個人身上,還說他的姐夫朱先生的大臉面在縣裡楦著,等等。白嘉軒從早到晚陰沉著臉,明知棗芽發了卻不去播種棉花。他走了一趟賀家,又走了一趟徐先生家,他對他們的苦楚的家人並不表示特別的熱情,只是冷冷地重復著同一句話:“我馬上到縣府去投案,我一定把他們換回來。”他對哭哭啼啼的鹿三的女人說:“三嫂,你甭急,我要是救不下三哥就不來見你。”
白嘉軒第二天一早就起身奔縣府。縣府裡的一位年輕的白面書生對他說:“交農事件已經平息。余下的事由法院處理,你有事去法院說。”白嘉軒放下褡褳,掏出一條細麻繩說:“我是交農的起事人。你們搞錯了人。你們把我捆了讓我去坐監。”白面書生先是一愣,隨之就耐心地解釋:“交農事件沒有錯。”白嘉軒吃了一驚,又覺得抓住了對方的漏洞:“沒錯為啥抓人?”白面書生笑著向他解釋:“而今反正了,革命了,你知道吧!而今是革命政府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允許人民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已經不是專制獨裁的封建統治了。交農事件是合乎憲法的示威游行,不犯法的。那七個人只是要對燒房子砸鍋碗負責任。你明白了嗎?快把麻繩裝到褡褳去。你要還不明白,你去法院說吧!”白嘉軒不是不明白,而是愈加糊塗。他又去找了法院,又掏出麻繩來要法院的人綁他去坐監獄。法院的人說了與白面書生意思相同的話,宣傳了一番新政府的民主精神,只是口吻嚴厲得多:“你開什麼玩笑!快把你的麻繩收拾起來。誰犯了法抓誰,誰不犯法想坐監也進不來。快走快走!再不走就是無理取鬧,破壞革命機關秩序。”白嘉軒收拾了麻繩,背起褡褳出了法院,就朝縣城西邊走來,決定去找姐夫朱先生想辦法。
第二天微明,白嘉軒又背著褡褳走下白鹿原,胸口的內衫口袋裡裝著姐夫朱先生寫給張總督的一封短信。總督府門前比縣府嚴密得多,荷槍實彈的衛兵睜眼不認人。白嘉軒情急之中就掏出姐夫的信來。衛兵們幾乎無人不曉朱先生勸退二十萬清軍的壯舉,於是放他進去。一位中年人接了信說:“張總督不在。信我給你親交。你回吧。”白嘉軒說:“我要等見張總督。”中年人說:“你等不住。總督不在城裡。你有事給我說。”白嘉軒把抓人的事說了,並帶著威脅的口吻說:“要是不放人,我就碰死到大門上。”中年人笑說:“碰死你十個也不頂啥,該放的放,不該放的還得押著。你快走,我還忙著。”白嘉軒急了:“不是我姐夫勸退方巡撫,你多半都成了亂葬墳裡的野鬼!你們現在官兒坐穩了,用不著人了是不是?”中年人笑了,並不反感他的措辭,反倒誠懇地說:“旁人的事權且忘了,朱先生的事怎麼能忘?你回吧!要是七天裡不見動靜,你再來。”白嘉軒當晚就宿在皮匠二姐夫家裡。
搭救和尚出獄費盡了周折。法院院長直言不諱地述說為難:“燒了人家房,砸了人家鍋,總得有一個人背罪吧?”白嘉軒說:“辦法你總比我多!”他不惜破費,抱定一個主意,用錢買也得把和尚買出來。徐先生把他的俸銀捐贈出來。賀家兄弟也送來了銀元。三官廟的老和尚胸膛上掛著“救吾弟子”的紙牌,到原上的各個村莊去化緣,把零碎小錢兌成大錢銀元,交給嘉軒。白嘉軒把鐺鐺響著的銀元送到法院院長的太太手裡,院長果然想出了釋放和尚的辦法。和尚釋放了。白嘉軒小有不悅的是,和尚獲釋後,既沒有向搭救他出獄的他表示謝意,也沒有向為他化緣集資的老和尚辭謝。他沒有再回到原上的三官廟,去向不知。和尚成了一個謎。這時候,有人說和尚原先在西府犯了奸,才逃到白鹿原上來的,進三官廟不過是為了逃躲官府的追緝罷了;又有人說他原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在白嘉軒看來,這些已經無需追究,更無需核實,因為搭救他們出獄的總體目的已經達到,至於他還當不當和尚,卻是微不足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