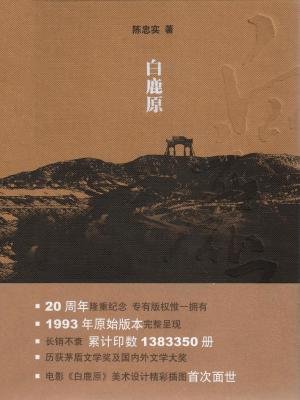“交農”事件經人們百次千次不厭其煩地議論過,終於淡漠下來了。有關白狼的嘈傳中止了,卻隨著又傳開了天狗的叫聲。傳說白狼原先在哪兒出現過,天狗的叫聲就在哪兒響起。聽到過天狗叫聲的人還嘬起嘴模仿著:“溜溜溜——溜溜溜。”細細的尖尖的叫聲與莊戶人養的柴狗汪汪汪的叫聲大相徑庭,一般人即使聽到“溜溜溜”的叫聲,也不會與狗的叫聲聯系起來。而狗們是能聽懂的,每當它們聽到“溜溜溜”的叫聲,就像聽到號角,得到命令一樣瘋狂地咬起來,整個村子,甚至相鄰的幾個村子的狗都一齊咬起來,白狼就不敢進宅跳圈了。
白鹿原又恢復了素有的生活秩序。牛拉著箍著一圈生鐵的大木輪子牛車嘎吱嘎吱碾過轍印深陷的土路,邁著不慌不急的步子,在田地和村莊之間悠然往還,冬天和春天載著沉重的糞肥從場院送到田裡,夏天和秋天又把收下的麥捆或谷穗從田地裡運回場院。白嘉軒也很快把精力轉移到家事和族事的整飭中來。
在鬧“交農”事件的前後一年多時間裡,《鄉約》的條文松弛了,村裡竟出現了賭窩,窩主就是莊場的白興兒。抽吸鴉片的人也多了,其中兩個煙鬼已經吸得傾家蕩產,女人引著孩子到處去乞討。他敲響了大鑼,所有男人都集中到祠堂裡來,從來也沒有資格進入祠堂的白興兒和那一伙子賭徒也被專意叫來。那兩個煙鬼喪魂落魄的醜態已無法掩飾,張著口流著涎水,溜肩歪胯站在人背後。白嘉軒點燃了蠟燭,插上了紫香,讓徐先生念了一些《鄉約》的條文和戒律。白嘉軒說:“賭錢擲骰子的人毛病害在手上,抽大煙的人毛病害在嘴上;手上有毛病的咱們來給他治手,嘴上有毛病的咱們就給他治嘴。”白嘉軒先叫了白興兒的名字。白興兒“撲通”一聲跪到祠堂供桌前:“我不賭了,我再不賭了!我再賭錢擲骰子就斫掉我的手腕子!”白嘉軒說:“起來起來!跟我來——”白嘉軒把白興兒叫到祠堂院子的槐樹下,“背過身子舉起手!”白興兒背靠著槐樹舉起雙手,人們清清楚楚看見了白興兒那手指間的鴨蹼一樣的皮,白興兒平時總是把手藏在衣襟下邊羞於露醜。白嘉軒又連著點出七個人的名字,有白姓的也有鹿姓的,有年輕的也有中老年的,一律背靠槐樹舉起了雙手。白嘉軒著人用一條麻繩把那八雙手捆綁在槐樹上,然後又著人用干棗刺刷子抽打,八個人的粗的細的嗓門就一齊哭叫起來。白嘉軒問:“說!各人都說出自個贏了多少輸了多少。”白興兒和那七個人都哭泣著聲如實報了數。白嘉軒默默算計一番,贏的和輸的數目大致吻合,可以證明他們尚未說謊,就說:“輸了錢的留下,贏了錢的回去取錢。”白興兒和另兩個贏主兒被解下手,然後跑回家取了錢又跑來,按族長的眼色把銀元掏出來放到桌子上。白嘉軒說:“誰輸了多少就取多少。”那五個輸家被解下來,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失財復得的事,顫巍巍地從桌子上碼數了銀元,顧不得被刺刷打得血淋淋的手疼,便趴在地上叩頭:“嘉軒爺(叔哥)我再也不……”白嘉軒卻冷著臉呵斥道:“起來起來!你們八個人這下記住了沒?記住了?誰敢信啊!把鍋抬過來——”幾個人把一只大鐵鍋抬來了,鍋裡是剛剛架著硬柴燒滾的開水。白嘉軒說:“誰說記下了就把手塞進去,我才信。”幾個輸家咬咬牙就把手插進滾水裡,當即被燙得跳著腳甩著手在院子裡打轉轉。白興兒和兩個贏家也把手插進滾水鍋裡,直燙得叫爸叫爺叫媽不迭。白嘉軒說:“我說一句,你們再記不下再賭的話,下回就不是滾水而是煎油!”
接著兩個煙鬼被叫到眾人面前,早已嚇得抖索不止了。白嘉軒用十分委婉的口氣問:“你倆的屋裡人和娃娃呢?”倆人吭哧半晌,耷拉著腦袋囁囁嚅嚅地說,“回娘家去了!”“要……要飯去了!”白嘉軒皺著眉頭,痛苦不堪地說:“一個引著娃娃回娘家去了,一個引著娃娃沿街乞討去了。你倆想想,一個出嫁的女人引著娃娃回娘家混飯吃是啥味氣?一個年輕女人引著娃娃日裡蹭人家門框夜裡睡廟台子是啥味氣?”白嘉軒說到這兒已經動心傷情,眼角潤濕,聲音哽咽了。眾人鴉雀無聲,有軟心腸的人也開始抽泣抹淚。白嘉軒說:“我已經著人把你倆的女人和娃娃找回來了。你們來——”眾人吃驚地看見,兩個年齡相差不多的女人拖著兒女從徐先生的居室裡出來了,羞愧地站在眾人面前。那個討飯的女人衣服破爛,面容憔悴,好多人架不住這種刺激就吼喊起來:“捶死這倆煙鬼!”白嘉軒說:“女人娃娃逢著這號男人這號老子就有遭不盡的罪。我想這兩個女人丟的不光是自個的臉,也丟盡白鹿一村人的臉!我提議把祠堂官地的存糧給她倆一家周濟幾鬥……大家悅意不悅意?”悅意的人先表示了悅意,隨之就數落起煙鬼的無德;不悅意的人先斥責煙鬼的敗家子行徑,隨之就表示根本不該予以同情,但究竟是人數不多。兩個煙鬼羞愧難當,無地自容,跪趴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喊說:“族長,你用棗刺刷子抽我這號不要臉的東西!我再要是抽大煙,你就把我下油鍋!”煙鬼們無以數計的丟臉喪德的傳聞使他根本不相信這些誓言,他還沒聽說過有哪一個煙鬼不是強迫而是自覺戒掉了這惡習的。他立時變了臉:“我剛才說了,你倆的毛病害在嘴上,得治嘴。我給你倆買下一服良藥,專治大煙癮。端來——”什麼良藥尚未端進門來,一股令人窒息的惡臭已經傳進祠堂院庭,眾人嘩然,是屎啊!後來,兩個煙鬼果然戒了大煙,也在白鹿村留下了久傳不衰的笑柄。
秋收秋播完畢到地凍上糞前的暖融融的十月小陽春裡,早播的靠茬麥子眼看著忽忽往上躥,莊稼人便用黃牛和青騾套上光場的小石碌碡進行碾壓。麥無二旺,冬旺春不旺。川原上下,在綠蔥蔥的麥田裡,黃牛悠悠,青騾匆匆,間傳著莊稼漢悠揚的“亂彈”腔兒。白嘉軒獨自一人吆喝著青騾在大路南邊的麥田裡轉圈,石碌碡底下不斷發出麥苗被壓折的“吱喳”聲。鹿子霖從大路上折過身踩著麥苗走過來,十月行步不問路,麥子任人踩踏牲畜啃。鹿子霖站在地頭。白嘉軒一圈轉過來,喝住牲畜,就和鹿子霖在地頭蹲下來。鹿子霖說話爽快:“嘉軒哥!我給你還禮報恩來了。”白嘉軒不失莊重地說:“我哪有禮有恩啊!”鹿子霖熱情洋溢地說:“你給咱兆鵬說下一門好親。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何況這是終身大事!”白嘉軒仍然不在意地笑笑。鹿子霖接著說:“冷大哥還有個二閨女,有意許給孝文。我向冷大哥自薦想從中撮合,八字也都掐了,沒麻達。就看你老哥的意思了……”白嘉軒蹲在那裡就啞了口。事情來得太突然。他說:“這事今日頭一回說破,我得先給老人說了……過三五日,我給你見個回話。”
由鹿子霖作媒,把冷先生和白嘉軒聯結成親家的事也辦得同樣順利。當一場凶猛的西北風帶來厚可盈尺的大雪,立即結束了給冬小麥造成春天返青錯覺的小陽春天氣,地凍天寒,凜冽的清晨裡,牛拉著糞車或牛馱著凍干的糞袋,噴著白霧往來於場院和麥田之間。冷先生的二閨女訂親給白家了,不過不是大兒子孝文,而是二兒子孝武。冷先生的大閨女訂給鹿子霖的大兒子鹿兆鵬,白嘉軒覺得自己的大兒子訂冷先生的二閨女有點那個,於是就提出了二兒子孝武。他回給鹿子霖的原話是:“我想給孝文訂娶個大點的閨女。咱屋裡急著用人(不便出口的一層意思是早抱孫子)。冷大哥的二閨女小了點兒。要是八字合,訂給孝武。”鹿子霖急於聯扯這門親事,並不過多思考白嘉軒另外的意思,就說給冷先生。冷先生同意了。
冷先生十分滿意兩個女兒終身大事的安頓。他不是瞅中白鹿兩家的財產,白鹿原上就家當來說,無論白家,無論鹿家,都算不上大富大財東;他喜歡他們的兒子,也崇敬他們的家道德行,都是正正經經的莊稼人;更重要的是出於他在白鹿鎮行醫久遠之計,無論鹿家,無論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難得在這個鎮子上立足;他也許不光憑他的冷峻的眼光看得出,而是憑他冷峻的神經感覺到了,“交農”事件之後白鹿兩家不好愈合的裂痕。他像調配藥方一樣,冷峻地設計而且實施了自己的調合方案,不管白嘉軒或鹿子霖心裡真恨假愛也不要緊,哪怕維持一種表面的和諧親密也是好的。當兩宗親事完成以後,冷先生在一個冬夜,訂了菜,溫了酒,請來了兩個親家,以少有的熱情和感慨說:“不結親是兩家,結了親是一家。我這人話短言缺又不會拐彎,日後咱們無論誰和誰有啥成見,都當面說清,不許窩在肚裡,我是掛面調鹽——有言(鹽)在先。我們仨人,我長幾歲,權且充個大(音讀斫)貨,說幾句老話:我看白鹿村缺不了嘉軒弟,也缺不得子霖弟。你倆人捏合好一好百好。我是欽服你們兩家人的品行,可不是圖地多房寬牛高馬大。白鹿原上只有一個‘仁義’村莊,甭忘了是縣令親自寫的栽的碑……”於是,由“交農”事件造成的白嘉軒和鹿子霖之間的芥蒂,不說化解,總之是被他們自覺自願地深深地掩藏起來了。其實倆人都需要維持這種局面。
交上腊月,縣長何德治騎著馬上了白鹿原,專程來拜謁白嘉軒,自然由白鹿倉總鄉約田福賢和第一保障所鄉約鹿子霖引路作陪。田福賢對何縣長說:“你坐在倉裡喝茶,我讓子霖把他叫來。”何縣長說:“不用。我登門拜訪。馬拴在倉裡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