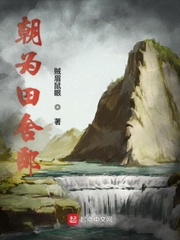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添副碗筷!”
姜采薇聽見喊聲時正盛湯,手一哆嗦險些把碗掉鍋裡,喊的人脾氣急,沒等她拿出去便自己衝進來。她把湯遞上,忍不住感嘆:“真新鮮,起這麼早上班去?”
丁漢白一口喝半碗:“少陰陽怪氣,不上班你養我?”
姜采薇被這小三歲的親外甥噎死,握拳捶對方後背才解氣,而後姜漱柳進來幫腔:“還怪別人陰陽怪氣,自己成天閉著眼請假,文物局局長都沒你得閑。”
丁漢白不欲與這母女般的姐妹抬杠,擠在廚房吃飽就走。好幾天沒上班,他趕早出門,路上買了份奶油蛋糕請清潔阿姨吃,讓人家把辦公室著重打掃一遍。
其實辦公室都是自己打掃,輪流著來,或者誰最年輕就自覺承擔。但丁漢白不行,拿笤帚端簸箕能折他的壽,於是每回輪到他就賄賂樓裡的清潔阿姨。
同事們陸續到了,發現桌上擱著手串,丁漢白說:“前幾天逛古玩市場買的,假的我已經扔了,真的瞎戴著玩兒吧。”
石組長問他:“給張主任沒有?”
丁漢白回答:“沒有,本人不愛巴結領導。”
石組長又氣又樂,瞅他那德行就頭疼,這時張寅拎著包進來,掃一眼大家問了聲早。丁漢白在石組長的眼色中只好起身,拍拍褲子抻抻衣襟,跟著張寅進了主任辦公室。
“歇夠了?”張寅拉開百葉窗,“李館長打電話說漢畫像石修好了,歡迎你去檢查。”
丁漢白沒惦記那茬兒,靜坐聽對方安排最近的工作。末了,張寅問:“玉銷記不是清高麼,怎麼連木頭串子也賣了?”
這顯然誤會了那些手串的來歷,丁漢白卻不解釋,從兜裡掏出自留的一串:“沒辦法,人不能憑清高過日子,但木頭都是上乘的,這串送您。”
張寅沒動:“行了,去忙吧。”
丁漢白狗皮膏藥似的:“瘤疤珠子,一個崩口都沒有,您瞧瞧啊。”
他這番賣力介紹,弄得張寅再也端不住姿態,眼皮一垂欣賞起手串。色澤和密度過了關,張寅拉開抽屜拿紫光手電,看紋看星,看得十分滿意。
“主任,那我先出去了?”丁漢白輕聲問,起身離開,門在身後關上的一刻撇了撇嘴。直到下午,張寅戴著串子已經招搖一圈,忽而得知是玳瑁古玩市場的地攤兒貨,只保真,不保優,氣得他恨不得把丁漢白揪起來打一頓。
三分氣東西,七分氣丁漢白的愚弄。
主任辦公室的門咣當碰上,眾人啞巴般伏案忙碌,石組長累心地滑著椅子靠近:“小丁,你干嗎非跟他對著嗆嗆?”
丁漢白敲著字:“就憑這文物分析表我能做,他做不了,做不了還不閉嘴當鵪鶉,淨點名我家鋪子壞我心情。”
石組長無奈地樂了:“單位這麼多人,懂的人才幾個,是不是?”
丁漢白敲下句號:“不懂沒關系,但我受不了一知半解瞎賣弄,還整天貶損別人,真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
他等著打印機運轉,心說這班上得太沒勁了,還是在家歇著好。
想到家自然又想到紀慎語,紀慎語說送他禮物,他拒絕,紀慎語早上又說回贈個貴重的,他沒抱任何期待,也估計自己不會有任何驚喜。
紀慎語莫名打個噴嚏,立在門當間吸吸鼻子。
關門之際姜采薇從拱門進來,正對上他的目光。“慎語,怎麼沒吃早飯?”姜采薇很惦記他,總給他拿吃的,“頭發這麼潮,洗澡了?”
紀慎語點點頭:“小姨,我這兩天不去客廳吃飯了,幫我跟師父師母說一聲。”見姜采薇好奇,他解釋,“我要做點東西,就不出院了。”
姜采薇驚訝地問:“那也不至於不出門不吃飯呀,是不是身體不舒服,你不好意思講?”
紀慎語感謝對方的體貼:“我怕分心就做不好了,你送我的桃酥還沒吃完,我餓了就在屋裡吃兩塊。”
他哄得姜采薇答應,對方還給他拿了好多零食水果,等人一走,他進屋插上閂,鎖上窗,沒理潮濕的頭發,照例拿出磨砂膏和護手油擦拭。
十指不染纖塵,指腹磨得平滑柔軟,再洗干淨,這准備工作才算完成。紀慎語坐在桌前,工具一字排開,光刀頭就十幾種,甚至還有個老式的小打磨機。桌面中央擺著那堆文物殘片,被分成兩撮,所有掉落的鈣化物和附著物也都被保存放好。
紀慎語挑出一塊破損的碗底,置於紙上,沿邊描畫出輪廓,再就著輪廓從殘片中挑揀,握刀切割,極細致地打磨。
半瓶從揚州帶來的膠候場,分分秒秒,一天晃過去。等到黃昏……等到暖黃的光落盡,只剩下昏黑,那一片終於妥了。不帶丁點繭子的指腹是最好的工具,能測試出任何不夠細膩的手感,紀慎語坐在椅子上數個鐘頭,終於拼好一個碗底。
這就是他不能長繭子的原因,也是他跟隨紀芳許多年學到的東西。
丁漢白曾問他會否修補書,他含糊其辭,其實他會,但修復只是涵蓋其中的一項。准確地說,他學的這一套叫“作偽”。
丁漢白沒回小院,到家後直接在大客廳等著吃晚飯,吃飯時左手邊空著,胳膊肘杵不著人,竟然有些不習慣。飯後陪姜漱柳看電視,他只要老實工作就是他媽眼裡的心肝肉,看個電視又被喂了滿腹的點心。
等到夜深回小院,他見紀慎語的房間關著門,洗個澡回來門仍關著。他索性坐在廊下讀那本《如山如海》,一卷接著一卷,稽古那卷太有趣,翻來覆去地看。
清風幫忙翻書,知了扯嗓子搗亂,丁漢白眼累了,回頭瞅瞅臥室門,咳嗽一聲:“奇了!三伏天居然大風降溫了!”
紀慎語一絲不苟地忙著,靜得如同沒了鼻息。
丁漢白把餌拋出去沒釣上魚,收書准備睡覺,踱步到人家房門口,好奇心伴著燈光蹭蹭往上漲。“紀珍珠,干嗎呢?”他切切地問,“餓不餓啊,咱到廚房熱碗魚羹去?”
紀慎語被擾得無法:“我不餓。”
丁漢白另辟蹊徑:“今天單位發生一件特逗的事兒,開門我給你講講。”
紀慎語說:“我不聽。”
“……”越拒絕越好奇,丁漢白恨不得把門板捅個窟窿,“這本書第四卷有錯誤,把磁州窯講得亂七八糟,你快看看。”
紀慎語不耐煩了:“我不看,你走。”
丁漢白被姜漱柳寶貝了一晚上,此刻立在門外嘗盡人間冷暖,最後生著悶氣走了。睡過一宿,翌日打定主意不搭理紀慎語,誰知出來發現隔壁還關著門。
腳步聲遠了,紀慎語眨動疲憊的雙眼,眼前是初具形態的青瓷瓶,還差瓶頸處沒有完工。他開門去洗漱,不到十分鐘又回來鎖上門,只吃幾口點心,不然飽腹更容易困。
雲來雲去,天陰了。
丁漢白下班路上被淋成落湯雞,奔逃回來直奔臥室,換好衣服才恍然探出身。果然,隔壁仍舊關著門,就算打地道也得出來喝口水,撒泡尿吧?
腳步聲漸近,紀慎語偏著頭磨瓶口,余光瞥見門外的影子。
丁漢白問:“你在裡面造原子/彈呢?”
紀慎語沒抬眼,只笑,丁漢白又問:“說完送禮物就不露面了,後悔?”
紀慎語煩死這人了,深呼吸保持手上動作平穩,丁漢白自覺沒趣,終於走了。他閉關兩天一夜,用拼接法初步完成青瓷瓶,因為瓷片本身就是海洋出水文物,後續加工簡單不少。
他又熬去整宿,將花瓶的紋理痕跡造出來,把刮下的沉積物與苔蘚蟲敷回去,雨一直滴著,他凝神做完數十道工序,在天快亮時已冷得感知不出正常溫度。
丁漢白多加一件外套,默默上班,再沒湊到門口詢問。
人的好奇心有限度,達到峰值便回落,無所謂了。
雨天心懶,辦公室裡沒人忙工作,連張寅也端著水杯無所事事地轉悠。丁漢白立在窗口看景兒,摸一片窗台蔓上來的楓藤,揉搓攔了再扔下去,只留一手的濕綠。
他猜測,丁延壽這會兒在玉銷記看報紙,門可羅雀真可憐。
他又猜測,姜采薇正在辦公室喝熱水,降溫還穿裙子,臭美。
心思最後拐回家,他想到閉門造車的紀慎語,神神秘秘,吊人胃口。
丁漢白沒想錯,家裡門依然閉著,車也造到了最後,紀慎語十指通紅,握刀太久壓癟指腹,浸過藥水明膠傷了皮膚,偏偏他精益求精,不肯有絲毫含糊。
紀慎語萬不可把這事兒告訴別人,家裡是做雕刻的,可這作偽比雕刻費時費力得多,被人知道平添麻煩。而且紀芳許當初倒騰古玩廣交好友,但沒什麼人知道他會這些,因為這是秘而不宣的本事,不是能廣而告之的趣事。
還有一點,紀慎語記得那天去玳瑁古玩市場,丁漢白告訴他會分辨真假,那神情語氣輕松又倨傲,不容置疑一般。要是丁漢白得知他會作偽,他想不出對方會有什麼反應。
琢磨著,斟酌著,紀慎語終於完活兒,雨也恰好停了。
他將青瓷瓶放進櫃子裡陰干,撐著最後一點力氣把桌面清理干淨,沒心思填補肚子,沒精力洗澡換衣服,連開門推窗都提不起勁頭。
三天兩夜不眠不休,繃緊的神思在躺上床那刻松下,紀慎語睡不解衣,急急見了周公。
雨後一冷再冷,晚飯煲了丸子砂鍋,飯後姜漱柳把單盛的一碗熱好,讓丁漢白端給紀慎語吃。丁漢白煩得很,老大不樂意地端出去,走兩步又返回:“把芝麻燒餅也拿上……”
他端著托盤回小院,驚奇地發現燈黑著。“紀珍珠?”他叫,將托盤放廊下,“我媽給你熱了湯,開門吃飯。”
裡面沒動靜,他不想像服務生似的:“擱下了,愛吃不吃。”
丁漢白揚長而去,鑽書房畫畫。畫到深更半夜,前情後事全都忘干淨,回屋睡覺聞見香味兒才清醒,再一看廊下的托盤,合著東西一直沒動?!
他徑自衝到門外,大力敲門:“開門,我還不信了,這是你家還是我家?”
敲了半晌,裡面毫無反應,丁漢白收手一頓,驀然發慌。裡面不會出什麼事兒了吧?紀慎語不會有什麼遺傳心髒病,死裡面了吧?
“紀珍珠!”他大吼一聲,抬腳奮力一踹,門洞開後衝進去,聞見一股藥水的酸味兒……打開燈,房間整潔,平穩的呼吸聲從床上傳來。
紀慎語縮成一團,顯而易見的冷。
“真他媽……神秘。”丁漢白走到床邊,扯開被子給對方蓋上,這才發現紀慎語沒換睡衣,髒著臉,眼下烏青面頰消瘦,雙手斑駁帶著印子。
他擰濕毛巾在床邊坐下,撩了滿掌細軟發絲,順著額頭給紀慎語擦臉。下手太沒輕重,鬼吼鬼叫都沒把人吵醒,竟然把人給擦醒了。
紀慎語臉皮通紅,疼得齜牙:“我不敢了……”
丁漢白停手:“不敢什麼了?”
紀慎語合著眼迷糊道:“不敢偷吃了。”
原來把丁漢白當成了紀芳許的老婆,還以為那疼勁兒是挨了一耳光。“師母給你擦擦。”丁漢白氣得變聲,又胡亂蹭了蹭,然後給紀慎語擦手。
謹小慎微,總怕稍一用力會把那指頭擦破,丁漢白端詳,尋思這手是干了什麼變成這樣?良久一抬眼,竟發現紀慎語明明白白地醒了。
正茫然地,靜悄悄地看他。
丁漢白擱下那只手:“你餓不餓?”
看對方點頭,他又說:“我給你變個魔術。”
紀慎語閉眼聽見丁漢白起身,聽見腳步聲離開臥室,復又返回。等丁漢白讓他睜開眼,他看見床頭放著一碗丸子湯,還有倆燒餅。
丁漢白回去睡了,什麼都沒問。
雨又下起來,紀慎語恍惚忘記了揚州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