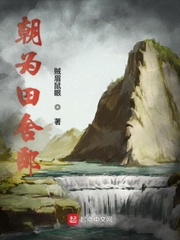第16章
明鏡拿起電話,搖了搖。“對,我要船務公司,請閔經理聽電話,我是明氏企業的董事長。”明鏡道,“我的航運單上,那兩箱貨,為什麼不讓提貨?”“明董事長,是這樣的,您的貨都是醫用品,光是醫用面紗就是禁止買賣的。您以前有海關總署的批條,我們見條子放行,現如今海關總署的批條不管用了,要加蓋特務委員會的公章,才能放行。”明鏡急道:“閔經理,不能通融嗎?我們也是熟客了……”閔經理抱歉道:“這個真不行,我們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權。”明鏡繼續爭取道:“閔經理,您看這樣行不行?我加一層運費給您……”“那可不敢,於今掙錢事小,被發現要坐牢,吃槍子的。”閔經理堅持,“其實,話說回來,您明董事長要蓋個特務委員會的章,還不簡單。”“什麼意思?”“喲,您沒看報紙嗎?令弟高升了。”明鏡不再說話,沉著一張臉慢慢放下電話,把扔在茶幾上的報紙又拿起來細看,專選時政版面仔細看起來。“嘩”的一下,報紙被揉成一團,褶皺不堪的報紙上,映著明樓高就汪偽政府要員的照片。同一張報紙,平展地擺在梁仲春的辦公桌上,一個紅色的大大的問號躺在報紙上。汪曼春站在他的辦公桌前,眼睛盯著被問號覆蓋明樓的臉的報紙,問道:“梁先生想告訴我什麼?”“一個多月前,日本軍部即將派遣到上海經濟司任要職的日本經濟學家、法學家原田熊二在香港遇刺。”梁仲春從抽屜裡拿出一份香港的報紙,往前一推,“遇刺那天,明樓就在香港。”“你認為明樓殺了原田熊二?好取而代之?”“你認為呢?”梁仲春反問,“原田熊二死了,對誰最有好處?原田可是日本軍部欽定的新政府經濟司負責人,他要活著,明樓會如此受到各方器重嗎?”“你怎麼知道是明樓殺了他?”“我不知道!”汪曼春冷哼一下,嗤之以鼻。“你看看明樓身邊都是些什麼人,那個品位奢侈,身手矯健,來去無蹤的阿誠。”汪曼春愣了一下。
“把這樣一個人帶在身邊,這可不是什麼學者風範。”“越來越復雜了。”“應該是越來越有趣。”梁仲春吩咐著,“設個套,試一試。”“你利用我。”“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關鍵的問題是,明樓不是情報販子,他更像是一個中間人。我感興趣的是,他的情報會分銷到哪裡?特高課?重慶?蘇聯?延安?美國?”汪曼春反問:“梁先生的直覺呢?”梁仲春想都不想,果斷道:“重慶。”汪曼春冷笑一聲:“我師哥跟周佛海,包括汪主席都是從重慶投誠過來的。”“正因為如此,他的掩護身份非常有效。”汪曼春還是不能接受梁仲春的判斷。“怎麼了?你不接受?就因為他曾經是你的情人?”汪曼春瞪視著:“我不想在工作時間談私人感情。”梁仲春繼續鼓動:“那麼?”“試試他。”汪曼春脫口而出,“我找個人假扮情報販子……”即便堅持了許久,汪曼春的內心防線還是被攻陷。和梁仲春的對峙中,她對明樓即使有情,也挨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戳到心尖上。“可行。”汪曼春鄭重道:“明天我叔父將在上海大酒店舉行一次‘上海金融界’的救市沙龍,我師哥也在被邀請之列,那就……爭取一場即興演出。”梁仲春認同地點了點頭。汪曼春問:“派誰去?”“你想叫誰消失就叫誰去。”汪曼春咀嚼著他話裡的含意,幽幽地道:“真想派你去。”梁仲春笑起來:“對,就這麼簡單。”話一出口,汪曼春心中了然,她喜歡聰明人,對梁仲春有敵意也有敬意。“汪處長,南雲課長雖然是你的老師,可是,她畢竟是日本人。76號是我們自己的地盤,守得住守不住,要看76號的工作效益。”梁仲春說,“明白嗎?”“明白。”“外界總傳說,我們76號二春爭權,我從不辟謠,為什麼?我們要讓日本人對我們76號放心。”汪曼春不置可否。“不過,對共產黨和重慶分子,我們必須見一個殺一個,汪主席才有可能在半壁河山下爭一席之地。”“等我消息。”汪曼春道。
沙龍包間裡,充斥著惺惺作態的表演和虛偽的贊美聲。人們高談闊論,對於經濟、政治、時事,無不論其利弊,活像一個自由的財經沙龍。
“……昨天夜裡,又有新政府的官員遇刺了。”某銀行家嘆道,“太恐怖了。”“世道人心簡直糟透了。刺客橫行,到處都是恐怖主義,抗日分子已然墮落到戰國水平,行此野蠻、下作的血腥勾當。”汪芙蕖回道。“有一句,說一句,日本人的修養是極好的。日本人至少不會從我們的背後開槍吧。日本人講的是武士道精神,講公平決鬥……”一位銀行家慨嘆,“中國的經濟真的是沒有一點希望了。”“我覺得,我們應該替新政府盡快拿出一個詳盡的金融改革方案。”有人建議道。“問題很多。新政府要看政績,通常先看經濟。我們要向新政府提倡經濟至上而不是政治至上。對吧,汪老?”又走過來一位銀行家對汪芙蕖請教道。
“我呢,人老了,膽子也就小了,步子也就慢了。”汪芙蕖呵呵一笑,反問明樓,“明樓,你說說看,現今的經濟題目應該怎麼做?”明樓放下酒杯,細長的眉目在金絲鏡片的籠罩下漾著色澤柔和的光彩,汪曼春痴痴地望著他不曾離去,在她心裡明樓是永遠抹不去的心痛和愛。
“經濟,歷來就是一個既難做又誘人的題目。當前大家矚目的問題,就是新政府會不會推出一系列的金融新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低迷的股市。不過,經濟政策不是靠‘堵’來建設新秩序的,始終要想辦法‘疏通’。戰時經濟蕭條,不僅僅是國內獨有的,國外也是一樣。”明樓分析著,“所以,我個人認為,新政府的金融改革,寧可保守,不宜冒進。”眾人贊賞般地點頭,有人說是高論,有人贊是高明,有人中肯道切題。說完,明樓走到汪曼春身邊,悄悄說道:“我實在受不了這裡的酸腐氣味了,原以為文人堆裡才會有臭氣熏天的酸味,想不到商人堆裡也開始發臭發腐了。”汪曼春笑而不語。“你今天也很奇怪,不是最討厭這種聚會的嗎?”明樓疑惑。“想聽真話?”明樓點點頭。“我就是想來陪陪你。”明樓笑了,笑得很滿足:“我去一趟洗手間……要不要一起去?”汪曼春笑著推了他一下,露出了羞澀的表情。明樓笑著起身離席,隨即,汪曼春下意識地朝座上的一個貌似商人的胖子使了個眼色,胖子立刻也離席而去。明樓站在洗漱台前洗手,他微屈著一膝,腰間皮帶扣銀光耀目,松松地掛著猶未系緊,嘴裡哼著《藍色多瑙河》,看上去心情不錯,伸手把金絲眼鏡摘下來,對鏡子整理著頭發。洗手間的門突然被推開,一個胖乎乎的男子出現在他身後,明樓知道他是在座的一名客人,但他也知道,這個客人是跟汪曼春一起來“蹭”沙龍的。“明先生,您好啊。”胖子熱情打著招呼。明樓應付性地答應了一聲,繼續整理頭發。“明先生,您還記得我吧?”“你是……”明樓奇怪地從鏡子裡看著他。胖子自我介紹:“明長官,我是軍統局戴局長派來的。”明樓恍然,沒有理他。
胖子見他不說話,以為就此搭上了話:“戴局長讓我跟您直接聯系。”說著,順手拿起明樓的眼鏡。
“擱下。”明樓發話了,“弄壞了,你賠不起。”胖子哈哈笑道:“您說,您這副眼鏡除了把您打扮成一個文化人,還能有什麼……”明樓快捷地從眼鏡框上取下一枚鏡片,端詳看了看。見狀,胖子趁勢也低下頭來。明樓一抬手,一個斜插,順勢就把那一枚薄如利刃的鏡片插進了胖子的喉管,動作迅捷有力,准確擊殺。
“它還有一個功能,簡單,實用。”明樓對著胖子的臉說。
男人還沒來得及反應,就側著身倒下,栽倒在明樓的皮鞋尖上,明樓下意識地往後退了一步,以免和屍體相觸。
就在屍體倒下後數秒,洗手間的門被撞開,阿誠衝了進來:“您沒事吧?大哥。”明樓試著甩了一下手,朝地下一指,說:“我的鏡片。”阿誠趕緊從屍體的喉管上拔出鏡片,遞給明樓。明樓拿到水管下衝洗,自言自語道:“好久不練,手生了。”衝洗干淨後,重新裝回到眼鏡框裡,“打掃一下,人家還要做生意。”“是,大哥。”阿誠替明樓打開洗手間的門,待明樓整理完畢後走了出去。西餐桌上,煙霧繚繞,微有咳嗽聲、清痰聲在席間傳播,甚有蔓延的趨勢。明樓氣定神閑地回到座位上,對汪曼春報以微笑。“怎麼去了這麼久?碰見熟人了嗎?”汪曼春有意旁敲側擊。明樓喝了一口酒,濃且勁的酒香在齒間散發出來,滿口蘭馨:“我在洗手間碰到一條‘瘋狗’,差點咬到我。”汪曼春心裡一緊:“而後呢?”“而後啊?”明台看了看她,“我給了他一個教訓。”汪曼春頓時顯得心神不寧,想前去探視一下。她的身子微微前傾,還沒有明顯的動作,明樓開口讓她坐著別動,聲音很輕,卻很有力度。
汪曼春神色詫異地坐穩。“汪大小姐什麼時候想改行做清潔工了?”明樓低低地淺笑,並於這淺笑中生出一絲惋惜之意。
汪曼春忽然間不寒而栗,且自慚形穢。她佩服眼前這個男人,這個曾經讓自己魂牽夢縈、自殘自殺的男人。五年過去了,他的那雙深瞳依然深似海洋,不可捉摸。
“師哥,你難道隨身戴著一副透視鏡嗎?”汪曼春半帶嬌嗔地試探著。
“知道什麼是潛意識嗎?”明樓說,“你的潛意識一直在誘導你工作,你聰明的小腦袋裡裝的是對每一個企圖進入新政府的人進行身份甄別。”汪曼春頓時啞口無言。“你要甄別,我不反對,至少你得派一個人來,你喊一條狗來萬一咬到我怎麼辦?”明樓雙眉一展,清瘦的面頰上沾了些紅暈,大約是紅酒的點染,或者是攻心的刺激作祟,“你是聰明女子,要學會識人用人收放自如,你身邊得有一群得力的幫手,而不是一群只會狂吠的狗。你要明白要進攻、要開戰,你得先學會維持雙方的‘均勢’,才會有機會獲取優勢。”汪曼春眼眶忽然濕潤起來,倒不是委屈,而是心懷畏懼。她欲開口講話,明樓像是事先洞悉了一切,闔攏了眼皮,把耳朵伸過去,肩頭斜靠著她,一副恭聽佳人教誨的模樣。
汪曼春低頭:“我錯了,師哥……”明樓笑起來,整個身子瞬間扶正,他將食指和中指並攏,壓在唇邊,嘴角依舊掛著神秘莫測的笑意,“噓”了一聲,溫情脈脈地說:“點到為止,點到為止。”兩人看似親昵的舉動,汪芙蕖看在眼裡,臉上露出溫馨的笑容,略微咳嗽了一聲,問道:“你們在說什麼有趣的事情?”明樓抬起頭,扶了扶眼鏡框:“曼春在向我認錯呢。”“呵呵,難得,實在難得。”汪芙蕖顯得很高興,“我們家曼春這匹小野馬,從小到大也只有你明大少爺能夠拉住韁繩。可惜啊,當年要不是你大姐反對,你們現在早就……”汪芙蕖話音未落,一聲具有穿透性的清寒有力的聲音果決地傳入耳廓,衝擊著耳膜:“當年要不是我反對,汪家大小姐現在已經是明家大兒媳婦了,對嗎?”明樓倏地推椅而起,順手將搭在膝上的餐巾擱置在餐桌上,站得筆直。他知道,明鏡來了。阿誠幾乎是在同時從外面跟著明鏡進來的,看情形很顯然,阿誠是設法阻攔而絕無用處的。汪芙蕖等人素來知道他明家規矩重,所以,整個沙龍頓時鴉雀無聲。只有汪曼春一口惡氣壓在胸口上,目中無人地側著臉。阿誠站在一邊,大氣不敢出。
明鏡穿著一件真絲緞面的粉底藍湘繡旗袍,高領低擺,袍身緊窄修長,胸前繡有清寒淡雅的白玉蘭花。熠熠閃光的水晶燈下,襯映著一張端莊持重的臉。一個尚未年滿四十的女人,盡管修飾得當,眼角處也還是隱約能看到細細的皺紋。
明樓站在明鏡跟前,低低地喊了一聲:“大姐。”明鏡沒應聲,眼光很快掃過明樓,落在汪芙蕖的身上。“大侄女,火氣不要這麼旺,畢竟時過境遷,大家還是一團和氣的好。”汪芙蕖滿臉堆笑,臉上的肥肉顫了顫,笑得太假,以至於汪曼春都有些看不下去。明鏡卻不事寒暄,單刀直入地對汪芙蕖道:“汪董事長,不,新任南京政府財政司汪副司長,我是專程過來跟您請安的。”“不敢當,不敢當。”“順帶告訴您一聲,您不必三天兩頭叫人拿著企劃書、合作書來敲我的門。您可別忘了。我父親死的時候,留有家訓,我明家三世不與你汪家結盟、結親、結友鄰。”此話一出,汪芙蕖的臉色頓現尷尬。“還有,您可以無視從前的罪惡……”“大姐。”明樓試圖截住明鏡的話。
明鏡頭也不回地冷著臉:“不准打斷我的話!”她對著汪芙蕖,繼續道,“千萬別再打我們明家人的主意。我明鏡十七歲接管明家的生意,多少次死裡求生活過來的!我什麼都不怕!”汪芙蕖的臉色灰蒙蒙的,被明鏡懟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你們南京政府,隨隨便便就給我扣上一頂帽子,說我是紅色資本家。好啊,想整垮我,吞掉明氏集團,你們拿出證據來。別像跳梁小醜一樣,給我寄子彈!”說著,從挎包裡拿出兩顆子彈,“啪”地一聲擲在餐桌上,子彈被振動得似乎要跳起來,汪芙蕖嚇得往回抽了一下。
看著汪芙蕖的臉色,汪曼春覺得太丟臉!想站起來回擊,又看到明樓似箭的眼光,只好再次忍耐下來。
明鏡轉過身,看著明樓,質問道:“你回上海多久了?”“一個多……”明樓張著嘴還沒說完,明鏡揚手就是一記耳光,把他嘴裡那個“月”字生生打回肚裡去了。汪曼春再也忍不住一聲尖叫,跳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