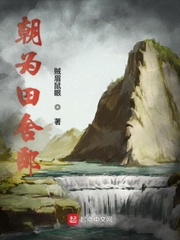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民間如何說起歸一類,文人口中怎樣,又歸一類。蔡太師作宰十余年,有些好事,有些壞事,不過也不是那樣簡簡單單就能評價的。如今朝堂,武臣之首當屬童樞密,而說說到文臣,執天下之望的,不是老夫,也並非李相,而是這位在家中寫字的老太師。老實說,此次北伐若真有什麼問題,我與李相撐不住的話,真壓得住場面的,只有他老人家了。”
吃過晚飯,秦嗣源與寧毅說著話,領著他朝相府後方的園子裡過去,便也順口說起了蔡京。這位作宰十余年的老人,在此時底層的風評並不好,文人當中則毀譽參半,到文官口中,大部分則能夠明白他的地位。秦嗣源也是六十的年紀,說起對方來,仍然要稱其為“老人家”,想來李綱、秦嗣源若被罷,對方恐怕就是第一時間復起穩定局面之人。
好在這次李綱出相,正逢北伐的最好時機,秦嗣源內蘊如海,雖然沒有蔡京作宰十幾年的積累,但也絕非省油的燈,足堪與之比肩。這等狀況,一時半會應該不會出現。
秦嗣源對此也是隨口說起,並無深意。幾名護衛隨行之下,兩人散步到後方花園,秦嗣源叫人拿來圍棋,如在江寧之中一般准備與寧毅對上一局,閑聊幾句之後,老人卻是問起來:“立恆於治國有何看法?”
這問題真是太過正式了,寧毅有點意外,遲疑一下,笑道:“右相大人……有些問道於盲了吧?”
他這句右相大人說得有些古怪,秦嗣源笑了起來,也是在說話間,有人隨家丁過來,卻是到相府來拜訪的成舟海。與老師行禮之後,秦嗣源揮揮手示意他在旁邊坐下。
“此次北伐,頗多艱難之處,但眼下童樞密已屯兵遼境,與蕭干對峙,常勝軍投誠。遼人在金人的進攻下,節節敗退。若是一切順利,今年之內結束戰事,克復燕雲也是有可能的。仗打完了,接下來就是安置之事……”老人落下棋子,“所以立恆倒也不妨隨便說說嘛。”
“隨便說?”寧毅失笑。
老人笑著點頭:“嗯,隨便說說。”
“好啊,那就隨便說。”寧毅看著棋局,想了想,落下棋子後,揮了揮手:“秦相每天在這裡,看著這城市,看到了什麼?”
此時兩人所處的涼亭在相府後花園的一處假山上,地勢稍高,雖然不可能俯瞰汴梁,但城市裡夜色結成的光芒,那熱鬧的氣息還是能夠感受得到。成舟海往四周看看,秦嗣源笑道:“這個問題有些大了吧?立恆不妨直言。”
“有沒有看到怨氣?”
“嗯?”秦嗣源皺了皺眉,“何出此言?”
“若要說治,便要看到怨氣吧。”寧毅拿著棋子在指尖,手指搓了搓,“這世道之上,每一個人生下來,必然與周圍人發生來往,來往必有碰撞摩擦,大大小小的怨氣,便也由此積累而來。”
“今日與鄰居吵了一架,是怨氣,與別人打了一架,是怨氣,買東西被人騙,是怨氣,無緣無故被人砍了一刀,也是怨氣。告官,官官相護,這裡有怨氣,審案不公,有怨氣……這些怨氣,大大小小的記在心裡,有些可以消彌,有些消彌不了。到死,一筆勾銷,秦相說的治,我覺得往實際一點說,治的就是這怨氣。”
秦嗣源愣了愣,落下棋子:“立恆此言,倒是頗有新意。”
“會說瞎話的不見得會做,我也就是紙上談兵。”寧毅笑笑,繼續說下去:“治怨氣也就兩個方面,教化與司法,教化便是道德、文化、習俗,孔聖人說天地君親師,排個座次,管聖人說,士農工商,列一列重要和不重要,想一想若是一個農民,從未念過書,求的不多,一輩子生活範圍不過一村一鎮,這類人,就算遇上被人欺負,自己覺得平常,晚上就忘了,怨氣便不多。我這樣的,讀了些書,走的地方多些,覺得自己了不起,與人碰撞摩擦也多,誰瞧不起我,我心裡就生氣,這輩子估計怨氣也多……”
他說到這個,秦嗣源與旁邊聽著的成舟海都笑了起來。寧毅接著笑道:“這世道上,道德水准好些,彼此有禮,都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該做,摩擦便少些,產生怨氣的機會也就少些。人因受到的教育程度不同,明理的程度也不同,而且人對自己的定位不一樣,遇上不同的事情,產生怨氣的可能性也不一樣,書生會因為旁人的不重視而生氣,老農便不會。”
“文化與習俗告訴每個人,你在這裡是個什麼位置,應該得到的尊重有哪些,道德使這社會得以潤滑,你回到家,鄉鄰和睦,兄友弟恭,妻子溫婉善良,這些東西,都會讓怨氣得以緩解。而司法,是最後解決的手段了。”
寧毅落下棋子:“我與成兄起了摩擦,產生怨氣,解決不了,怎麼都不舒服,那就只能告官了。司法若得人信任,官府照章辦事,公正嚴明,上方一判,他與我都心服口服,怨氣便得以消解。可若司法不能公正,世上人都覺得官官相護,律法無用,我與成兄,去報官,首先想的,是到處找關系,到頭來,他的關系或許能壓我,但我趨避一時,心中怨氣仍然不能解除。而他財雄勢大,就算我一時服了,他仍然會覺得我這人竟敢招惹他,定要讓我後悔,甚至連他心中的怨氣,都無法消除。那司法也就成笑話了。”
他搖了搖頭:“這怨氣一時半會沒有什麼事,但人一輩子,發生過的事情,都會記得,慢慢的怨氣加劇,若在死前怨氣太多……人就要殺人,就要造反,有的人不敢,但他更容易被他人煽動,更容易成為禍害,人們性情怪異,彼此之間再無人情信任可言。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總是要消除這怨氣,令其……症狀更輕,人數更少,世道也就更好。”
他說完這話,秦嗣源與成舟海沉默了片刻,成舟海笑道:“照如此說來,豈非不行教化之世是最好的?大家都是農民,沒有讀書人,便沒有怨氣了……”
“但人性追求更好。”寧毅笑了笑,“你追求吃得飽,追求穿得好,吃飽穿好之後想要有個姑娘,有姑娘以後想要傳宗接代,中間也還想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言自明的,社會發展,要消彌怨氣,使其不至於崩潰,消彌怨氣也是為了讓社會走得更穩,只是說治這一項,應該是以消彌怨氣為中心原則,治療與發展是並行的。發展這東西,擋不住,就好像變法一樣……”
他頓了頓:“歷朝歷代,每一次變法,不是什麼聰明人想到了好辦法,所以推動了這世道。而是世道發展,到了關卡處,才有人出來推行變化,因為大家看到,必須要變了。自商鞅變法開始,推行教化,讀書人漸漸增加,想往上走的人,越來越多,他們若走不了,怨氣就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就得推行一種新的方法,使所有人都有個盼頭,每一次變法的目的,調整朝堂、社會結構的目的,大都是如此,有人不滿,便要讓他們滿意而已。世上之法,從來是人們有用了,才會出現,而並非它出現了,人們照著做……”
他說完這個,成舟海想了想:“如今這世道,讀書人確實是越來越多了,看起來過不多久又得變?”
“希望有得變吧。”寧毅隨口答道,“其實商人也越來越多,他們有錢,有往上爬的心思。如今許多高官,不也是被商人影響到了麼?現在他們可以慢慢影響,到了一定程度,一定會推著變的……呵,我這也算是在商言商了……”
成舟海皺起眉頭,片刻之後,才點頭同意:“會死一大批人的。”
寧毅還在看棋局:“一個社會潮流,一變就是二三十年上百年,我躲著也就是了。”
他實際上還有一句話沒說,武朝如今文恬武嬉,看起來歌舞升平,實際上都不知道還有沒有變的機會。倒是在這句話後,一直聽他說話,沉默著下棋的秦嗣源開了口。
“立恆……在霸刀莊裡推行的那些東西,有為此做准備的想法麼?”
寧毅皺起眉頭來。自上京以來,他大概知道秦嗣源對這個很感興趣,知道他會有一次詢問,卻想不到問的是這個問題。
“那是一個偏方。”想了一會兒之後,他如此說道,“與治世無關。而且……現在不好說,若有機會看到結果,以後倒是可以拿來探討一番。”
他看了看秦嗣源。
那確實只是一個偏方,治的是積弱,不是世道。中國近代史上的那次革命,最值得稱道的,是對每一個參與的基層成員進行了煽動。而在此之前,每一次的造反、起義或是大規模的武裝鬥爭,煽動的層面都僅僅停留在士大夫與將領的一層,真正的底層成員永遠只是跟著大潮走,沒有煽動的價值。而這個煽動的價值,也只能體現在戰鬥力上,於其它則關系不大。
秦嗣源點頭笑了笑:“立恆有這樣的想法,又有這樣的能力,自山東回來,又何妨去讀讀國子監,試試功名?”
寧毅也笑起來:“我只是瞎說而已。對那些事……沒有能力,也真不感興趣。”
寧毅做事的能力早擺在那兒,秦嗣源哪裡會對他的能力質疑,只是此時也只能笑著搖頭:“也罷、也罷,此事我們回來再說……今日還有事,這一局算老夫輸了。舟海,你替為師陪陪他,待會要走,也送送立恆。哦,立恆後天離開時,我再去送你。”
他今天留下寧毅,主要的好像就是與寧毅論論那“治國”,此時說完,趕著去處理自己的事情了。待老人背影消失,寧毅扭頭看了看旁邊的成舟海。
“成兄,莫非是專門過來找在下的?”
成舟海這一次過來,什麼事情都沒跟秦嗣源說,而且看他神情,似乎也是有些東西要跟自己說,寧毅微感疑惑。那邊,成舟海抬頭看看天色,微笑拱手。
“還有時間,邊走邊說?”
“好。”
就在兩人一道離開秦府的同時,汴梁城內的另一處地方,周佩將一把匕首揣進懷裡,懷著堅毅的神情,正在將自己裝進一個大麻袋。那麻袋將她裝進去之後,封好了口子,然後又被打開,周佩將腦袋鑽出來看了看,才再次進去,對旁邊的人說了一句:“你們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