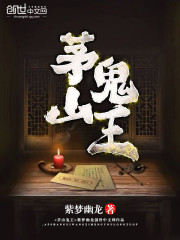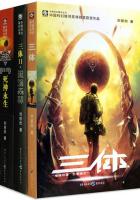第272章 絕頂的官僚(2)
所謂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掃平天下,也絕不會缺少對手,因為在這個地方,什麼都會缺,就是不缺敵人。
張四維死了,但一個更為強大的敵人,已經出現在申時行的面前。而這個敵人,是萬歷一手造就的。張居正死後,萬歷得到了徹底的解放,沒人敢管他,也沒人能管他,所有權力終於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備按自己的意願去管理這個帝國。但在此之前,他還必須做一件事。
按照傳統,打倒一個人是不夠的,必須把他徹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響,才算是善莫大焉。
於是,一場批判張居正的活動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
張居正在世的時候,吃虧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罷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過。現在時移勢易,第一個跳出來的自然也就是這些人。
萬歷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呂首先發難,攻擊張居正之子張嗣修當年科舉中第,是走後門的關系戶雲雲。
這是一次極端無聊的彈劾,因為張嗣修中第,已經是猴年馬月的事,而張居正死後,他已被發配到邊遠山區充軍。都折騰到這份兒上了,還要追究考試問題,是典型的沒事找事。
然而,事情並非看上去那麼簡單,事實上,這是一個設計周密的陰謀。
丁此呂雖說沒事干,卻並非沒腦子,他十分敏銳地察覺到,只要對張居正的問題窮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寵信。
這一舉動還有另一個更陰險的企圖:當年錄取張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輔申時行。
也就是說,打擊張嗣修,不但可以獲取皇帝的寵信,還能順道收拾申時行,把他拉下馬,一箭雙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風平地而起。
申時行很快判斷出了對方的意圖,他立即上疏為自己辯解,說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編號,沒有姓名,根本無法舞弊。
萬歷支持了他的老師,命令將丁此呂降職調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氣。但這道諭令的下達,才是暴風雨的真正開端。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楊繼盛那樣的孤膽英雄,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團伙作案。一個成功言官的背後,總有一撥言官。
丁此呂失敗了,於是幕後黑手出場了,合計三人。這三個人的名字,分別是李植、江東之、羊可立。在我看來,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實的“罵仗鐵三角”。之所以給予這個榮譽稱號,是因為他們不但能罵,還很鐵。李、江、羊三人,都是萬歷五年(1577)的進士,原本倒也不熟,自從當了御史後,因為共同的興趣和事業(罵人)走到了一起,在戰鬥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成為了新一代的攪屎棍。
之所以說新一代,是因為在他們之前,也曾出過三個極能鬧騰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劉台、趙用賢、吳中行。這三位仁兄,當年曾把張居正老師折騰得只剩半條命。十分湊巧的是,他們都是隆慶五年(1571)的進士,算是老一代的鐵三角。
但這三個老同志都還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張居正,他們偏罵,這叫義憤。後來的三位,大家都不罵了,他們還罵,這叫投機。
丁此呂的奏疏剛被打回來,李植就衝了上去,槍口直指內閣的申時行,還把管事的吏部尚書楊巍搭了上去,說這位人事部長逢迎內閣,貶低言官。
話音沒落,江東之和羊可立就上疏附和,一群言官也跟著湊熱鬧,輿論頓時沸沸揚揚。
對於這些舉動,申時行起先並不在意,丁此呂已經滾蛋了,你們去鬧吧,還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幾天以後,萬歷下達了第二道諭令,命令丁此呂留任,並免除應天主考高啟愚(負責出考題)的職務。
其實申時行並不知道,對於張居正,萬歷的感覺不是恨,而是痛恨。這位曾經的張老師,不但是一個可惡的奪權者,還是籠罩在他心頭上的恐怖陰影。
支持張居正的,他就反對;反對張居正的,他就支持,無論何人、何時、何種動機。
這才是萬歷的真正心聲。上次趕走丁此呂,不過是給申老師一個面子,現在面子都給過了,該怎麼來,咱還怎麼來。
申時行明白,大禍就要臨頭了,今天解決出考題的,明天收拾監考的,殺雞儆猴的把戲並不新鮮。
情況十分緊急,但在這關鍵時刻,申時行卻表現出了讓人不解的態度,他並不發文反駁,對於三位御史的攻擊,保持了耐人尋味的沉默。
幾天之後,他終於上疏,卻並非辯論文書,而是辭職信。就在同一天,內閣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楊巍同時提出辭呈,希望回家種田。這招以退為進十分厲害。刑部尚書潘季馴、戶部尚書王璘、左都御史趙錦等十余位部級領導紛紛上疏,挽留申時行。萬歷同志也手忙腳亂,雖然他很想支持三位罵人干將,把張居正整頓到底,但為維護安定團結,拉人干活,只得再次發出諭令,挽留申時行等人,不接受辭職。
這道諭令有兩個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時行,說這事我也不談了,你也別走了,老實干活吧。
此外,是告訴江、羊、李三人,這事你們干得不錯,深得我心(否則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為止,以後再說。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此後的續集告訴我們,這一切,只不過是熱身運動。
問題的根源在於“鐵三角”。科場舞弊事件完結後,這三位拍對了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東之升任光祿寺少卿,李植任太僕寺少卿,羊可立為尚寶司少卿。
太僕寺少卿是管養馬的,算是助理弼馬溫,正四品;光祿寺少卿管吃飯宴請,是個肥差,正五品;尚寶司少卿管公文件,是機要部門,從五品。
換句話說,這三個官各有各的好處,卻並不大,可見萬歷同志心裡有譜:給你們安排好工作,小事來幫忙,大事別摻和。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沒明白其中的含義,給點兒顏色就准備開染坊,雖然職務不高,權力不大,卻都很有追求,可謂是手揣兩塊錢,心懷五百萬,歡欣鼓舞之余,准備接著干。
而這一次,他們吸取了上次的教訓,打算捏軟柿子,將矛頭對准了另一個目標——潘季馴。
可憐潘季馴同志,其實他並不是申時行的人,說到底,不過是個搞水利的技術員。高拱在時,他干,張居正在時,他也干,是個標准的老好人,無非是看不過去,說了幾句公道話,就成了打擊對像。話雖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緣不錯,又屬於特殊的科技人才,還干著司法部部長(刑部尚書),不是那麼容易搞定的。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徹底終結了他。這封奏疏徹底證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絕口不提申時行,連潘技術員本人都不罵,只說了兩件事——張居正當政時,潘季馴和他關系親密,經常走動;張居正死後抄家,潘季馴曾幾次上疏說情。
這就夠了。
申時行的親信,不要緊,個人問題,不要緊,張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沒過多久,兢兢業業的潘師傅就被革去所有職務,從部長一踩到底,回家當了老百姓。
這件事干得實在太過齷齪,許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棟分別上疏,為潘季馴求情,卻被萬歷駁回,還罰了一年工資。
有皇帝撐腰,“鐵三角”越發肆無忌憚,把戰火直接燒到了內閣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別狠,明的暗的都來,先是寫匿名信,說大學士許國安排人手,准備修理李植、江東之。之後又明目張膽地彈劾申時行的親信,不斷發起挑釁。
部長垮台,首輔被整,鬧到這個份兒上,已經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個倒霉的是誰,連江東之當年的好友,刑科給事中劉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來大吼一聲:
“你們要把當年和張居正共事過的人全都趕走,才肯甘休嗎(盡行罷斥而後已乎)?!”
然而讓人費解的是,在這片狂風驟雨之中,有一個人卻始終保持著沉默。面對漫天陰雲,申時行十分鎮定,既不吵,也不鬧,怡然自得。這事要換在張居正頭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這位仁兄的脾氣,免不了先回罵兩句,然後親自上陣,罷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罷休。劉台、趙用賢等人,就是先進典型。
就能力與天賦而言,申時行不如張居正,但在這方面,他卻遠遠地超越了張先生。
申首輔很清楚,張居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務天才,而像劉台、江東之這類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個白痴水平。和他們去較真兒,那是要倒霉的,因為這幫人會把對手拉進他們的檔次,並憑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長期的工作經驗,戰勝敵人。
所以在他看來,李植、江東之這類人,不過是跳梁小醜,並無致命威脅,無須等待多久,他們就將露出破綻。所謂寬宏大量,胸懷寬廣之外,只因對手檔次太低。
然而“鐵三角”似乎沒有這個覺悟,萬歷十三年(1585)八月,他們再一次發動了進攻。
事情是這樣的,為了給萬歷修建陵墓,申時行前往大峪山監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結果挖出了石頭。
在今天看來,這實在不算個事,把石頭弄走就行了。可在當時,這就是個掉腦袋的事。
皇帝的陵寢,都是精心挑選的風水寶地,要保證皇帝大人死後,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這麼塊石頭地,存心不讓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時行畢竟只是監工,要把他拉下馬,必須要接著想辦法。經過一番打探,辦法找到了,原來這塊地是禮部尚書徐學謨挑的。這個人不但是申時行的親家,還是同鄉。很明顯,他選擇這塊破地,給皇上找麻煩,是有企圖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兩人的關系,就能把申時行徹底拖下水,而這幫野心極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輔的繼任者,只要申時行被彈劾下台,就立即推薦此人上台,並借此控制朝局。這就是他們的計劃。
然而,這個看似萬無一失的計劃,卻有兩個致命的破綻。
幾天之後,三人同時上疏,彈劾陵墓用地選得極差,申時行玩忽職守,任用私人,言辭十分激烈。
在規模空前的攻擊面前,申時行卻毫不慌張,只是隨意上了封奏疏說明情況,因為他知道,這幫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後,萬歷下文回復:“閣臣(指申時行)是輔佐政務的,你們以為是風水先生嗎(豈責以堪輿)?!”
怒火中燒的萬歷罵完之後,又下令三人罰俸半年,以觀後效。三個人被徹底打蒙了,他們抓破腦袋,也想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歸根結底,還是信息工作沒有到位,這幾位仁兄晃來晃去,只知道找徐學謨,卻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萬歷。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親自出手挑塊地,卻被他們罵得一無是處。不過還好,畢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罰了半年的工資,勵精圖治,改日再整。
可還沒等這三位繼續前進,背後卻又挨了一槍。
在此之前,為了確定申時行的接班人選,三個人很是費了一番腦筋,反復討論,最終拍板——王錫爵。
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過場,張居正奪情的時候,上門逼宮,差點兒把張大人搞得橫刀自盡,是張居正的死對頭,加上他還是李植的老師,沒有更適合的人選了。看上去是那麼回事,可惜有兩點,他們不知道:其一,王錫爵是個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歡張居正,卻並非張居正的敵人。其二,王錫爵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進士,考試前就認識了老鄉申時行。
會試,他考第一,申時行考第二;殿試,他考第二,申時行第一。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
基於以上兩點,得知自己被推薦接替申時行之後,王錫爵遞交了辭職信。這是一封著名的辭職信,全稱為《因事抗言求去疏》,並提出了辭職的具體理由:
老師不能管教學生,就該走人(當去)!這下子全完了,這幫人雖說德行不好,但畢竟咬人在行,萬歷原打算教訓他們一下後,該怎麼樣還怎麼樣。可這仨太不爭氣,得罪了內閣、得罪了同僚,連自己的老師都反了水。萬歷想,再這麼鬧騰,沒准兒自己都得搭進去。於是他下令,江東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級,發配外地。
家犬就這麼變成了喪家犬。不動聲色間,申時行獲得了最終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