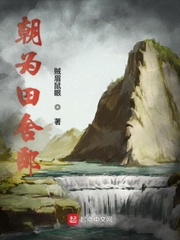顧青感受到了滿滿的惡意,同時他也發現了一個真理,女人哪怕尊貴如公主,也是不講道理的。
“道理”這東西,跟女人天生胡攪蠻纏的屬性相悖。
“殿下且慢,不能殺!”顧青情急大喝道。
萬春公主怒道:“為何不能殺?”
“不教而誅謂之虐,臣請問公主殿下,殺臣的理由是什麼?”
提起理由,萬春公主愈發羞憤了:“理由你難道不知嗎?”
顧青茫然地道:“臣真的不知。”
“你,你你剛才……”
“臣剛才做什麼了?”顧青眼神無辜地看著她。
“你明明看到……”萬春公主說了一半便說不下去了。
“臣剛才在此賞夕陽,除此什麼都沒看到。”
旁邊一名年長的宮女上前,小心翼翼地道:“殿下,不可妄殺朝臣,事情會鬧大的……”
萬春公主恨恨剜了顧青一眼,冷聲道:“你說的話自己可要記住了,你什麼都沒看到,若本宮在外面聽到任何風言風語,必定是你傳出去的,那時本宮拼了被父皇責罵也要誓取你性命。”
顧青不甘地指了指周圍十幾名宮女,道:“若是她們傳出去的……”
“也取你性命!”
顧青心悅誠服地道:“公主殿下處事公正,不偏不倚,臣拜服。”
萬春公主臉蛋一紅,哼了一聲轉身便走。
山腰寢殿內,萬春公主捂著臉躺在床榻上,一雙白玉般的蓮足在半空亂蹬。
玉真公主坐在旁邊,一臉好笑地看著她:“你說你的運氣究竟差到什麼地步,居然從浴池一路滾到山道上,還是光著身子……”
“皇姑——”萬春公主尖叫起來,崩潰地揪著頭發道:“莫提這事了,我都想自盡了!”
玉真公主笑道:“被人看到就看到了,反正又沒少一塊肉,量顧青那小子也不敢傳出去,他若敢亂說,皇姑親自幫你剁了他。”
萬春公主氣得直蹬腿:“什麼叫被人看到就看到了?我從小到大可沒被男人看過,皇姑你說顧青是不是故意的?他一定是故意等在山道那裡,等我從竹林裡摔下來。”
玉真公主掩嘴笑個不停:“沒錯,他定是故意的,他早就算准了你一定會從山上摔下來,等著看你白花花的身子。”
玉真公主又提到白花花的身子,萬春羞憤欲絕:“皇姑你再提此事,我便從山上跳下去,我不活了!”
恨恨地瞪著玉真公主,萬春道:“當初建道觀時,你為何要在竹林裡修浴池?你當時安的什麼心思?”
玉真公主大笑道:“我早算准了你會從竹林裡白花花地滾下去,所以特意為你修了個浴池,不然你如何白花花的?”
萬春大怒,飛身撲過來撓玉真的癢癢肉,二人滾成一團笑鬧不停。
良久,二女累了,停下來並頭躺在床榻上,仰頭望著寢殿上方的房梁,玉真公主喘著氣道:“那顧青把你看光了,不能不負責吧?幸好他尚未娶妻,而你也未嫁人,不如請你父皇賜婚,將你們結成一對兒,那樣便可以讓他隨時看白花花的你了,罰他看一輩子。”
萬春羞憤地捂住頭:“皇姑莫說了,我對他無男女之意。”
萬春哼道:“大唐能作詩的少年何止千千萬,難道遇到一個會作詩的少年我便要嫁給他麼?”
玉真眼中含笑道:“會作詩的少年當然不少,可既能作詩又看光你身子的人,普天之下僅此一人,你不嫁他還能嫁誰?”
“皇姑你又說!又說!”萬春氣急敗壞撲過來撓她,二人再次笑鬧一團。
殿外的雲板敲了三下,宦官邁著細碎的腳步從殿外穿行而過,尖著嗓子報時:“天地人和,至福恆昌,夜半,子時。”
寢殿內,二女安靜下來,漸漸有了困意。
睡意朦朧之中,萬春公主如夢囈般呢喃道:“皇姑,我的意中人不僅要有安邦定國之才,亦要有情有義俯仰不愧怍天地的真性情,如此,才可令我甘心下嫁,顧青……他還不夠。”
說完萬春公主沉沉睡去。
…………
第二天一早,顧青再次向玉真公主請辭。
玉真公主頗為意外,想了想又覺得在意料之中,笑著上下打量他。
顧青被她看得不自在,身子扭了扭,干笑道:“臣在長安左衛尚有公務,實在無法久留於此,還請公主殿下見諒。”
玉真公主好笑地道:“昨日不是說好了三日後再走嗎?為何突然又改了歸期?”
顧青嚴肅地道:“臣昨夜輾轉反側,想到左衛的同僚們殫精竭慮為我大唐日理萬機,而臣卻在風景怡人之地不思進取悠閑度日,臣反省之後,頓覺羞愧無地,辜負天子所托……”
玉真公主嘴角扯了扯:“真會編,會作詩的才子果然不凡,編起瞎話來眼睛都不眨,這勉強也算本事吧?”
“臣字字發自肺腑,絕無一字妄語。”
玉真公主似笑非笑道:“如此著急回長安,難道不是因為昨日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看了什麼不該看的東西?”
顧青茫然道:“臣昨日與摩詰先生談論詩文,除此並未做任何不該做的事呀。”
玉真公主哼了哼:“好,你繼續裝,回到長安後你也要裝下去,管好你的嘴,否則……哼哼。”
顧青長揖行禮:“殿下的哼哼好可怕,臣一定謹記殿下之言。”
玉真公主噗嗤一笑,道:“去吧去吧,本宮這次便不留你了,想想都替你們尷尬,還是暫時不見為好。”
顧青松了口氣,笑道:“臣謝殿下體諒,日後若有閑暇,臣當再來道觀恭聽殿下教誨。”
顧青長揖作別,然後轉身離開。
顧青走後,玉真公主身後的山水屏風人影一閃,萬春公主從屏風內走了出來,垂頭不語,卻滿臉羞紅。
玉真公主笑道:“看光你身子的人已經走了,他還算識相,不好意思待下去,一大早便急著告辭,你可滿意了?”
萬春哼道:“他走或不走,與我何干?”
玉真公主笑道:“既然與你無關,那我可就把他請回來再住幾日了……”
萬春氣得跺腳道:“皇姑你又逗我。”
玉真公主若有深意地道:“你不稀罕他,可有別人稀罕他呢。據我所知,鴻臚寺卿張九章的侄孫女懷錦,與顧青來往很親密,懷錦似有求鳳之意。”
萬春神情一怔,喃喃道:“張懷錦?”
玉真公主好笑地看著她:“顧青這般翩翩少年,怎麼可能沒人喜歡?你若不喜歡,便只能拱手讓人了。邀請顧青來道觀之前,我著人特意打聽了一下顧青此人,他可不僅僅會作詩,這個人呀,頗不簡單呢……”
“他……哪裡不簡單了?”
玉真公主悠悠地道:“你既然無意,便莫來問我,你若有意,可自己去打聽,我什麼都不會說。”
…………
顧青坐著自家的簡陋馬車匆匆下山。
不下山不行了,太尷尬了,昨夜顧青確實輾轉反側難眠,閉上眼腦子裡便全是一片白花花的畫面,雖然昨夜所見非常短暫,不過是驚鴻一瞥,但該看到的全都看到了,車速太快,顧青有點暈車……
獨自坐在馬車裡,顧青盤腿闔眼假寐,嘴角忽然一勾。
沒想到長得像混血兒也就罷了,身材竟也如此不凡,白。
往後在長安還是盡量躲開與萬春公主見面吧,不是尷尬的問題,顧青覺得自己很有可能會被她殺人滅口,畢竟女人向來是不講道理的,回頭她若越想越覺得吃虧,很難說她會冒出什麼喪心病狂的念頭。
兩個時辰後,馬車進了長安城,從西面延平門而入,穿過豐邑坊,長壽坊,橫穿朱雀大道,快到東市時,顧青聽到馬車外面一陣喧鬧,伴隨著人群的尖叫聲。
顧青一愣,掀開馬車的車簾。
卻見東市外的安邑坊大街上,人群如洪流般湧走,看行人的神色滿是驚恐惶然,仿佛看到了洪水猛獸般。
片刻之後,顧青馬車方圓附近的行人已跑得一個不剩,緊接著,遠處傳來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顧青凝目望去,卻見一隊披甲的巡街武侯匆匆趕來。
再看馬車前方空蕩蕩的街道中央,一名中年男子渾身是血倒在地上,地上已流了一大灘鮮血,中年男子穿著頗為華貴,已沒了動靜,顯然人已死了。
男子旁邊站著一位魁梧大漢,大漢滿臉絡腮胡,眼神滿是戾氣,手執一柄匕首,匕首上沾滿了血,明明四周已無人,大漢仍將握匕首的手高舉向天,朝四周嘶聲喝道:“好教各位知曉,本人周橫武,殺人者便是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在殺人處等官府來拿問,莫牽扯不相干之人。”
顧青皺眉,僅僅一句話,他便聽出了游俠的味道。
“被殺者,長安東市祥福記掌櫃劉敬祖,我與劉敬祖無怨無仇,但我還是親手殺了他,為何?蓋因劉敬祖為富不仁,所賣絲綢以次充好,將上等的亳絲換成下等貨,福州一位商人不知情,進了大批次等貨回了福州,發現後趕來長安與劉敬祖爭辯道理,劉敬祖卻不認賬,轉而訴之官府,官府言稱無據,不予受案。福州商人家中債台高築,被逼無奈之下,上月全家老小共計二十余口喝了砒霜死了。”
“周某本是草莽行俠之人,立誓鏟盡人間不平事,聽說此事後,周某孤身來長安,等了數日得知劉敬祖的行蹤,今日將其擊殺於鬧市之中,殺人者周橫武無悔,坦蕩認罪,但能為人間鏟了一樁不平事,告慰福州商人全家老小之冤靈,周某死亦無憾!”
“哈哈,痛快!此時若有酒該多好。”
說完周橫武扔掉匕首盤腿坐在街心,周圍行人隔著老遠悄悄窺視,又敬又畏地看著他,看熱鬧的人群裡有幾個膽大的忽然鼓掌起哄。
“干得好!快意恩仇,鏟盡不平,真壯士也!”
周橫武聽著人群裡的叫好聲,不由寬慰地仰天哈哈大笑,隨即大聲道:“誰能借周某一壇濁酒,周某今生還不起,來世定當報答。”
人群裡敬佩周橫武的幾個人湊了酒錢,在旁邊的酒樓裡買了一壇酒,壯著膽子小心翼翼遞到周橫武面前。
周橫武接過酒,笑道:“你莫怕我,我非嗜殺之人,若無恩怨,絕不向無辜之人動手,更何況你對我有施酒之恩,此恩來世再報。”
說完周橫武捧起酒壇,大口灌了半壇酒,放下酒壇擦了擦嘴,大笑道:“真正痛快了!”
巡街的武侯早已到了現場,一直在靜靜地等周橫武喝完酒,最後武侯們上前,用鐐銬將周橫武鎖拿,周橫武也不反抗,神色坦然地任武侯們將他押走。
空蕩的街心似乎仍回蕩著一縷俠氣。
熱鬧看完了,顧青吩咐車夫繼續走。
坐在馬車裡,顧青的表情卻很平靜。
看俠客快意恩仇,鏟人間不平事固然痛快,可是如果這個世道處處需要行俠仗義的人來主持公道,那麼這世道已變成了什麼模樣?
如果所謂的正義只能靠這些草莽游俠來維持,官府卻無能為力,那麼世道未免太可笑了。
最重要的是,“正義”二字由誰來定義?游俠嗎?
馬車到了常樂坊,顧青想了想,吩咐車夫去李十二娘府上。
進了李十二娘府,女弟子們正在院子裡練劍,見顧青進來,女弟子們紛紛朝顧青行禮,有幾個女弟子行完禮後卻咯咯一笑,嬌羞地跑開。
李十二娘府上有客人,見顧青突然到來,李十二娘一喜,道:“不是去終南山的公主道觀了麼?為何如此快便回來了?”
顧青笑道:“想李姨娘了,便提前回來了。”
李十二娘哼了哼,笑道:“恐怕想的不是我吧?懷錦那丫頭怎麼回事?你去道觀這幾日,她每日都來我府上催問你何時歸來,你和她莫非……”
顧青嘆道:“好好的兄弟之情,李姨娘怎可誤會?我與三弟之純潔,天地可鑒……”
“好了好了,給你介紹幾位朋友。”李十二娘不客氣地打斷了他,轉身朝前堂內的三個中年男子笑道:“這位是顧家夫婦的獨子,顧青。他非江湖之人,如今官居左衛長史。”
三位中年男子立馬起身,朝顧青抱拳行禮。
顧青笑著還禮,同時不動聲色地打量三人,三人皆是一身勁裝武夫打扮,看抱拳的做派便知是江湖人,應是俠客之流。
其中一名魁梧大漢笑道:“我叫陳扶風,籍籍無名之輩,十多年前與令雙親在長安結識,陳某生平最為敬服者便是令雙親,可惜……”
李十二娘打斷道:“好了,莫提當年的事。每次見到你們這些故人便要重提當年,一次次徒惹傷心,所以我近年已不願再見故人了。”
陳扶風笑道:“好,不提便不提,說起當年的事,我也不好受。”
李十二娘對顧青道:“你來得正好,今早從青城縣送來一封書信,看筆跡是懷玉寫給你的,送信的人說,似乎有急事,張懷玉許以重金,八百裡加急送來的。”
說著李十二年從懷裡掏出一封信給顧青。
顧青心頭一緊,張懷玉從來不給他寫信的,這次不僅寫了信,還是八百裡加急,顯然出了大事。
展開信匆匆看了一遍,顧青的神情愈見冷峻。
李十二娘看著他,好奇地道:“怎麼了?懷玉在青城縣有麻煩了嗎?”
顧青將信遞給她,苦笑道:“張懷玉沒麻煩,麻煩的是另一個人……”
李十二娘接信看了一遍,邊看邊皺眉,道:“這個宋根生是你的朋友嗎?還是青城縣令?縣令怎可如此糊塗,輕易動豪紳的土地田產?”
顧青嘆道:“這個宋根生,一直有些天真,我只是沒想到他居然如此天真。”
想了想,顧青不得不辯解道:“說是糊塗倒不至於,宋根生拿問豪紳,顯然是縣內的土地和賦稅已到了迫在眉睫的關頭,豪紳或許行事過分了……”
李十二娘無奈地道:“這些話你跟我說有甚用?懷玉寫信給你,雖未在信中求援,但能看出她也很著急了,否則依那丫頭的性子,斷不會主動寫信的。接下來你打算如何辦?”
顧青沉吟片刻,道:“信裡說,宋根生還未問出豪紳背後的人,我懷疑此人大有來頭,應是長安城的某位權貴,我想請李姨娘打聽一下,看長安城裡哪位權貴在蜀州青城縣置有大量田產……”
李十二娘點頭道:“可能會費一些時日,打聽清楚應該不難,若打聽出了結果,你該如何辦?”
顧青嘆道:“當然是直接找到正主,把事情平息下去,宋根生畢竟是我從小到大的朋友,他惹下的麻煩,我來擔當便是。”
李十二娘眼裡漸漸有了笑意,道:“記得你剛來長安時,臉上有笑,但眼中無情,我曾經有過憂慮,擔心你本性無情冷酷,沒想到你已慢慢在改變,如今的你,擔得起‘有情有義’四個字。”
“放心,姨娘會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