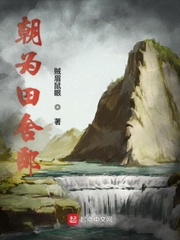臣子上疏,諫止昏行,這是臣子的義務和本分。
顧青上的這道奏疏其實用辭還算克制,但奏疏裡的強硬語氣卻仍令李亨感到很不爽。
大唐向回紇借兵,屬於戰略層面的大事,李亨與曾經的東宮謀臣們商議了多日才確定下來的。
李亨雖是大唐新的天子,但他很清楚自己的實力不夠強大,手裡真正能掌控的只有三萬余朔方軍,剩下的只有不知在何處打游擊的安重璋。
顧青手裡的安西軍兵強馬壯,但人家分明已有擁兵自重的跡像,從杜鴻漸發來的奏疏裡,李亨知道安西軍已被顧青完全掌握,如今的安西軍將士只知顧公爺,而不知大唐天子,這支軍隊李亨無法調動,也不敢得罪。
回紇借兵的條件,李亨也與朝臣們商議多次,確實有些人反對,也有人贊同。反對的人跟顧青的理由一樣,此非明君之道,而贊同的人則比較功利,他們認為平叛之事比天大,只要能迅速平定叛亂,一切代價皆可付出。
後來李亨也當面問過郭子儀,高仙芝等軍中將領,郭子儀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他是軍伍中人,看問題很現實,一切用軍事的立場來解釋的話,世事如棋局,無非以子易子,重要的是勝負。
權貴是做大事的人,而做大事的人往往少了幾分人味兒,他們已經習慣了棋局的思維,擺在棋盤上的棋子本就是用來攻守或是犧牲的,只要犧牲有價值,這枚棋子就沒白用。
包括長安的婦孺百姓和財產,他們也是棋子。
【書友福利】看書即可得現金or點幣,還有iphone12、switch等你抽!關注vx公眾號【書友大本營】可領!
一項政令拿到朝堂上討論,有反對的,也有贊同的,這很正常。
但是李亨卻偏偏對顧青的反對奏疏很不滿。
因為提出反對的人是顧青,就這麼簡單。
顧青和他麾下的安西軍是李亨無法掌控的人,而且顧青擁兵之勢已越來越明顯,李亨想到自己登基居然還要派人去問他的意見,甚至不得不付出南方賦稅的代價來換取顧青口頭上的擁戴,李亨便覺得屈辱,明明得位正統,卻要自降身份詢問一個臣子的意見,大唐天子何時已如此不堪了?
許多的不滿,再加上深深的忌憚積累在一起,再加上顧青這道語氣強硬的反對奏疏,於是顧青對天子對朝廷的諫止奏疏被無限放大了,李亨心裡也將他的奏疏定性為惡意。
一個手握兵權且惡意滿滿的臣子,李亨怎能容他?
寬敞奢華的金帳內,李亨將顧青的奏疏合上,鼻孔裡輕哼了一聲,轉眼望向旁邊的李泌,道:“李卿,顧青的奏疏你怎麼看?”
李泌垂頭道:“陛下,臣以為,顧青所言並無錯處,回紇人的條件確實不該答應,於陛下聖名有損。”
李亨聞言愈發不滿,哼道:“朕手中只有三萬朔方軍,靠這點兵馬如何能平定叛亂?向回紇借兵也是無奈之舉,至於回紇人的條件……可以談一談嘛,談都不談就極力反對,顧青難道不覺得有失臣子之禮嗎?”
李泌看了看李亨的臉色,猶豫了一下,還是忍不住道:“陛下,安西軍和朔方軍南北夾擊的戰略已成,多費些時日,關中定可收復,其實回紇借不借兵並不重要,有郭大將軍和顧青兩位統兵平叛足矣。”
李亨冷聲道:“郭老將軍也就罷了,顧青的安西軍,朕能信嗎?將來平叛之後,焉知他顧青不會成為第二個安祿山,他若真是忠於大唐忠於朕的臣子,朕派杜鴻漸和李輔國去安西軍大營時,便該識相地把兵權交出來,可他沒有絲毫交兵權的打算,呵,鮮於仲通和哥舒翰也甘屈於下,算起來安西軍已有十萬控弦之士,這麼多兵馬,他想干什麼?”
李泌心中其實也有猜疑,沒辦法,顧青手中的兵馬太強大了,任何人看到了都不會安心,有這樣一支不服宣調的強大兵馬在臥榻之側,誰能睡得著?
李泌想了想,道:“陛下,如今最重要的還是平叛,平定叛亂後,陛下還政於長安,臣以為陛下可封賞群臣,尤其對顧青,可委以重任,讓他做到人臣之巔,只不過……”
“只不過怎樣?”
“人臣之巔,自是文職為尊,顧青可任右相,掌朝政大小事,爵位再封高一點,封個郡王亦可,但節度使之類的武職可卸下了,同時,安西軍中諸將亦當封賞,將他們分別封到不同的州縣任武將職,安西軍將士打亂分散,一部分戍邊,一部分禁衛宮闈,一部分充作地方州縣駐軍,如此,陛下之憂可解矣。”
李亨想了想,不由大悅,笑道:“李卿不愧是朕的肱骨之臣,對朕助益良多,顧青若是亂世英雄,朕便剪了英雄之羽翼,把他困在方寸之地,猛獸囚於樊籠,焉能振爪張目?”
李泌也笑了笑,心中不由喟嘆。
他對顧青的印像不錯,二人曾於重陽宮宴上結識,彼此都對對方有好感。若無官職和立場,想必二人定是一生的知己好友。
然而李泌終究是李亨的臣子,他注定要站在李亨的立場上決定敵友。
…………
日落時分。
兩千余兵馬跌跌撞撞行走在洛陽城外的大道上,後方十余裡外,隱約可見安西軍的旌旗飄展,喊殺聲陣陣傳蕩。
王貴騎在馬上,臉上青一塊黑一塊布滿了塵土污漬,頭盔不知扔哪兒去了,披散著頭發,身上的鎧甲也不整齊,肩甲和胸甲都丟了,騎在馬上東倒西歪,一臉惶恐之色望向身後的追兵。
旁邊一名軍士扛著叛軍的旌旗,旌旗上繡著“大燕河東節度使安”的字樣。
旌旗上的名號並非安祿山,而是安祿山麾下的一員大將,名叫安守忠,他原姓王,後來被安祿山收為義子,於是改姓安,其人智勇兼備,頗受安祿山重用。
安祿山死後,安守忠奉命戍守潼關,如今潼關的守將便是他。
王貴打著安守忠的旗號正是恰當。
洛陽城外,王貴一行兩千余人一副殘兵敗將的模樣,倉惶地朝洛陽進發,後面還有兵馬打著安西軍的旗號喊殺追擊,路上早有洛陽城派駐在外的叛軍斥候看到,飛快將消息傳到洛陽。
王貴和麾下兩千余將士皆是叛軍打扮,而且戲演得很投入,不僅服飾旗號沒問題,而且喬裝成了敗軍的樣子。
敗軍該是什麼樣子?
丟盔棄甲,倉惶逃命,軍不成軍,兵將不屬。
王貴演這場戲很講究細節,臨行前便布置了很久,還親自下場指導將士們的演技,尤其嚴禁露出笑容,一支倉惶敗逃的軍隊不應該有笑容,他們的臉上只能出現滿滿的驚恐和求生欲。
兩千兵馬跌跌撞撞來到洛陽城西門外,看著高高懸起的吊橋,王貴騎在馬上喘了幾口氣,仰頭看著城樓大聲道:“城中袍澤快快放下吊橋,讓我等進城!”
洛陽城樓上探出一個腦袋,大聲問道:“爾等是何人?”
王貴惶然道:“我是河東節度使安守忠的麾下忠字營校尉偏將,我姓王名貴,你們難道沒聽說過我嗎?”
城樓上問話的小將疑惑地向身邊的袍澤投以詢問的眼神,袍澤們紛紛搖頭,表示不認識這號人。
“安節帥奉旨戍守潼關,爾等為何來此?”
王貴苦澀地道:“顧青的安西軍太厲害了,攻關的第二日,潼關……丟了。”
城樓上眾將士大驚。
小將驚怒道:“不可能!安節帥是我大燕威名赫赫的大將,怎麼可能輕易失守潼關!”
王貴苦澀地道:“我等剛從潼關逃出來,潼關丟沒丟我們難道不知?別多說了,快放下吊橋讓我們進去,後面還有安西軍的追兵。”
小將仍不信,冷笑道:“你說是就是?如何證明你的身份?你的腰牌和官憑告身呢?”
王貴忍不住怒道:“爾等說的是人話嗎?我們在潼關為陛下和大燕拼命,潼關失守我們好不容易撿了條命跑出來,你還要我們的腰牌?逃命的時候誰還管那些瑣碎?”
小將搖頭道:“沒有腰牌,恕我不能放你們入城,這是規矩。”
王貴大怒:“狗屁規矩!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還怕我是唐軍奸細麼?如今是什麼境況了,咱們大燕被唐軍打得節節敗退,關中丟了好幾個城池,若非我家眷妻兒皆在河北幽燕,老子早就帶著兄弟們改投唐軍了,何必如喪家之犬跑回來?你個混賬再不開門,我便真領著兄弟們投唐軍了,咱們被唐軍打得抱頭鼠竄,逃到洛陽還要受你這小人的腌臜氣,為大燕賣命還有甚意思!”
王貴說完,後面的兩千余將士紛紛指著城頭大罵起來,不少人索性扔了兵器旌旗,一副馬上倒戈投敵的樣子。
這般做派反倒令城頭上的小將猶豫了,一肚子牢騷加上投敵倒戈的威脅,倒真像是叛軍的風格,城下這兩千多人若真是袍澤兄弟,不開城門或許會給自己惹禍。
正在猶豫間,後面數裡之外傳來隆隆的馬蹄聲,極目望去,一支數千人的兵馬掩殺而來,打著的正是安西軍的旗號,喊殺聲如春雷陣陣,令人心悸膽寒。
王貴見狀大急,指著城頭怒喝道:“安西軍追來了,再問你一次開不開門,你若不開門,我們馬上放下兵器歸降!一切罪責都是你,是你害我們無處可逃,你個雜碎,等著被上面殺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