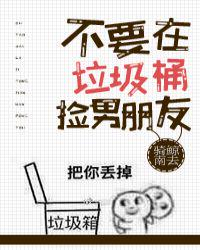滿寶和白善一起“咦”了一聲。
殷或笑道:“不說其他人家如何,我們家裡,就是我祖母,她不常出門,每年逢春遇秋也都會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花市的。若是遇見有喜歡的便買下,稀奇的也買下,由下人買了進獻的反而少些。”
殷或雖然不管事,也萬事不入心,但有些事兒每年都會有,他也就記下了。
一旁的長壽見少爺他們說的歡騰,便補充道:“還有與我們家相熟的花農,手上若是種出新品來,或是種出來的花好,也會送到門上來,老夫人或姑奶奶們見著了喜歡都會留下的。”
滿寶問:“貴嗎?”
長壽頓了一下後道:“與市價是差不離的,看主子們喜歡,要是有特別喜歡的,心裡高興,自然會給高些。”
滿寶便明白了。
殷或卻問,“這麼多花,來年要是都長不出好花來,那些人家豈不就知道被騙了嗎?你不怕他們到時候找上門來?”
滿寶理直氣壯的道:“我賣出去的花是好的,他們自己養殘了怎能怪我呢?”
殷或笑道:“一盆兩盆的花如此也就算了,可這麼多盆花都有問題就惹人懷疑了,而且有些人家是不會想這許多的,全憑好惡行事。他覺得你賣的花養不出好花來,那就是你的花的問題了。”
比如他姐姐們。
他道:“你這些花肯定都不便宜,買得起的不是大富就是大貴人家,你一下得罪這麼多人好嗎?”
滿寶和白善對視一眼後笑道:“我們早想到這一點兒了,所以到時候會喬裝一番,反正不讓人發現我們,也就你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才告訴你的。”
殷或就笑道:“與其如此,不如交給我算了。”
滿寶和白善“啊?”了一聲,一臉的迷惑。
殷或道:“你們再喬裝也會留有痕跡的,你們給我的話本中不是說了嗎,雁過留痕,人走留跡,順騰便能摸瓜,你們不如把花給我,我代你們賣給其他人,別人以後來問我時,我就說是在路上偶爾遇到的一個花農,隨我怎麼形容他都可以,痕跡便斷在了我那裡。”
滿寶問:“你不怕他們找你麻煩?”
殷或笑道:“他們不會的,為那麼一盆花不至於。”
誰會找他的麻煩呢?
他的身體情況擺在這兒,性情擺在這兒,誰會想到是他坑的他們?
就算是他承認了,他們恐怕都不信,而且殷家的地位擺在這兒,除非他家一下從天上落到了地下,不然誰也不會因為那麼一盆花找他的麻煩的。
而若是他家從天上落到了地下,他這副離不開藥罐的身子肯定也活不下去了,那少一樣和多一樣又有什麼區別呢?
倒是這麼一件事實在好玩得很。
滿寶就好奇的問,“那你打算把花賣給誰呀?”
殷或問,“你原先打算賣給誰?”
滿寶:“我想賣給益州王的親戚們。”
殷或:……
他想起他們是從劍南道人,便問道:“你們和益州王有仇?”
“就是不喜歡他,討厭他。”
殷或一頭霧水,“總要有個理由吧。”
滿寶就敗壞他的名聲道:“益州王特別的壞,他貪了修建河堤的銀子,使得犍尾堰決堤了。”
殷或:“這事我聽說過,可不是說主要貪酷的是前益州刺史閆刺史嗎?劍南道節度使和益州王只是被蒙蔽其中,無意收了他的禮,不過失於監察倒是實在的罪名。”
白善到:“那都是假的,我們全益州的百姓都知道,主要貪錢的就是益州王和前節度使。”
殷或張大了嘴巴,朝堂上說的和外面說的也相差太大了吧?
他只是偶爾聽父親和祖母提了一兩句,那這些事父親知不知道?
滿寶繼續道:“還有,他還驅趕災民,強占他們的田地,讓很多回鄉的災民都變成了無地無房的人;為了過個端午節鋪張浪費,大造花車,掏空了安陽縣的財政……”
白善忍不住扭頭看滿寶,悄悄的用手指扯了扯她的衣服,讓她不要說的太過分,不然一聽就假了。
滿寶接下來說的就收斂了一點點,“他肯定是作惡多端,於是有刺客殺他,但他只顧自己逃命,把百姓都推到了刺客面前,然後為了抓刺客大肆抓捕無辜的百姓……”
白善忍不住咳嗽出聲,過分了啊,益州王倒是想抓捕無辜的百姓,那最後不都是他前腳抓,唐縣令後腳就把人提溜走審問,然後順勢放了嗎?
殷或聽得一愣一愣的,因為大家都是朋友了,而且滿寶和白善在他心裡一直是比較靠譜的兩個人,他沒有任何懷疑的就信了。
他呆呆的問道:“難道就沒人管嗎?”
滿寶嘆氣,“誰管呀,在益州,益州王最大,皇帝倒是比他大,但天高皇帝遠,他也管不到我們益州去呀。”
殷或連連點頭,“天子腳下,權貴的確要收斂一些。”
滿寶和白善便一起抬頭看他。
他頓了頓後道:“她們從來不會在外動手,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當街攔人,或勸或罵,或者找到對方家裡去……”
殷或越說臉越紅,但他還是堅持說完了,“我自覺這樣做得不對,父親也說過她們,但因為她們沒犯什麼大的律法,因此倒無人彈劾。上一次對你們做的最過分的一件事是讓人走了我大姐夫的關系想捉拿你們。”
滿寶突然一拍掌,樂道:“我就說嘛,我肯定沒猜錯,你們家怎麼會不叫衙門來抓我們呢,原來是已經叫了,那最後怎麼又沒來?”
殷或:“……祖母派人去攔住了。”
滿寶還略微有些可惜呢。
殷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氣微微有些喘,臉都薄紅起來,卻透著蒼白。
滿寶一看他的臉色便道:“你氣不足,以後還是要少說一點兒話,情緒也不要起伏太大,對了,京城的權貴很凶嗎?你姐姐們這樣都還不算跋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