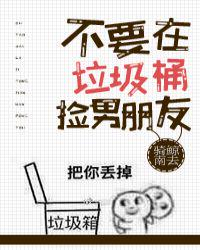對於賺錢,周立君很感興趣,因此興致勃勃的問道:“向先生打算做什麼生意?”
她可是知道的,以前向銘學一心報仇,好像賺的錢都拿去報仇了,所以似乎過得還挺窮?
向銘學就指了周四郎道:“以前我販過糧食和藥材,正巧四郎以後打算走草原這條線,因此我們打算一起做。”
周四郎連連點頭,“我走了這一趟才知道,我們那點兒錢和人去草原上走個來回實在是太虧了,一些小的商號,每次去草原都不少於二十車呢。”
周四郎目前是沒有這個能力的,倒不只是車的問題,主要還是人和錢。
出遠門,帶的人一定是要信得過,可以交付性命的,現在周四郎身邊帶的全是當初從益州城帶出來的三子幾個,還是少了點兒。
但再往外招人他也怕,萬一招到歹人怎麼辦?
正巧向銘學也有這個意思,倆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
周四郎錢不多,向銘學的錢也少,但合在一起倒也勉強能看,主要是他們手底下都有一群絕對信得過的人。
而向銘學在草原上還有點兒人脈,知道路,所以倆人這一次同路就一拍即合決定合作了。
滿寶是不管這些事的,周四郎做生意的錢一直記著賬呢,大部分是公中出的錢,還有一些是各房放進去的布料換的,那算是各房的,也都記著賬呢。
不然周立君和周立重他們跟著干什麼?
基本上,賬都是他們管著的。
果然,滿寶對這些不感興趣,周立君卻問得很詳細,沒辦法,回頭賬還得她和兩個哥哥做呢。
滿寶問:“對了,立重呢?”
“他剛才停車去了,這會兒可能在前頭吃席了。”
周四郎起身道:“走,我們先去給大少爺敬酒去。”
周四郎興衝衝的要去給白大郎敬酒,結果酒剛敬出去就被周六郎順手接過去喝了。
周四郎一頓,看他喝得臉都紅了,便忍不住拍他腦袋:“你是不是傻啊,我的酒你都擋。”
白大郎喝得也有些懵,看到周四郎便樂道:“怎麼周六哥還變出周四哥來了?”
向銘學聽著忍不住一笑。
白大郎傻乎乎的,笑眯了眼,“竟然把向大哥都變出來了。”
眾人:……
白老爺見了連忙拉住白善和白二郎道:“趕緊的,把你們大哥送回洞房去,把客人們攔一攔。”
他是長輩不好出面,只能白善他們兩個去了。
白善一聽,立即拉了白二郎上前擋住還在不斷敬酒的客人,喊道:“吉時到了,吉時到了,我們把新郎官送回新房了,周五哥,你幫著大堂哥把酒喝一喝吧。”
一邊說一邊扶著白大郎就要走。
大家不甘願,立即攔道:“這可不行,這才哪兒到哪兒呀,看現在天光大明的,怎麼就進新房了?”
大家不同意,白善就拉了還在起哄的成大郎道:“成大哥,我大堂哥不擅酒,這會兒已經醉得不行了,再喝下去要出醜了,而且大堂嫂還在新房裡等著呢。”
成大郎一聽,立即不起哄了,也連忙幫著攔。
新娘家的人都開口了,大家自然只能給他一個面子,於是半拉半推的讓白大郎走了。
白善和白二郎一人扶著他一個胳膊送到後院,到了新房門口,白善就敲開門,將他推進去,“行了大堂哥,這會兒沒人了,你別裝了。”
一直耷拉著腦袋胡言胡語的白大郎悄悄睜開了一線眼睛。
住在一塊兒那麼久了,誰不知道誰呀?
每當白善他們出去聚會一起玩樂時,白大郎總有自己的事兒要做,基本上不是在交友就是在參加文會詩會什麼的,十次總有九次是帶著酒氣回來的。
不過今天白大郎的確喝了不少,這會兒雖不至於真的罪糊塗了,但也的確醉了。
他打了一個酒嗝,白善和白二郎立即嫌棄的離他三丈遠。
白大郎衝他們揮手道:“前面就多拜托你們了,還有,和周四哥向大哥說一聲,今日招待不周,明日再賠罪。”
說罷就把新房門給關了起來。
白善和白二郎轉身便走,下了台階才想起來,“不對呀,我們不應該要鬧洞房嗎?”
白善抬頭看了看天色道:“沒事,一會兒天稍黑些了就來鬧。”
結果白大郎根本沒給他們這個機會,大家從午正吃到了下午晚食過,大部分人都醉了,白老爺立即安排了車馬將人送回去。
白善他們倒沒醉,但還沒來得及提出鬧洞房呢,高松就給他們准備了車馬,恭送劉老夫人和老周頭錢氏等上車。
滿寶也記掛著鬧洞房呢,遲疑著不肯走,“爹,要不你們先回去,我們先去看看白師兄他們?”
白老爺立即道:“哎呀,他有什麼好看的,明兒認親就能看到了,你們先回家去吧,對了,我跟你們一塊兒過去。”
於是白老爺出面,將一行人全帶走了。
心心念念鬧洞房的白善幾個默默的回家去了,一回到家就忍不住嘆息。
滿寶道:“明天要早起進宮啊。”
白善:“認親沒我們的事兒了,唉~”
白二郎:“嫂子應該會被認親禮給我們留著吧?”
不僅他們三個,就是周立學他們也不能看熱鬧了,不過這會兒他們已經暫且放下這事,因為他們大哥周立重回來了。
他不僅人回來了,還給他們從草原上帶了好多東西回來。
周立重拿出一把黑黝黝的短刀,拔出來給他們看,眾人哇的一聲,他自得道:“這是我用兩匹緞子換的,可鋒利了。”
滿寶看了看後道:“我也有一把,上面還鑲滿了寶石呢。”
周立重強調道:“小姑,刀是拿來防身的,在上面鑲寶石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周立威跟著點頭,“本來刀還只是刀,鑲了寶石變成了寶刀,大家都想搶了。”
周立君卻道:“但值錢呀,小姑的刀多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