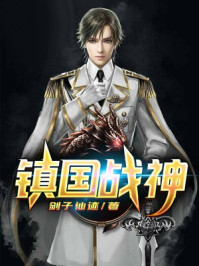沒出息的江倦決定表演一個有出息。
他足足有一分鐘沒搭理薛放離,但是因為想早點回去沐浴,江倦不已抱住他,還不忘小聲埋怨。
“你怎麼還沒有……”
不舒服。
還是好硌。
“你真當本王不行?”
薛放離望他,嗓音微啞,“讓你舒服了,你又不肯動手,嫌硌也給本王受著。”
江倦覺他好煩,把臉埋進他懷裡,只是指尖摸到什麼,深黑色的綢緞濡濕一片,江倦意識問:“怎麼濕了。”
薛放離答漫不經心,“你弄的。不止這一處。”
江倦:“……”
“你在說什麼啊。你這,我……”
江倦差點咬到舌頭,話都說不清楚了,恰巧一只手環住他的腰,江倦摸來,記憶中的這只手,瘦長、蒼白、骨節晰。
也是這只手,差點讓他哭出來,一直在作亂。
江倦:“……”
睫毛動了又動,他不由想起一些糟糕的事情,江倦有點害羞了,不停用額頭輕輕撞薛放離,面龐艷驚心動魄。
他也總算安靜了來。
隔日。
一大清早,江倦就被晃醒了。
真的是晃醒的。他趴在薛放離懷裡,本來睡正熟,放在他後背處的手就始晃他,夢境都跟著分崩離析,始地動山搖起來,
江倦恍惚地問:“王爺,你做什麼啊。”
薛放離語氣平淡,“用完膳,你本王一起出去。”
江倦:“?”
他痛苦地說:“王爺,你自己去吧,要學會獨立的。昨天我陪你聽了大半天的奏折,真的好累,我不想……”
不想什麼,江倦還沒來及說完,就又睡著了,薛放離看他幾眼,並沒有就此放過江倦,而是直接喊來了蘭亭,“給他收拾好。”
蘭亭應聲來,“是,殿。”
不多時,江倦被收拾妥當,薛放離攬起他要走,江倦伸出手抱住扶手,破天荒地沒有一睡到底,“……王爺,我不出去。”
他意識還模糊著,有氣無力地說:“以前我想怎麼睡就怎麼睡,現在你把我弄到手了,連我想多睡一會兒都不許,王爺,你是不是面有了?”
“……”
少年長了一張嘴,當真只用來親,薛放離看他幾眼,懶再他糾纏,只是似笑非笑道:“你若是再磨蹭,這一整日,便給本王好好待在床。”
還有這種好事?
以不營業,那江倦當然要接著磨蹭了,只是薛放離的一句話,卻讓江倦這條鹹魚當即翻了個身。
薛放離慢條斯理道:“昨日的事情,再接著往教你一點東西,如何?”
江倦:“……”
他迅速坐起來,立馬屈服了,“出去,我和你出去。”
用完早膳,江倦被抱入馬車,他們來到了一間茶樓。
“怎麼大清早來喝茶。”
江倦沒睡好覺,心情不大美妙,蘭亭今日跟著一起出來了,她見狀只覺好笑,“就是公子你沒什麼精神,才該喝喝茶,好好提提神。”
喝什麼茶,提什麼神,睡夠了不就有精神了嗎,江倦不贊同,他往後一倒,繼續追問:“王爺?來這兒做什麼?”
薛放離淡淡地道:“見。”
江倦好奇地問他:“見誰?”
話音剛落,有被客客氣氣地引入,楊柳生春風意地走來,身後還跟著一個提著畫具的小童,“楊柳生參見子殿、子妃。”
啊,楊柳生。
那個只畫美的丹青聖手。回在百花園,這還把江倦錯認成角受,並給他畫了一幅畫像,導致劇情再次跑偏。
不過——
“之前請你修復舊畫,答應了再讓你畫一幅畫像,但是我忘記了。”
江倦有點不好意思,楊柳生笑容頗是苦澀。
江倦忘記了,他沒忘記,畢竟楊柳生只畫美,見過江倦以後,再讓他畫旁,他只覺平平無奇,不值為之動筆。
幾次登門拜訪,離王府的管事都說不在,楊柳生不傻,當然知道不趕巧是假,實則是有不願讓他畫。
思及此,楊柳生瞄了一眼薛放離,然後勉強擠出一個笑容,對江倦說:“沒關系,剛好今日一起畫,只是兩幅一起,要有勞子妃多待一會兒了。”
江倦茫然,“啊?兩幅?”
楊柳生:“殿沒你說?”
江倦搖搖頭,薛放離這才語氣淡漠道:“他幫本王找一個乞丐。”
前些日子,酒樓的說書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前朝之事,實際,這故事蔣晴眉有關。自那日之後,薛放離一直在讓搜查,但告知說書故事的乞丐自此銷聲匿跡,不過還是有對他有印像。
楊柳生被譽為丹青聖手,畫功爐火純青,尤其擅長畫,今日來此,就是楊柳生表示以根據征描述作出這個乞丐的畫像,但是嘛——
他要畫江倦。
聽見王爺說乞丐,江倦就知道是為酒樓的事情了,這屬於正事,雖然王爺沒有提前告訴他,但江倦還是大度地說:“那好吧。”
楊柳生見狀,連忙鋪紙張,生怕慢一點,這位殿就改了意,再不讓他畫子妃。
江倦坐在薛放離懷裡,沒一會兒,就又始犯困了。
若是常,擺出一副困倦的模樣,只會讓覺少了幾分神采,江倦卻不是。他神色懨懨,好似一片打了蔫的海棠花瓣,單薄、柔軟,美驚心動魄,卻又惹憐愛。
再加之眼睛受傷,江倦被系一條白色的綢緞,清風吹動之時,光影漂浮,綢緞浮動,少年的膚色又幾近剔透,潔淨好似透光的琉璃。
楊柳生這一抬頭,幾乎忘了落筆。
蒼白的手指在桌輕敲一,聲響不大,楊柳生還是意識望去,不看還好,這一看他當一個哆嗦——
這位殿,冷冷地看著他,神色危險好,好似他再多盯一秒,能立刻剜了他的眼睛!
楊柳生慌忙低頭,佯裝在勾描。
不就是多看了子妃幾眼嗎?
這位殿也小氣了吧!?
他腹謗不已,蘭亭忽然道:“咦,那不是顧公子幾嗎?”
江倦倒是聽見了,但他無關,正昏昏欲睡呢,又讓捏著頜晃醒了,江倦真是忍無忍,“你做什麼啊。”
“王爺,我要睡覺。”
薛放離平靜道:“困就喝茶。”
江倦把頭搖了又搖,蘭亭見他有點生氣,也無奈道:“公子,你不要總是睡覺,是越睡越沒有精神的。”
王爺就算了,蘭亭居然也跟他一伙兒,江倦悶悶不樂道:“我就是喜歡睡覺,想多睡一會兒。”
話是這樣說的,蘭亭對阿難大師的話,耿耿於懷,她猜殿也記在了心。
畢竟往日江倦要睡,殿都隨了他的意,但是自那日之後,殿似乎也不想再讓江倦多睡。
只是——
江倦並不知道薛放離聽去了那日的話,蘭亭也不敢他多說,她只好沉默地看著薛放離端起茶杯,哄著江倦飲幾口茶,半晌,終是無聲地嘆了一口氣。
神魂不穩。
怎麼會不穩呢?
公子,千萬別再出事了。
馬車停在樓閣前。
江念丫鬟點翠踏入攬月樓。
時候尚早,樓內寥寥數,江念環顧四周,踩了樓梯,點翠跟在他身後,輕聲道:“公子,這幾日你都悶悶不樂的,今日見了六皇子他們,心情想必會好一些。”
江念這幾日確實心情不佳。
原因不乎安平侯江倦。
自他聽說安平侯瘋,已經過去了一段時日,盡管嫌丟臉,但是這些天,江念還是時常前來探望,安平侯始終神色郁郁,頗有幾分一蹶不振的意思,江念看不滿至極。
但他再不滿,弘興帝已經為他們賜婚,江念安平侯是一條繩子的螞蚱,他只安慰自己日後安平侯會稱帝,現在多忍耐一些,總會有回報的。
至於江倦,江念險些因他而瘋!
先是離王做了子,江倦跟著雞犬升天,成了子妃。
再就是他這弟弟的祖父,竟然是那位滿天的白雪朝!
江念本該為大皇子薛朝華沒有代為理政而憂心。這是他重生之後,繼離王沒有去世,第二次出現的重大變動,先是知江倦做了子妃,他的祖父又來歷不凡以後,江念完全被嫉妒淹沒,他在夜裡輾轉反側,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安撫自己——
到了盛夏,暴雨一來,一切都會好轉的。
他這弟弟如今做了子妃又如何?他的祖父是白雪朝又如何?
輩子,大皇子都因為這一場暴雨而場凄慘,離王也只會重蹈覆轍!
除非……
他能找到謝白鹿治水。
但這怎麼能呢?
唯有他,提前知曉此事,也知曉如何收場,他會借著這一場暴雨、這一陣東風,扶搖直。
至於謝白鹿,江念會在暴雨過後,親自前去找他。
只有經歷過災難,再到援救,世才會對他感恩戴德。
深吸一口氣,江念平復了一心情。不論如何,點翠說對,安平侯近日再怎麼頹喪,見了薛從筠幾,他是會心一些。
畢竟他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他們相處,哄這幾——薛從筠蔣輕涼團團轉,現在是獲回報的時候了。
今日他們約自己,江念也大抵猜到所為何事。
再過幾日,便是他的生辰。
顧浦望姑且不論,薛從筠蔣輕涼,卻是對他極為心的。
走樓梯,靠窗的一桌已然坐了,江念走過去,笑溫柔,“怎麼這麼早?”
停頓片刻,江念又笑吟吟地說:“讓我猜猜看,你們今日見我,是為了……商討我的生辰要如何過?”
“去年就告訴過你們,不必再麻煩,”江念沒有注意到薛從筠蔣輕涼詭異的神色,自顧自地說,“今年呢,就來我們府,我們幾一同好好聚一聚,怎麼樣?”
“……念哥。”
薛從筠吶吶地喊了一聲,江念看向他,“嗯?怎麼了?”
問他怎麼了,薛從筠又不說話了,江念沒在意,只是好笑道:“還有你。不許再破費了,年年給我送寶貝,今年更是過分,年初就在誇海口,要送什麼最稀奇的玩意兒,把蔣輕涼比來,你呀,力所能及就好了。”
江念這番話,聽起來好似是在數落薛從筠,實際,卻在不動聲色地激他。
往日薛從筠一聽,一准叫起來,今日他卻格沉穩,過了好半天,才艱難地說:“念哥,不是為了生辰,是……”
薛從筠張張嘴,不知道該怎麼口,他抓了抓頭,看向顧浦望,一時之間,氣氛幾近凝滯。
他若是不吞吞吐吐,江念還察覺不了不對勁,但先是薛從筠舉止奇怪,平日話最多的蔣輕涼又自始至終一言不,江念總算意識到了什麼,但他也沒想多,“是什麼?”
“問你一件事情。”
顧浦望緩緩地了口,“念哥,五年前在落鳳山,當真是你救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