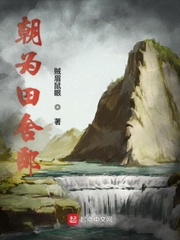第99章
幾乎是兩人回內殿的時候,空中的月色斂起滿淺輝,藏進了厚厚的陰雲中,夜風過境,帶獨屬秋日的纏綿悱惻,吹得滿院花草簌簌而動,楹窗下,幾竿青竹凌然而立,竹葉摩挲的獨特韻律低低落落,像極了三五人暗暗絮語。
須臾,豆大的雨點落下,劈裡啪啦打在琉璃磚瓦,亭台長廊上,聲勢浩大,來勢洶洶。塵游宮四面楹窗半開半闔,風向微變,掛在窗下的銀鈴便碰撞出叮鈴的短促聲響。
紅燭搖曳,垂的軟帳輕紗。
湫十絲散亂,鋪在特意縫制的正紅綢緞上,成凌亂無序之勢,像一捧顫巍巍舒展的海藻。她子稍動,滿頭青絲也跟漾動。
小妖怪膚色極白,襯鮮艷的紅,落在人眼裡,如無暇美玉。
秦冬霖長指上繞一兩縷她的烏,微微傾,慢條斯理勾她,聲音裡含輕而啞的笑意,顯得莫名危險:“真說?”
個時候,樣的話語,無疑只有一個意,湫十甚至能看到人臉上的一行大字:再說,今夜就別說了。
湫十捂了下眼,瑟縮往後挪了挪。
沒臉,說了她真的沒臉。
可有時候,她顯然低估了男人的劣性/根。哪怕人是清冷矜貴,看上去清寡欲得行的中州君主。
她越是想說,他越是要逼她說。
個時候,秦冬霖的那張臉,便成了蠱惑人的武器。
男人的唇生帶初雪的溫度,湫十的唇角一路輾轉,到耳後,到長長的鵝頸,她敏感得行,嘴有多硬,具體就有多軟。
“宋小十。”秦冬霖握她的手,繞到自己腰封上,字字滾熱勾人:“還會會?”
個“還”字,當真用得十分微妙。
湫十哼唧唧幾聲,手指勾了勾,雙頰生紅,杏目布霧蒙蒙的水意。
三次兩次成功,秦冬霖徹底沒了耐,他沉眼,執她的手將腰封解了,末了,問:“能忘?”
湫十扭過頭,沒搭理他。
但顯然,個時候,也需要她的回答。
秦冬霖的長指順白頸下那一段起伏的膩人弧度一路向下,沒入衣裙下勾了勾,湫十呼吸驀的輕了下來,杏目睜得圓圓的。
“放松一點,嗯?”男人下顎線條每一根繃緊,聲音沉得徹底。
在他再一次傾上時,湫十艱難出聲:“你等,等一等。”
秦冬霖深深吸了一口氣,凝目望她,好似在問,個時候,怎麼停?
湫十討好似仰一段嫩生生的玉頸,揚滿頭青絲,笨拙親了親男人的下巴,聲音磕磕絆絆,幾乎軟成一灘水:“輕,輕一點。”
平時膽子比誰大,到了時候,就縮進了烏龜殼裡。
秦冬霖的目光落在她窈窕的腰線,白膩的山巒,以及粉嫩生暈的少女臉龐上,想,宋湫十還真看得起他。
說停就能停,說輕就能輕。
“嗯。”他垂眼,看那絳紅的嫁衣,想小妖怪兩個月來在自己眼皮底下東躲西藏,過得實容易,他攏了下她的長,知是說給她聽,還是說給自己聽:“我輕一點。”
金風玉露,嬌吟短泣。
而事實證明,即使是在床上,秦冬霖依舊是那個一言九鼎,言出必行的好君主。
他說輕,就真的輕。
輕慢,要多磨人有多磨人。
因時間格外的長。
湫十第二次承受道的力量,那種余韻綿長的痛苦幾乎刻進了骨子裡,她眼角泛紅,終於忍受了種慢吞吞的折磨,閉了下眼,喘一聲說一聲:“秦冬霖,你別……”
她受住咬了下手指:“能能給個痛快。”
秦冬霖忍了許久,被困進退兩難,聲音啞得像話:“嚷疼了?”
湫十受住蹬了下腿,腳趾尖蜷縮起來,伶仃單薄的腳踝被扼住,秦冬霖抬起她的腿,問:“還叫秦冬霖?”
湫十被逼得小獸似的哽咽出聲,將好話說盡:“郎君。”
秦冬霖親了親她濕漉漉的額角,像征性問:“我重一些?”
回答他的,是肩胛骨延伸到後背的兩條殘忍指甲劃痕。
====
翌日明,吃飽饜足,神清氣爽的男人有一搭沒一搭擁側隆起的一小團,半晌,抬眼看了看外面的色,算時間,輕手輕腳起下榻。
蘆葦仙在外間伺候他更衣,見他滿面春風,撿了幾句吉利話說,為塵游宮裡裡外外伺候的人討了點賞頭,記起正事,正色道:“君主,兩位少君在安溪亭喝了一夜酒。”
秦冬霖早就猜到了似的,並如何訝異,穿戴齊整後抬步往安溪亭的方向去了。
下了一夜的雨,塵游宮的庭院裡,花草樹木洗盡鉛華,煥然一新,即使已經入秋,濕潤的土壤裡,也還是因為一場雨,催生出了許多才冒頭的嫩芽,一叢叢一片片,生機勃勃,看十分喜人。
安溪亭在東邊,距離塵游宮有段距離,秦冬霖到的時候,伍斐手腕上那朵顫巍巍的牽牛花正使出吃奶的力氣纏住宋昀訶的酒盞,讓它跟伍斐碰杯。
秦冬霖看了眼趴在桌上成人樣的宋昀訶,看向還算清醒的伍斐,挑了下眉,無聲問。
“關我的事。”伍斐急忙撇清責任,他搖了搖腦袋,站起來給秦冬霖倒了一杯,指了指邊七倒八歪擺放的五六個空酒壇,道:“昨夜才黑,你大舅哥就拉我開喝,二話說,一杯接一杯往下灌,知道的說是嫁妹妹,知道的還以為受了什麼莫大的打擊。”
秦冬霖一撩衣袍,在石椅上坐下,眉目清絕,春風得意,伍斐抬手跟他碰了一下,仰頭一飲而盡,道:“小十瞎搗鼓的一場可算,你若是有,怎麼也得補一場大的,熱鬧些的吧。”
多的好友,他話的意,無非就是嫌昨晚沒找到機會灌酒,想找個正大光明的機會好好灌一場。
秦冬霖頷首,道:“會在流岐山辦一次。”
小妖怪折騰想哄他開是一回事,是她的意,但他能委屈她。
也舍得委屈她。
伍斐才滿意笑了,去推了下宋昀訶的手肘,聲音裡實在沒什麼脾氣:“聽見了沒?放了沒?”
一向清潤溫和的人醉得跟灘爛泥似的,伍斐連推了好幾下,才堪堪抬起頭,眼神在四周掃了一圈,直到看到秦冬霖那張臉時,才終於撿回了幾分清明。
四目,誰也沒有說話。
秦冬霖長指敲了敲桌面,起給位名副其實的大舅哥倒了一盞酒,推到他手邊,道:“兩家定親的消息,你三百歲聽到三萬歲,還接受了?”
語氣,理所當然,毫避諱。
伍斐嘶的吸了一口氣,急忙攔在他們中間,朝秦冬霖低聲道:“行了啊你,人醉成樣了,你還總戳他傷疤干什麼。”
典型的得了便宜還賣乖麼。
宋昀訶伸手端過那杯酒,抿了一口,放下來,聲線復溫和:“秦冬霖,我只有一個妹妹。”
秦冬霖置可否,他開口:“我們幾個小到大,也算知根知底,宋湫十追我跑,你說什麼,些她稍親近我一些,你就擺臉。”
“說說看,我哪裡惹你了。”
伍斐左看看,看看,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宋昀訶也知他的性格,當即深深吐出一口氣,袖袍裡取出幾張折起的紙張,推到桌邊,一言。
伍斐難得將他副模樣,隨手抽出一張,打開一看,眼皮一跳,默默折了回去。
秦冬霖接過最上面的一張,翻開,隨意掃了兩眼,看下一張,直到將三張全部看完,才抬眼望向與小妖怪有一兩分似的宋昀訶。
白紙上面謄抄古籍上的幾段描述或記載,如妖帝曾在何時遇見哪位奇女子,共結伴闖秘境,或互生情愫,有一段露水之緣。
玉面,錦繡,甚至常在塵游宮出現的趙招搖赫然在列。
“些東西,你信?”秦冬霖問。
宋昀訶搖頭,緩緩吐出兩個字:“信。”
誠然,他們幾個自幼識,多少的兄弟,生死險境能彼交付後背,他自然知道秦冬霖是個怎樣的人,怎樣的性格。
可宋湫十是他唯一的妹妹,他沒辦法擔個。
,兩人尚可說是門當戶,流岐山雖然勢大,可兩家是世交,主城也是什麼任人欺負的小門小戶,萬一以後受了委屈,宋湫十隨時可以回來,可秦冬霖現在還多了一層君主的份。
他要是念舊情,跟你講幾分道理,若是念呢。
能怎麼辦。
有時候,聰明人和聰明人說話,點到為止,後面的深意,大家裡有數。
秦冬霖抖了抖那幾張紙,懶洋洋抬眼,一行接一行解釋:“當萬族朝聖,玉面領舞,宋小十跟我鬧脾氣,一句‘尚可’,多的半個字沒有,知道怎麼生出麼多事。”
“個給垣安奏琴——”秦冬霖啞然,深覺中州搬弄是非的人才實有些多:“我還未承載命時,她的師尊來拜訪我師尊,當時,我恰有所感,隨意奏了半段,聽見有人來便走了。”
人越走越高,只要有人想,總會給扣上一頂某須有的帽子。
“趙招搖,宋小十的朋友。”
秦冬霖捏最後那張紙,想了半,沒能想起錦繡號人是誰。
說完,他看向宋昀訶,問:“你在擔什麼?”
宋昀訶想,人難測。
止住的擔,止住的後怕。
秦冬霖道:“中州眾臣之中,朝聖殿上下,帝後與君主尊,我與宋小十意見若有分歧,她甚至可以出手攔截中正十二司頒布下去的律令。”
“長老院裡完完全全是她自己的人,她若是犯懶,我便幫她處理些事情,她若樂意,長老院就是一個鐵桶,誰也插了手,包括我。”
“而且,你們也太小看宋小十了。”秦冬霖搖了搖手中的酒盞,聲線裡帶懶散的笑意:“她三次跟我交手,兩次打成平手。”
每一字,每一句,恍若在說,只要他日後她有本分好,她隨時能拍拍屁股就走,沒人敢攔,也沒人攔得住。
話說到裡,宋昀訶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跟秦冬霖碰了一下,摁了摁脹痛的太陽穴,別有深意開口:“既然成了親,小十喚我什麼,你是是也該跟改口?”
伍斐頓時來了精神,起哄道:“改口就說過去了。”
秦冬霖涼颼颼瞥了他一眼,半晌,站起,有些尷尬撫了撫筆挺的鼻梁骨,那一聲兄長,左滾右滾,面那張小看到大的臉,愣是吐出來。
他道:“等正式成親,再說。”
====
秦冬霖回塵游宮的時候,已是日上三竿。
床榻上的人半眯眼,一見他進來,睫毛飛快顫了顫,閉上了眼。
秦冬霖腳步停了一瞬,提步走到床榻邊,在床沿上坐下,輕重捏了捏她綿若無骨的手指,上的酒香遮擋住。
“還醒?”
他將人抱往裡挪了挪,自己躺了上去,側抱她,唇瓣一下一下落在她的後頸上,本意是想小意溫存,可多時,男人的動作間,已然帶上了意亂情迷的危險意味。
湫十也顧上尷尬尷尬了,她小聲哼哼,連推了他好幾下。
秦冬霖緊慢用一只手扼了她纖細的手腕,聲音裡帶上了難以言說的誘哄意味:“再睡一會?”
說話間,他手已經輕車熟路探了下去。
湫十頓時嘶的一聲,惱羞成怒一口咬在他手腕上,急氣:“秦冬霖,你是是想和我打架?”
張牙舞爪的小妖怪,聲音軟綿綿的,實在沒什麼威懾力。
秦冬霖抽出手指,倏而笑了一聲,禁錮她的腰/肢,寸寸碾磨,眯眼喟嘆道:“我的小妖怪。”
“是水做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