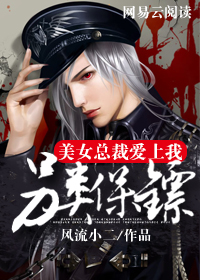藺承佑被這話氣笑了:“就為了討我的浴湯,就跑來壞我和阿玉的——”
好事?
頓了下,又改口道:“我欠的?”
“小涯。”滕玉意有點傷心,在被子裡悶悶地說,“果不為了討浴湯,是不是壓根沒想過回來我?走時就沒有半點不舍?知道我至今天天為准備果子和酒嗎?”
小涯滿不在乎地聳聳肩:“器靈的天職是護,老夫功德已滿,該回去等待下一個需渡厄的有緣了,滕娘子的酒和果子雖好,老夫也不能再賴在身邊一輩子不走不是。”
滕玉意一噎,這兒藺承佑已經重新穿戴好,回手放下簾幔將滕玉意遮得嚴嚴實實,走到案幾邊,一撩衣袍,半蹲下來量小涯。
小涯昂著小臉,眼上的綢帶紅得像火。
似乎察覺到藺承佑在觀察自己,他再次砸吧了下嘴。
這模樣簡直無賴到了極點。
“浴湯我就得給?”藺承佑哂笑,“勞白跑一趟,今晚我還偏不盥沐了。”
小涯慢悠悠抱起了胳膊:“老夫早就知道世子愛干淨。平日天天沐浴,連澡豆都是專用的,今日大禮出了那麼多汗,怎不盥沐?方才太情急沒顧得上,這回該補上了。”
藺承佑的臉燒得像火炭,冷不丁出手,便捉住小涯,不料小涯一翻身就沒入了劍身,即便藺承佑動作快閃電,也差了半寸。
“出來,我好好招待。”
小涯自是不肯出來:“老夫也不是成心來討嫌的。世子且想想,當初果沒有老夫,和滕娘子怎在紫雲樓相遇?細論起來,老夫還是和滕娘子的大媒呢。就衝著這個,世子給老夫准備一百桶洗澡水也是應該的不是……”
“是絕聖棄智的不能用,還是我師公的不能用?他們也都是有道家氣的純陽之軀。我只問,為今晚偏來討我的浴湯?”
“這個嘛……”
藺承佑斜睨劍柄,忽有點明白過來了:“也有點舍不得阿玉是不是?”
滕玉意正躲在幔帳後急急忙忙穿裙裳,到這兒,忙掀開一條簾縫往外。
小老頭慢騰騰劍裡鑽出,坐穩後用小手掩住自己的臉,頗有點赧的樣子。
藺承佑笑了:“據我知,器靈與的緣分是有定數的。時辰一到,絕不能再拖著不走,同我浴湯,是知道自己若是強行折回對自己的靈力頗有損害,可又舍不得阿玉。”
明明都狠心走到渭水了,又大老遠折回來她一面。這浴湯不是為了清洗謂的“髒污”,是為了這多出來的一趟做彌補。
小涯繼續捂著臉,嘴裡卻咕噥道:“什麼舍得不舍得的,老夫可不是婆婆媽媽的。老夫是惦記滕娘子的石凍春和蟠桃,這樣的好酒好果子別處可覓不著。”
滕玉意剛才還為小涯滿不在乎的告別傷心,這突又有點酸楚:“小涯。”
藺承佑想了想,讓小涯鑽到劍裡,起身道:“等著。”
到床邊坐下掀開床幔往裡,發現滕玉意重新穿上了外裳外裙,便拉著她下床,傾身在她耳邊說:“我出去湯。”
滕玉意紅著臉嗯了一聲。
不一兒,嬤嬤們魚貫而入。一撥負責奉熱湯和巾帕,另一撥則端著一盤盤鮮果和一壺壺美酒。
藺承佑是最後一個進來的,手裡還提著兩壺樣式特別的酒。
嬤嬤們只當是新婦吃喝,安置東西時,不免含笑量坐在床畔的滕玉意。
藺承佑卻道:“這一天我也沒好好吃東西,這兒早餓了,干脆好好吃喝一頓再睡覺。”
說著屏退嬤嬤們,把酒放到案幾上,清清嗓子道:“我去盥洗了。”
滕玉意沒好意思回視藺承佑,只應了一聲,走到案幾前坐下,敲敲劍柄:“出來。”
小涯重新鑽出,滕玉意歪頭端詳小涯:“這樣我有點不習慣,把綢帶摘下來吧。”
小涯摸索著扯下綢帶,冷不丁到面前的盤盞,新鮮果子琳琅滿目,各色各樣的酒水也有七-八種。那雙綠豆眼頓時綻出精光,搓了搓手說:“唉嘿嘿,世子可大方,老夫這趟來得值。”
滕玉意為自己和小涯斟上一杯酒:“果沒有相伴,我也不能渡過這場災厄,本為沒機了,還好今晚補上了。”
說著,鄭重其事舉起酒杯:“小涯,這杯酒,我敬。在我最困頓最黑暗的那段時日,幸得有為我引路。”
小涯忽把頭扭向一旁,不接話也不喝酒,滕玉意好奇傾身,意外發現小涯眼眶有點紅。
“小涯……”
小涯胡亂揉了把眼睛:“來的時候也不知在哪兒碰上髒水了,害得老夫眼睛疼。”
說著轉過頭捧起那一小杯酒,咕嘟咕嘟一飲而盡。
“這是酒?聞著比石凍春還香。”小涯意猶未盡地眯了眯眼。
“換骨醪。”滕玉意說,遙想當初,這兩瓶換骨醪還是她為了感謝藺承佑的救命之恩送給他的,樣子藺承佑一直沒喝,今晚為了招待小涯倒是痛快拿出來了。
滕玉意感激地瞥了眼淨房的門簾,這世上怕是沒有第二個比藺承佑更懂她的了。
“此酒不易得,我和世子都沒舍得喝,滋味還不錯吧?”滕玉意幫小涯斟上第二杯。
小涯感慨萬千:“止不錯,簡直是瑤池仙釀。在滕娘子身邊這一年雖說沒少受驚嚇,但美酒算是實實喝過癮了,到了下一任身邊,也不知道能不能有這際遇。”
說話間瞥滕玉意裙擺後方的紅繩,小涯愣了愣。
滕玉意順著回頭一,紅繩本該系兩頭,可沒等她幫藺承佑系上另一端小涯就冒出來了,那一頭還系在她的腳踝上。
“這是……”門簾一動,藺承佑盥洗出來。
他新換了件簇新的朱色錦袍,鬢邊仍濕漉漉的。
滕玉意忍不住瞄了瞄藺承佑,他手裡拿著個囊袋,料著是浴湯,奇道:“不干脆讓小涯到浴槲裡供奉。”
藺承佑撩袍坐下,順手把囊袋裡的浴湯傾瀉到一個琉璃盆內:“那可是我和的浴槲,怎能讓旁用?”
這話讓面紅耳赤,小涯卻眉開眼笑,縱身跳入琉璃盆中,歡暢地在盆中游來游去:“這麼多浴湯夠老夫洗好幾回了。”
藺承佑拿過滕玉意手裡的酒壺給自己斟了一大杯酒,一本正經對著小涯舉了舉杯:“小涯,衝著幫阿玉渡過最難熬的那段時日,我也該敬幾杯酒。說是青蓮尊者當初用玉笏制成做成的法器,專為有緣渡厄,道觀和佛寺禁錮不住,一蟄伏便是數十年甚或上百年,今夜我們夫妻與君一別,今生怕是再無緣相了。大恩不言謝,這一杯,藺某干為敬。”
這是藺承佑頭回用此敬重的口吻同小涯說話,此話一出,一股濃濃傷感的離愁在青廬裡彌漫開來,小涯也不瞎三話四了,默默游到盆邊抱住酒杯慢慢酌。
滕玉意連酒也不喝,只留戀地望著小涯,忽道:“對了,說到挑選,我還有件事沒來得及問呢。菩提寺的慧仁和尚告訴阿爺,能來到我身邊,是因為我阿娘……”
她哽了下,自經歷過生離死別,她早已懂得體恤阿娘的苦心,但每回提到此事時仍不免傷感,過片刻,勉強穩了穩心神:“我和阿爺不只背負一個的詛咒,不破咒,注定一次次死於非命。阿娘第一世沒能成功幫我和阿爺渡厄,第二世才把求到了身邊。上一世的事我雖猜得八九不離十了,但未必就是相,今我災厄已渡,總不怕泄露天機了,能不能告訴我上一輩子殺害我的,還有幫我借命的都是誰?”
小涯擺擺手道:“不成的,不成的,這話說出來,老夫再洗一百次世子的浴湯也不管用了。”
似是怕滕玉意和藺承佑追問,小涯冷不丁琉璃盆裡爬出,抖了抖身上的水,精神矍鑠跳到劍上:“喝也喝了,吃也吃了,告別也告別過了,老夫在滕娘子身邊整一年了,再賴著不走對我都不好。世子,勞煩把我擱到貴府的井邊吧,方才我瞧過了,那井就在不遠處,天下水源相通,老夫自有法子回到渭水。滕娘子,老夫一向只出現在需渡厄之身邊,千辛萬苦破了錯勾咒,往後定平安順遂的,今夜一別,我後無期!”
說罷,一狠心鑽入了劍身裡。
滕玉意傾身抓向小劍,到底遲了一步,她望著那柄瑩透安靜的小劍,剎那間淚濕了眼眶,過去這一年,她經歷了很多事,結識了很多,這個最初給她瓊琚的小兒,到底離她而去了。她心裡滿是不舍,扭頭對藺承佑說:“我想送送小涯。”
“那我帶出去。”
“可我是新婦不能出青廬。”
藺承佑笑道:“阿玉,是個守規矩的嗎?前都過得隨心欲,嫁了我難道就該縛手縛腳了?半個時辰前我就讓把青廬附近的都驅散了,這兒出去不必擔心撞。”
滕玉意破涕為笑,上前伏到藺承佑肩膀上,藺承佑把小涯劍遞給滕玉意,轉頭身後說:“我之間哪有那麼多規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萬事多有我護著,再任性的事我都陪做。”
滕玉意的笑容心底攀到臉上,懶洋洋聞著他脖頸上的清冽氣息,親昵地嗯了一聲。
藺承佑忽想起什麼:“記得那回和李淮三對質時說過謂‘上輩子’的事,上輩子是不是也想嫁我來著?是不是一早就知道我有多好了?”
滕玉意一默,忙否認:“胡扯。李淮固的話也信?壓根沒有的事。”
藺承佑嘖了一聲:“上回都承認了,現在倒是不肯認賬了?細細告訴我當時是怎麼謀求我的,我又是怎麼對說不娶的。我保證不笑話。”
滕玉意環緊他的肩膀,閉著眼睛嘟噥:“當時只了一半,實話告訴吧,上輩子也是愛我愛得不行。”
“的?”藺承佑狐疑。
“的。”滕玉意點點頭,語氣十分篤定。
正藺承佑言,青廬外連個走動的下都不,兩到了口井邊上,滕玉意取出小涯劍放到井台上,萬分不舍地撫了撫劍身:“走吧。”
不料劍身一燙,小涯又鑽了出來,他叉手站在井邊,一指滕玉意裙邊的紅繩:“唉,老夫原本不想說的。瞧,們不是都弄來了雙生雙伴結嗎?這可是狐仙為了求偶傾注大半靈力煉制的,據說能窺前塵影事。告訴們一個法子,們將其系在腳踝上,若是上輩子們之間有牽扯,總能在夢裡窺相。”
藺承佑和滕玉意同時一愣,小涯劍卻迅速滑入井中,撲通一聲,濺出一點水花,接下來水面回歸平靜,仿佛什麼也沒發生過。
***
回到青廬裡,滕玉意仍有些悵惘。
藺承佑牽著滕玉意走到床邊,坐下後二話不說撩起她的裙擺。
這回滕玉意沒再躲,只紅著臉任藺承佑研究她腳踝上的那根紅繩。
“小涯這樣的上古神劍,必定知道不少幽冥之事,我只是沒想到,這根紅繩還有這作用。”藺承佑抬眸瞅了瞅滕玉意,忽笑道,“這回總算有機知道上一世我是‘愛愛得不行’的了。”
滕玉意有點心虛,下意識就把腳縮回,而實在舍不得這雙生雙伴結的好寓意,只得任他擺弄,口裡哼了聲:“小涯慣喜歡糊弄,他的話可做不了准,再說夢還是反的呢,即便夢什麼,那也未必是。”
藺承佑的笑容帶著些玩味:“滕玉意,我怎麼覺得很怕我窺前世之事。說,方才是不是吹牛了?”
“我吹什麼牛?”滕玉意,“難道現在不是對我愛之若渴嗎,那麼上輩子愛戀我又有什麼可稀奇的?”
話音未落,唇上一熱,藺承佑傾身將她吻住。
滕玉意的心靜止在了胸膛裡,藺承佑身上的溫度似能把融化,一下沒能支撐住,同他一起倒回到床上,藺承佑的呼吸和吻一樣滾燙,在她耳畔說:“原來也知道我愛若渴……”
他的吻,落到她的唇瓣、脖頸……一路往下。
他的手,順著她的腳踝往上探入她的裙底。
滕玉意的眼圈一燙,那股飄飄忽忽的熱氣把她一下子帶到了雲端,下一瞬,又像是跌落到浩瀚洶湧的海浪中。那高高的浪裹住她的身軀,把她卷過來,推過去,她羞赧,呻-吟,顫抖,躲閃,藺承佑對她有無限耐心,熾熱且隱忍,追逐又體貼,終於,在那聳動的水浪中,她宛一朵嬌盛的花,一寸寸在他身下綻放。
幔帳裡,一傳出滕玉意的輕嗔和低泣聲,一兒又傳藺承佑牙疼似的“嘶嘶”聲。
“別咬著我……”
滕玉意顫聲:“……不許動。”
“好,我不動。阿玉,我忍不住……啊……松口……咬疼我了。”
“……我才疼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帳內終於不再“架”了。
滕玉意渾身是汗,迷迷糊糊感覺藺承佑在幫自己擦拭身體,她羞得不願睜開眼睛,任他擺弄一晌,推開他,自顧自蜷縮成一團躲到床裡。
藺承佑替滕玉意蓋上被子。
滕玉意剛閉眼,懷裡忽多了個布偶,藺承佑後頭環住她,吻了吻她的腮幫子:“那兩個婢子說,睡覺時離不開這個。”
滕玉意摟緊布偶。
“阿玉……”藺承佑撥開她腮邊濕透的發,“……還疼麼?”
滕玉意眼睛閉得更緊了,想起自己痛極的時候曾咬過藺承佑的肩頭,也不知咬得重不重,她踟躕了一,到底轉過頭,微微抬起一點眼眉,藺承佑把玩著她肩上的一縷青絲,似在琢磨什麼。
他生龍活虎,哪有半點疲憊之態。
滕玉意飛快掃一眼藺承佑的肩膀,又飛快把目光移開,之前他的肩背露在外頭,現在又重新穿上了寢衣,傷口被擋住,也沒法仔細端詳。
“在瞧什麼?”藺承佑回眸笑問。
“還疼嗎?”
“疼。”
莫不是咬重了。滕玉意忙放下布偶,探頭向他的肩膀。
“親眼瞧瞧就是了。”
滕玉意瞥他一眼,輕輕挑開他寢衣的衣領,明明只是確認他的傷口,這動作卻讓兩個的臉都紅了。
果,藺承佑的右肩上留下了一個清晰的牙印,而很淺,過兩天就消了。
“騙子!一點也不重。弄得我才疼呢。”
藺承佑一眼不眨望著面前那張美若蓮花的粉面,笑道:“是覺得不夠重,那再咬我一口?”
他的胳膊正好在她唇邊,滕玉意毫不客氣張口就咬,而只輕輕地含住,並不肯用力咬,抬眸對上他眼睛,他含著笑意,眸色深得似有個漩渦能把她吸進去,她推開他,閉上眼睛:“我乏了,我睡了。”
或許是太困乏,這一閉眼,她很快就睡著了。
等到滕玉意再睜眼,已是次日拂曉。
她怔忪了一,再一轉眸,就到那張熟悉的側臉,桌上紅燭幾乎燃盡了,但燭光仍能清楚地照亮身邊的輪廓。
滕玉意還是第一次到藺承佑熟睡時的樣子,忍不住悄悄支起胳膊,垂眸量藺承佑。
藺承佑睡覺時氣息很輕,燭光落在他高挺的鼻梁上,為他那俊美飛揚的五官添了抹清雋柔和的色彩。
昨日洛陽風塵僕僕趕回,路上那樣顛簸,他一定累壞了。滕玉意靜靜支頤端詳藺承佑,耐心等藺承佑自己醒來,忽又想起什麼,悄悄掀開寢被往下,紅繩仍系在兩的腳踝上,但昨晚她並未夢前世。
藺承這張平靜的睡臉,也不像夢了什麼。
滕玉意疑惑地重新掩上被子,繼續托腮端詳藺承佑,望著望著,突發現藺承佑寢衣的前襟,靠近胸口的某處布料著比別處深,像是被水洇濕了似的。
滕玉意有點好笑地想,這塊水漬……該不是藺承佑睡覺時流口水吧。
腦中又冒出個念頭,等等,果是他流的,位置未免太靠下了……這說不定是她夢中流的。滕玉意的笑容凝在臉上,這是被藺承佑發現,少不得取笑她一通。不行,必須趁他醒來之前把那塊擦干,橫豎簾外就有備用的巾櫛……
這樣一想,滕玉意便屏住呼吸藺承佑身上越過,怎知這時候,腰後忽一緊,沒等她反應過來,藺承佑就一個翻身將她壓在自己身下。
“別擦了,我早就瞧了。”
滕玉意錯愕,藺承佑的眸子敏銳清澈,哪有半點睡意。兩個四目相對,都有點不好意思。
“、早就醒了?”
“睡得熟,沒忍心吵。”藺承佑指了指自己前襟上的口水,“滕玉意,雖說我早就知道睡覺愛流口水,但我沒想到的口水能淌到我寢衣上。
“我怎麼不知道我睡覺流口水?”滕玉意急著否認,“說不定是自己流的,偏賴到我頭上。”
藺承佑一笑:“昨晚我可是親眼著貼過來的,我倒是想躲開,可死活抱著我睡,我差點被擠到床下去。”
“胡說……”滕玉意睫毛一顫,“我睡覺時只抱著我阿娘的布偶。”說話時目光胡亂一掃,卻發現小布偶歪躺在她的枕邊。
這下沒話說了。
“總不能賴到布偶頭上。”藺承佑盡情嘲笑滕玉意,一低頭,吻她露在外頭的白玉般的脖頸。
滕玉意又羞又癢,笑著躲閃:“我就是愛流口水,是嫌棄我,那去別處睡好了。”
“那可不成。日後在哪兒睡,我也只能在哪兒睡。”
忽外頭傳來一陣腳步聲,阿芝歡快的笑聲在青廬外響起:“阿兄,嫂嫂,們起來了嗎?”
又有下道:“大郎、玉娘大喜。關公公來傳宮裡的旨意了。”
兩一愣,阿芝絕不無故來吵他們,樣子時辰已經不早了,只怪青廬昏暗,一時不出天色。
滕玉意面紅耳赤,忙推開藺承佑下地,剛一動,身子差點栽到床底下,虧得藺承佑拽住她的胳膊,及時把她拉回床上。
兩低頭一,卻發現兩個的腳踝上都系著紅繩,若是一個下地,另一個勢必也得跟著。
滕玉意忙解開紅繩,藺承佑攔住她:“出青廬的時候才能解開這紅繩。”
滕玉意狐疑:“那怎麼辦?”
藺承佑索性抱著滕玉意下床,讓她環住自己的腰,順勢讓她將雙足踩在他的腳背上:“這不就好辦了?”
說著揚聲對外頭說:“知道了,阿兄同嫂嫂說話,讓采蘋嬤嬤帶到花園玩去。”
兩個都赤著足,滕玉意被藺承佑帶著一步步挪向淨房。
滕玉意不得不環住藺承佑的腰,同時仰頭望著藺承佑,還不好意思,末了干脆支使他:“我渴了,我喝水。”
藺承佑又改而抱著她退向案幾,邊退邊低頭笑著端詳她:“別笑,腮邊是什麼,待我再受累幫洗把臉吧。”
***
上房裡笑語喧騰,成王夫婦、藺承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舅舅舅母全都在座。
成王妃笑著說:“方才們也王爺說了,濮陽等地陸續上奏,說當地有妖異作亂,奏請朝廷即刻派僧道前去降妖,正好佑兒帶玉兒去南陽做法事,緣覺方丈也同行,王爺就同師兄說,不越性把東明觀的五位道長和絕聖棄智都派上,讓他們一群熱熱鬧鬧同去降妖,路上也好有個照應。”
舅母王應寧微笑道:“倒是個好意,趁這機玉娘可跟大郎好好在外頭游山玩水。”
阿芝來勁了:“那我也去。”
藺效覷著女兒:“去做什麼?”
阿芝撲到父親懷裡:“同哥哥嫂嫂一同捉妖呀。”
歡笑聲中,滕玉意同藺承佑進去行禮,一進屋,便覺四面八方投來視線,那種慈愛的目光讓心中發暖。
藺承佑拉著滕玉意到正中跪下,笑著說:“兒子帶新婦阿玉給爺娘請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