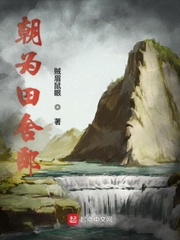晚上之前。
封凌趁著厲南衡還在裡面監督那些學生的動作,走出教室直接去找主教練。
“主教練,你晚上別去體育館。”封凌直接說。
主教練今天的課都已經結束了,已經換過了衣服,准備等著他們一起去體育館,聽見她這話,直接抬頭看她:“怎麼?怕我打不過他?”
“不是,我只是認為沒有必要去打,什麼比劃不比劃的,毫無意義,你能明白我的意思麼?”
主教練站在桌邊沒動,看了她一會兒才說:“意思是無論我是否能打得過他,你對我也不會有任何感覺,就像對陳北傾那樣的漠視態度一樣,僅僅因為我跟你是同事的關系,所以你一直很客氣沒有太疏遠,但如果我因為不小心對你暴露出的感情而跟厲南衡去比劃一場的話,你會很懊惱自己處在這樣的事件當中?”
封凌:“……既然你知道,為什麼還要去打?”
主教練笑笑:“阿零,你不懂男人的心態,輸就輸,贏就贏,怎樣都好,但是既然喜歡同一個人,就該用男人的方式去解決,就算我知道自己打不過他,但至少我爭取過。”
“還有。”主教練挑眉道:“你和他的很多功夫路數看起來都差不多,雖然厲南衡最近在這裡也僅僅只是幫你帶一帶那些學生,也沒怎麼出過手,可我能在一些蛛絲馬跡和身手動作還有出手的習慣裡看得出來,你的這點本事,該不會都是他教的?”
只有這種有功夫底子,能細心鑽研看得出來別人功夫路數的人,才能在這樣很小的蛛絲馬跡裡看出來這一切。
主教練雖然的確不一定能打得過厲南衡,但他畢竟在這行裡做了這麼多年了,別人隨便出手的一個動作他都能記得住對方出手的方式。
所以雖然他這些天沒有因為厲南衡的被“收留”而說過什麼,但顯然什麼事情也瞞不過他的眼睛。
“我有一位朋友在洛杉磯警局工作,跟我說過關於xi基地的事,那天我偶然因為厲南衡的名字而覺得像是在哪裡見過,特意結合了洛杉磯那邊的搜索詞一起查了查,雖然關於厲家的事情在網絡上查不到多少,關於xi基地的事也大都是保密的,沒有多少能查得到的東西,但終究還是在xi基地的法定負責人那裡看見了厲南衡的名字。”主教練邊說邊盯著封凌看起來仍然平靜無波的臉:“他是xi基地的負責人,那你是什麼人?之前我一直看你的身手不錯,年紀又這麼小,很好奇你有怎樣的經歷,現在不得不懷疑,你是不是xi基地的成員出身?”
“是。”
面對著這些證據確鑿的話,封凌也的確是沒什麼好遮掩的,畢竟就算是撒謊說不是,他心裡也明白她是在撒謊。
所以還不如坦然些。
“xi基地竟然會收女人?”
“如果xi基地肯收女人,我現在也不會跑到波士頓。”封凌沒解釋太多,只說了這麼一句後,想了想又道:“那些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但既然你猜到他的身份了,就不要去打了。”
主教練卻只是笑笑,又看了眼不遠處的教室,再看了眼手腕上的時間:“我等他。”
封凌皺眉:“還要打?”
“為什麼不打?”主教練挑眉。
封凌:“……”
……
晚上。
理工大學內部體育館。
兩個男人的約鬥,在封凌的眼裡覺得實在是太幼稚太莫名奇妙,她實在想不通,兩個都二十多歲的大男人,厲南衡平時不屑與人爭鬥,主教練平時也是行事穩重的類型,可竟然一拍即合的真的說打就跑過來要打一架。
她懶得去體育館裡看,直接開車回家,進了家門後就直接將門反鎖,懶得理會那兩個神經病。
而體育館裡的兩人根本也沒打多久,主教練知道自己打不過,一直在防守,厲南衡也看得出來對方是在試探自己,出手很敷衍,最後耗時耗力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打出什麼結果來,兩個身高腿長的男人最後懶得再打了,雙雙躺到了體育館的地上喘息,沒再打,也沒說話,只躺在那裡,看著體育館上方的燈。
“能有幸跟xi基地的老大在這裡比劃一場,還真是我的榮幸。”主教練一邊看著上面的燈一邊喘息著說:“我還以為你想直接來這裡廢了我,沒想到竟然一直在放水。”
厲南衡也只是喘了幾下,躺在那,不以為然的哼笑:“知道的還不少。”
“我也是剛知道你是xi基地的老大,最開始的確很震驚,但想想阿零的身手就已經讓人很驚嘆了,你的出現還有xi基地的身份只會讓我終於能理解她的身手究竟是在哪裡學來的,不愧是大名鼎鼎的xi基地,連個小姑娘都能學來這麼好的身手,如果我想慕名而去的話,不知道我這麼大的年紀還收不收?”主教練邊說邊笑。
厲南衡沒答,只淡看著上方的燈。
空氣裡陷入一陣靜默,最後主教練起身,坐在原地,看了眼空蕩蕩的體育館,說道:“雖然我不知道阿零為什麼會離開你們的xi基地,也不知道你們的過去,但在我的印像裡,一年半之前,她剛到我們武道館的時候,是個安靜沉默到讓我們很多人懷疑她是不是有性格缺陷的人,後來發現她上課時教那些學生的方式雖然嚴格冷漠,但又做的很細致,教的很好,久而久之我們才確定,她只是性格不喜與人交流,也從來不喜歡說廢話而己,而且她的防備心很重,不會跟誰走的太近,那時候除了上課的時間之外,她自己都一個人呆著,我們去找她說話,她也只是靜默的看著,一點要融入裡的想法都沒有,孤僻的像個獨行者,我是從那時候起開始注意到她的,真的是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性格的女孩子。”
主教練笑了笑之後又說:“又莫名奇妙的覺得,她的沉默之下隱藏著的一定是受過的傷和滿身的刺,否則她不會有這麼厚的鎧甲,不會拒絕所有人的靠近,我一直在想,她究竟是有什麼樣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