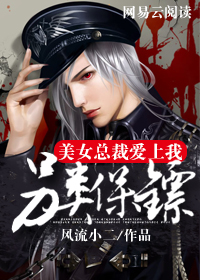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李道士現在總算明白了這句話,雖然他好不容易找到了魔道的線索,但是在此之前,他還得先做上一件事,就是幫公主殿下制一副畫。
沒錯,六公主的要求就是這麼古怪,在人間繪上一副畫,而這,便是她選擇出入天人二界的方式。
雖然這看起來有些幼稚,但是上界仙法玄奇,對方既然如此做了,必然是有一定的把握才對。
但麻煩就麻煩在這幅畫上,無論是道士的前世還是今生,對於畫藝,那都是通了九竅,一竅不通的水准,能把小雞化成兩圈一豎,那已是巔峰之作了;而這幅畫的復雜程度,明顯是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
“道長,你這幅飛天仕女圖別的倒也罷了,唯獨神女的這雙眼,已經是有了十分的靈韻,普通匠師的水准,絕對是描摹不出,請恕老朽無能為力。”
說這話的,是人送外號畫中骨的老畫師,正所謂畫皮畫肉難畫骨,所以他這境界已算是相當的高,按照道士的理解方式,至少一幅畫賣上百兩銀子不費吹灰之力,要不是有青城道長的名號,還真是難得見上一面,他都這麼說,道士也真是有些頭疼。
“或許京城第一名手趙端陽有此本事,這位百年一出的畫聖正在姑蘇游歷,似乎這幾日就要離開了——”
話音未落,卻已不見了道士的身影,老畫師不由的撫須感慨,“青城道長不愧是青城道長,竟有一日千裡的本事,現在怕已在姑蘇城外了吧。”
事實上,這種一日千裡的本事,道士是沒有的,他只是先施展隱身術,然後化作吊睛大虎,玩命的向姑蘇飛去,在累的跟狗一樣之前,終於趕到了。
“媽了個蛋,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學會一種道家遁術,不然這種趕路方式,就算是道爺也受不了啊,”李道士累的直喘氣,在夕陽西下之前,他終於趕到了姑蘇,也就是蘇州。
江南有六府,蘇州、杭州、淞江、嘉興、寧國、洛都,這蘇州好山好水好畫,文氣之重,還要在洛都之上;道士張開天眼,只見白氣瑩瑩,文光璀璨,從城內城外飄出,爛如錦繡,高有七八丈,短有兩三尺,數量之多,難以計數,這些都是文人的文氣,道士在上空盤旋一二,找了股光芒最亮,形如墨卷長軸的,飛了過去。
在道士的印像中,這文人,也就是古代的書呆,畫畫要是畫的不錯,那基本上文化水平也低不到哪裡去,所以這很有可能就是趙端陽的那一股。
翠竹成林,點綴綠意一片,白桃兩三,更加片片生機,有道是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桃竹林,便是寒山寺外最大的一景,此時此刻,就在這桃竹林中,一個三十出頭的文士正在駐足賞景,不過他欣賞的方式跟普通的游客不同,別人都是賞花賞葉賞景,而他則是賞根賞杆,似乎對於它們破土的方式很感興趣。
“你就是趙端陽?”
文士聽得聲音,回頭一看,卻見一個青年道士不知何時出現在他的身後,訝然道:“正是趙某,閣下可是青城道長李長生?”
“咦,你認識我,”道士更加驚訝,他本還在琢磨著如果對方是趙端陽的話,怎樣才能忽悠對方免費幫自己畫畫,可讓他沒想到的是,對方居然認識自己,難道道爺的名聲已經傳到京城了嗎?
見對方這番表情,趙端陽連忙解釋道:“實不相瞞,在下與杜書杜慕文乃是至交,他曾與我說過道長的相貌,是故只是初次見面,便能識得。”
“你居然認識杜書呆,那就更好辦了,幫道爺繪一幅畫吧,”李道士開門見山,這年頭流行的就是殺熟,朋友的朋友,那不就是坑友嘛!
趙端陽只是稍一愕然,便點了點頭:“自是可以。”
出乎道士預料的,這趙端陽居然是個知書達理,人情通透的人物,他本以為像這種文藝圈人士,基本上都會留著小辮子,蓄著大胡子,渾身邋裡邋遢,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氣勢,看來這種殺馬特的風格也不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嘛。
而據他所說,杜書呆自從在京師學了半年的畫後,就又游歷江南江北,現在不知道正在哪個勝景名跡中窩著呢,而且據信上所說,他有一個叫阿顏的小娘子作陪,漫長旅途倒也不甚寂寞。
“阿顏!?”
“難不成道長認識這位姑娘?”趙端陽問。
“認識倒是認識——”李道士抽了抽嘴角,只不過這只漂亮書妖為了救杜書呆,不是已經死了嗎?難不成杜書呆得了妄想症,還是說,他被鬼魂纏身?
好在令道士心安的是,按照對方的說法,這書呆子依舊是活蹦亂跳,暫時不像是要掛的樣子,這就好辦,以後再見面時,幫他看一看便是。
六公主對於這幅畫的要求很古怪,對於紙質筆墨都無甚要求,唯獨要長三丈,寬兩丈,單是這個,便難倒了九成的畫師,便是外行也知道,這大畫向來比小畫難畫,不僅要一蹴而就,一點點疏忽,全部苦功便都成了無用功。
而事實上,當道士把從上界帶下來的畫軸展開之時,這位京城名手幾乎第一時間沉浸在了畫中世界中,宮闕寶閣,飛檐朱宮,無邊的仙雲,以及在畫中的那七個飛天仕女,好半晌才道:“這畫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李道士雖然不明白對方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這幅畫絕對不是凡品,不然怎麼可能穿過天人二界的間隙,而且想想那一夜六公主是如何把自己召上來,那本身就有很大的疑問。
“做此畫,我需要三天的准備,以及七天七夜的繪制時間,”趙端陽頭也不回的道,直到此時,這位畫中大家才露出了真正‘文化人’的氣質來,那種執著、狂熱的感覺,哪怕只看背影,道士都能感受的到。
而且十天的話,倒也不是來不及。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畫出殘陽落,書畢天地昏。這是文人夢寐以求的四種成就,而在漫漫歷史長河之中,發生這種事的概率相當不高,說不定還不如修士成仙的概率,而眼下,道士很有可能有幸見得這種場面。
三天之後,也不知這趙端陽做了何等准備,再出現時,卻有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勢;老兄,我只是請你去畫幅畫而已,你做出一副要上斷頭台的表情是要怎地?
“一個畫師,也許一輩子都做不出一副讓自己滿意的畫作,十年前,我做出了一副,沒想此生還由此機遇,再做出一副,道長,請你放心,這一次,便是嘔血三升,我也會做出來!”
李道士目瞪口呆的看著對方,文化人的想法他真是搞不明啊,只是做一副畫而已,要不要這麼誇張?
趙端陽把作畫的地點選擇在了寒山寺後山的石壁上,空石流溪,白璧無瑕,卻是最適合作畫的場所,一筆、一墨、一硯,便是足矣。
處於對方的反常表現,李道士並沒有去看對方的作畫,而是盤膝坐定於溪上的一塊大石上,雙眼似閉非閉,精氣神感受著方圓十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竹,他有預感,繪制這畫,並不像表面上的這般簡單。
而事實上,他的猜測是對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