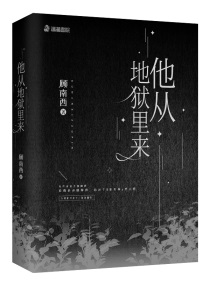“嗯,昨天去的。”
她著急問道:“那你抄了多久的經書?”
“沒多久。”戎黎說,“寺裡的老僧見我腿不好,網開一面了。”
她不信,掀開被子去看他的腿。
下午他說腿疼,她以為是他想要她主動,才故意那樣說,原來是真疼,怪不得在浴室待了那麼久。
她把手覆在他膝蓋上,那裡還是腫的,淤血沒散,青了很大一片:“你不是不信嗎?”
掌心下的皮膚在發燙,她眼眶熱了。
他說:“現在信了。”
她跟他說過,她姑姑曾經為她求過一枚,去年車禍的時候,那枚平安扣碎了。
或許善良可愛的人真的能得到庇佑,所以在佛堂的時候,他沒敢提自己,甚至會下意識低頭,怕一身罪過會惹怒神靈。
“是不是很疼?”徐檀兮怕弄疼他,不敢用力,輕輕地按摩他膝蓋旁邊的穴位,“要不要吃止疼藥?”
戎黎下午吃過止疼藥了,剛剛也吃了,他撒謊:“不用吃藥,我在浴室熱敷過,已經沒那麼疼了。”
她俯身湊近,笨拙地吹著他發燙的膝蓋,頭發從她耳邊滑落,輕輕掃過他的皮膚。
又軟又癢。
也不知道是止疼藥起了作用,還是她起了作用,好像不那麼疼了,他扶著她的腰,把她撈進懷裡,她生怕撞到他的腿,連忙小心翼翼地往後挪。
“心疼了?”
“嗯。”她聲音悶悶的,很心疼。
戎黎抱著她躺下:“那說點好聽的哄哄我。”
她還是害羞,紅著臉在他耳邊小聲地說。
次日,天晴,杏雨梨雲,春色芳菲。
秦昭裡回南城了,她約徐檀兮和周青瓷在天方娛樂城小聚。都是女孩子,徐檀兮沒讓戎黎跟著。
晚上八點,娛樂城裡正是熱鬧時候,迪廳裡人很多,動感的音樂刺破耳膜、割斷神經,使人在喧囂裡發狂。
今晚的dj是姜灼。
場子裡很熱,他穿著一件黑色短袖,只戴了一只耳機,右手在混音台上,左手高高抬起,隨著音樂在控場。
氣氛熱到爆炸,他頭上的汗流得很凶。
像床上的他,性感得一塌糊塗。
“確實。”周青瓷是公眾人物,卡座的位置故意選得很偏,她鴨舌帽沒摘,半張臉都藏在昏暗的陰影裡,“有送他出道的打算嗎?”
秦昭裡想也不想:“沒有,娛樂圈太亂了,不適合他,他主修大提琴,將來是要當音樂家的。”
語氣別提多驕傲。
周青瓷哪能看不出來,她這是走心了。
“你呢?”
“什麼?”
周青瓷故意調侃:“想當音樂家夫人嗎?”
她嘴硬:“大總裁不香嗎?”
估計沒小嬌夫香。
周青瓷笑了笑,沒戳穿她。
“徐小姐。”
迪廳的經理親自端了壺茶過來:“您的茶。”他把茶壺放下,態度很恭敬,“請您慢用。”
徐檀兮道了聲謝謝。
“你來酒吧喝茶,”秦昭裡喝了口酒,拖著三分醉意的調子,“杳杳,說不過去啊。”
徐檀兮倒了杯茶,湊近輕嗅,小飲一口:“我酒量不好。”
秦昭裡拆穿她:“是你家那位不讓喝吧?”
她低眉淺笑,沒有否認,迪廳裡很吵,她安靜地喝著茶。
秦昭裡和周青瓷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徐檀兮話少,多數時候只是聽著,偶爾被問到,才會應上幾句。
隔壁卡座也是女孩子,聊天的聲音很大。
“那個dj不錯。”
這句話被秦昭裡聽到了,她抬了抬眼皮。
說dj不錯的那個女孩年紀不大,穿了一身名牌,五官應該動過,漂亮是漂亮,就是缺了那麼點味道。
女孩的同伴問:“有興趣。”
“有點兒。”
同伴說:“對他有興趣的人不少,不過我聽說他有金主了。”
“誰啊?”
“這就不清楚了。”
女孩盯著正在打碟的姜灼看,方才沒注意,這才看見他耳朵後面有東西:“他耳朵上戴的是什麼?”
另一個同伴說:“助聽器吧。”
女孩搖了搖杯子裡的酒,興致勃勃:“居然還是個殘疾人,我還沒玩過殘疾人呢。”
咚的一聲。
是酒杯底座砸在桌子上的聲音。
“罵誰殘疾人呢?”秦昭裡站了起來,嘴角掛著笑,有幾分漫不經心,看不出來生氣。
但徐檀兮知道,她生氣了。
女孩在隔壁卡座,看不清人,她言語挑釁:“你誰啊?”
秦昭裡下巴一抬,指姜灼:“他金主。”
女孩還太年輕,不知道天高地厚,意味深長地哦了聲:“殘疾人玩起來過癮嗎?”
一口一個殘疾人,這是缺少社會的毒打。
秦昭裡伸手去拿酒杯。
周青瓷抓住她的手,搖了搖頭:“人多眼雜。”她的身份不適合在公眾場合下大動干戈。
“口罩有嗎?”她問。
周青瓷猶豫了幾秒,從口袋裡摸了副沒戴過的給她。
她說:“忍不了。”
她戴上口罩,拿起啤酒瓶,走過去,直接砸在了女孩頭上。
------題外話------
***
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