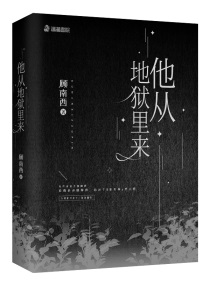憨憨她開竅了,震驚:“檀兮的男朋友就是個撿漏的!是個冒牌貨!”
徐仲清是終極老婆奴:“老婆你說得對,老婆你好聰明!”
冬天晝短夜長,不到七點,外面的天還昏昏暗暗,夜裡打了霜,窗戶玻璃上結了一層薄薄的冰霜花,室內外有溫差,窗戶內側凝了水霧,一層玻璃隔著,是真真正正的霧裡看花。
門哢噠響了一聲,坐在沙發上戎黎立馬站了起來:“杳杳。”
他一宿沒睡,眼下有淡淡的清痕。
徐檀兮剛在臥室的洗手間裡洗漱了,頭發還沾了些水,她從房裡走出來:“你在這兒等多久了?”
他嗓音有點干澀:“我沒睡。”
昨晚和蕭既通過電話之後,他就過來等了,像等待即將判刑的犯人,恨不得快點解脫,又怕不得翻身。
他不說話,仔細觀察她的臉色,仔細猜測她的喜怒,不敢妄動,不敢妄言。
他在等她判罪。
她只說:“你先回去睡覺。”
他搖頭,想拉她的手,忽然不太敢了:“你和我說說話,我要知道你的態度。”
他的態度就很明白,他是來認罪的,不打算狡辯。
徐檀兮看他臉色蒼白,很不忍心:“你去睡會兒,等你睡醒了我們再談。”
“我睡不著,吃安眠藥也沒用。”他整宿沒睡,頭發也亂糟糟的,看上去有點頹,“你是不是生我氣了?”
徐檀兮已經知道答案了,但還是想聽他親口說。
“蕭既說的是真的嗎?”
戎黎一句都沒有狡辯:“是。”他坦白,把他的卑劣都告訴她,“我沒有救過你,醫院大火的時候我在場,不過我是共情障礙者,根本沒把別人的死活當一回事,更不會救人,是我威脅蕭既不准說出實情,也是我讓醫院目睹過的人都閉嘴,我頂替了他,假裝是你的救命恩人。”
他就是這麼卑鄙的人,沒有同情心,沒有慈悲心,為了自己目的,什麼惡劣的事情他都做得出來。
他甚至,想過滅口。
說完,他又去看她的臉色,觀察她眼裡有沒有厭惡、有沒有反感。
徐檀兮很平靜:“一開始就騙了我嗎?”
“不是,腦子裡有淤血是真的,不記得大火的事情也是真的。”
他車禍後遺症,顱內有積血,就不記得大火的事情。
後來他想起來的時候,覺得老天都在幫他,如果沒有這麼多陰差陽錯,他跟徐檀兮根本走不到一起。
徐檀兮坐下,拉著他也坐下:“你什麼時候想起來的?”
“頭受傷那次。”
想起來之後,他根本沒想過坦白,而是去套她的話,去封口。
看吧,他就是這麼惡劣的人。
“為什麼不跟我坦白?”
戎黎毫無底氣:“怕你不要我啊。”
他知道真相的時候,已經非她不可了,他冒不起一點險,只能將錯就錯,反正也不會有比徐檀兮不要他還壞的結果。
徐檀兮眉頭皺了。
戎黎的神經立馬繃緊了。
“我說了很多次啊,不是因為救命之恩才和你在一起,你為什麼不信我呢?”
她生氣了。
她是很溫柔的人,脾氣好,耐心也好,很少會生氣,她也很慣他,平時不論他做了什麼,她都不會指責他。
可是現在她生氣了。
戎黎立馬認錯:“我錯了,我不好,我以後再也不騙你了,你可以生我的氣,打我罵我也行,不要分手。”
其實他心裡沒覺得自己錯了,如果能再重來一次,他還是會選擇冒名頂替,但他會處理得更利索、更干淨,絕對不會讓蕭既有開口的機會。他之所以會認錯,是因為徐檀兮覺得他錯了,他無所謂,對錯對他不重要,只要她覺得他錯了,那他就認錯好了,他不想忤逆她。
他語氣像在求她:“杳杳,不要跟我分手。”
怎麼罰都行,分手除非他死。
徐檀兮比他冷靜,雖然在生氣,但沒有發脾氣:“不全是你的問題,是我先弄錯了,我先在醫院認錯了人。”
戎黎下意識把後背挺直:“那你後悔了嗎?”
他沒有等她回答,一整夜沒合過眼,眼眶發紅:“是你先追我的,你先表白的,你不能招惹了我又不要了。”
他先發制人,想以退為進,語氣是在控訴,但聲調越來越小。
他本就生了一雙乖巧好看的杏眼,眼角一圈暈開了一層紅,就算他什麼都不說,那樣看著人,也最會招人心疼。
徐檀兮無奈:“我何時說不要了?”
戎黎坐過去一些,稍稍挨著她:“那你還喜歡我嗎?我做錯了事,你還喜歡我嗎?”
徐檀兮點了點頭:“但我有一些生氣,我不喜歡你騙我。”
戎黎緊繃的神經終於松了一點:“可以生氣,氣多久都可以,只要別分手。”
“我沒想過分手。”
戎黎繃緊的神經又松了一點點,他把她的手拉過去,包在掌心裡握著。
“如果我當初沒有弄錯,我們是不是就不會遇到了?”
徐檀兮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她是生氣的,戎黎確實做得過分了,可又覺得慶幸,如果沒有弄錯,那就沒有後來的事情了,結局可能止於一張支票。
以身相許這種事情,沒有普遍性,有針對性,針對的是心儀之人。
“不會有如果。”戎黎低下頭去,親她的手,“我們是注定了的。”
坦白局過了。
徐檀兮問正事:“昨天你有沒有找過蕭既?”
戎黎剛變晴的臉色驟然陰了:“為什麼突然說他?”
因為她太了解戎黎了。
“你不要為難他。”
蕭既戳破了他的謊言,依照他的性子,不會這麼算了。
“你偏袒他?”
尾音往上提,是質問。他惹人心疼那雙杏眼突然變得鋒利凶狠,像是領地被人闖入了的獅子,他把獠牙露出來。
剛被緩和下來的氣氛,就這樣,瞬間到了冰點。
蕭既在他這裡,就是顆定時炸彈。他腦子裡都是假想敵,整個人繃著,處在危機意識當中,攻擊性很強。
“我沒有偏袒他。”徐檀兮很理智,她解釋,“他於我有恩,我們不能以怨報德。”
戎黎立馬抓住了她話裡的‘漏洞’:“所以你是說我以怨報德?”
她說的是不能以怨報德。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患得患失的他就像炮仗捻子,一點就燃:“所以你覺得我無理取鬧?”
他握著她的手,很用力。
“我沒有。”
“你有。”
他現在很情緒化,徐檀兮不想跟他爭吵:“等你冷靜下來我們再談好不好?”
不好。
蕭既這顆定時炸彈已經引爆了。
“蕭既是你的恩人,他救過你,所以你要感激他?你要報答他?你要像喜歡我一樣喜歡他?”
一談到蕭既,戎黎就思想極端、方寸大亂。
說到底,是他沒把握,他不是徐檀兮的救命恩人了,別人才是,他怎麼可能沒有危機感,所以她一原諒他,他就得寸進尺,她一提到蕭既,他就斤斤計較。
“你現在不理智,我們不要再談這個問題。”
這是他們第一次爭吵。
徐檀兮不喜歡吵架,非常不喜歡。
“不理他不行嗎?不能當作沒有這回事嗎?我可以給錢,他要多少我都給。”戎黎很固執,對任何可能影響到他跟徐檀兮的異性他都容忍不了,語氣越說越強硬,“你不能離他遠一點嗎?不能當作沒有那場大火嗎?救命之恩怎麼了?非得回報嗎?”
他從來沒有這樣過,對她這麼咄咄逼人。
徐檀兮眼睛都紅了:“我們不要吵了好不好?戎黎,你先冷靜一下。”
她起身要走。
戎黎立馬抓住她,沉默了很久,他服軟:“我錯了。”
他不覺得自己有錯,他甚至想讓蕭既這個人從世界上消失掉。
但她難過了。
“我不好,不該跟你吵架,我不找他麻煩了,你別喜歡他行不行?”
不是他反復無常,是他時刻都在看徐檀兮的臉色,她縱容的時候,他就有恃無恐,她稍微不悅,他就不敢放肆。
他看見她眼睛紅了,然後開始害怕了。
“對不起,對不起杳杳,是我不好,不該對你那麼凶,不該那樣跟你說話。”他坐著,手摟著她的腰,仰著頭,目光開始小心翼翼,“杳杳,我是不是很不正常?像個有病的人,一會兒求你原諒,一會兒無理取鬧。”
獅子把獠牙和爪子都收回去了,露出了最軟的肚子,杏眼把凶狠和強硬都壓下去了,變得水汽蒙蒙。
他真的很會,捏著別人的心玩。
徐檀兮本來生氣的,看見他這樣,氣不起來了,因為心疼:“誰說你不正常了。”
她彎著腰,親了親他的眼睛。
他贏了。
她的弱點是心軟。
“阿黎。”
她每次疼惜他的時候,都喜歡喊他阿黎。
戎黎渾身的刺都被她扶平了:“嗯。”
“我其實很慶幸,慶幸弄錯了,要是不弄錯,我就遇不到你了。”她紅著眼眶,“我很喜歡你,也會一直喜歡你,不會喜歡別人,就算蕭既對我有恩,我也不會喜歡他,他有難我會幫他,這是我處事的原則,但跟私人感情沒有關系,你要相信我。”
“記得我給你寫的情詩嗎?”她輕聲念出來,“既見君子,雲胡不喜。”
因為危機意識而狂躁的獅子安靜乖順下來了。
戎黎把語氣放軟:“那你現在消氣了嗎?”
徐檀兮摸了摸他的眼皮:“你去睡覺,我就消一點。”
已經分不清是誰哄誰了。
“那你陪我一會兒。”戎黎怕她不答應,“不然我要吃安眠藥才睡得著。”
他已經很少吃安眠藥了,只有情緒不穩定的時候才會睡不著覺。
“好。”
醫院大火的事暫時翻篇了,壓在戎黎心頭的大石頭也放下了,這是他跟徐檀兮第一次爭吵,以徐檀兮心軟告終。
戎黎睡熟後,徐檀兮去醫院探望溫時遇。在路上的時候,裴秉德打了電話過來,再三賠禮道歉,並且承諾不會走漏任何風聲,且會好好管教家中的孽子,絕不讓他再為非作歹。場面話說完後,他才說正事。
“已經找到了往溫先生酒裡下藥的人,是我家的佣人。”裴秉德再一次道歉。
徐檀兮問:“誰指使的?”
裴秉德遲疑了一陣:“是溫女士。”
到了醫院,徐檀兮直接去看望溫時遇,他住vip病房,她在外面敲了敲門。
“請進。”
她推門進去:“舅舅。”病房裡沒有外人,她在床頭的椅子上坐下,“你好些了嗎?”
“已經無礙了。”
溫時遇昨晚上喝的酒裡有致幻、催情的藥物,所幸攝入量不多,洗完胃就沒有大礙了,不過手臂和掌心有外傷,是他自己用瓷片割的,為了保持清醒。
“裴家剛剛給我打了電話,找出往你酒裡下藥的人了。”
“是溫女士嗎?”
他喝完有問題的酒之後,只見過溫照芳母女。
徐檀兮頷首:“她收買了裴家的下人。”溫照芳的目的不難猜測,“她應該是想把檀靈許到溫家。”
溫時遇解釋:“昨晚我推開她了,什麼也沒發生。”
------題外話------
****
乖,去睡覺,剩下的我白天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