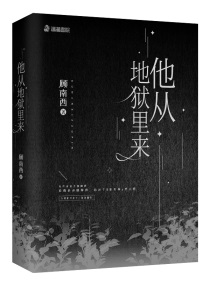黨黨醒了,烏溜溜的眼珠在轉。
戎黎伸手遮住了黨黨的眼睛,另一只手鑽進被子裡。。。
他動作很輕。
“疼嗎?”
徐檀兮不好意思,不看他,側著頭,窗外金色的陽光在她眼裡融化。
“還好。”她耳根泛紅了。
戎黎把力道放重了一點,慢慢揉開:“不要忍,疼就告訴我。”
她安靜了幾秒,轉過頭來,瞳孔濕漉漉的,像落了晨露的黑曜石。
她說:“很疼。”
他手上已經盡量輕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遮了眼睛不舒服,黨黨哼哼唧唧了幾句,開始哭鼻子。
戎黎本來就心疼徐檀兮,小孩還哭,他瞥了一眼,語氣凶了:“你別哭了。”
黨黨哪裡聽得懂,繼續哭。
徐檀兮擰著眉,說戎黎:“你不要凶他。”
戎黎心裡還壓著火:“他讓你受了好多罪。”
生孩子受不受罪因人而異,徐檀兮是屬於很受罪的那一類,剖宮產之後發燒、止痛藥不見效、傷口比別人好得慢、嘔吐、頭暈,她吃了很多苦頭。
戎黎目前對這個孩子還喜愛不起來。
徐檀兮卻不一樣,恨不得時時看著、抱著:“那也不准凶他。”
戎黎俯身,含住,吮了吮。
徐檀兮嘴角溢出了聲音,很痛。
他力道放輕些:“給他吃奶粉好了,不吃就餓著。”
一周後,黨黨乖乖吃奶粉了。
不吃能怎麼辦?催乳師都請了,沒用。
住院十二天,徐檀兮受了很多罪,她之前車禍動過大手術,身體底子並不好,恢復得很慢,體重比懷孕之前還要輕,家裡長輩著急,輪番給她燉湯補身體,但她胃口不好,吃多了會吐。
戎黎除了回家洗漱之外,所有時間都待在醫院,一樣吃不好睡不好,十幾天下來,他也跟著瘦了。
出院半個多月之後,徐檀兮的氣色才慢慢好轉。
她睡眠質量不好,晚上睡得淺,黨黨一出聲她就醒了,剛要起來,戎黎把臉埋在她肩上蹭了蹭。
睡醒之後他聲音沙沙的,還有點鼻腔:“你接著睡,我起來。”
戎黎以前有起床氣的,而且很嚴重,現在沒有了,他剛起來還有點迷糊,頭發亂糟糟的,揉了把眼睛,去櫃子上拿了張尿不濕,把兒童床裡的黨黨抱出來,換完尿不濕又去泡奶粉。
黨黨基本是戎黎在帶,從一開始的手忙腳亂,到現在有模有樣。
還記得黨黨出生的第四天,戎黎笨手笨腳地抱他。
孟滿慈在旁邊教:“手往上一點,拖住他的背部。”
他愣愣的:“哦。”
手跟生了鏽似的,僵硬又遲鈍。
黨黨那時候就一丁點兒大,戎黎抱在手裡都不敢動,更不敢給他穿衣服,怕自己沒輕沒重。
孩子沒出生之前,他去上過准爸爸的培訓課,當時一個班十幾個准爸爸,他的仿真娃娃哭得最慘,甚至哭到沒電,手和頭都不知道斷了多少次,他以為他以後抱孩子也會那樣一團糟,但真正碰到有溫度的黨黨之後,他其實是不敢動的,腦子裡那些培訓的內容也全都忘了,像塊木頭。
徐檀兮還在休養,是他在帶黨黨,慢慢地才熟練了。
他一只手抱著小孩,一只手拿著奶瓶,一大一小你看我我看你:“看什麼,快點吃。”
語氣不溫柔,眼神卻是柔軟的。
這個孩子身上有徐檀兮的骨血,是他的孩子,他能看清他,即便在昏暗裡,就像能看見徐檀兮一樣。
這個認知,很讓他心軟。
黨黨發出很小的吮吸聲音,像奶貓嘬著嘴,眼皮懶懶的,一耷一耷。奶沒全部喝完,小東西就又睡著了。
戎黎輕輕地把他放回兒童床上,蓋好被子才回去睡覺。
他剛躺下,徐檀兮往他懷裡鑽:“你現在好熟練啊。”
“嗯。”他拍拍她的後背,“睡吧。”
她不想睡,剛剛燈光裡的戎黎的影子還散不掉,在她心裡作亂,撓得心髒很癢。
她仰著頭,唇碰到他的喉結,輕輕吮了吮。
戎黎素了太久,她一碰他就能燒著:“別親了。”
她不聽。
他捉住她的手:“你不困了?”
她笑著咬他的下巴:“嗯,不困了。”
她趴到他身上,有一下沒一下地親他。
戎黎被她撩得不行,手覆在她腹上:“這裡還疼嗎?”
“已經不疼了。”
戎黎怕壓到她的刀口,把她抱起來,平放在床上,自己離她遠點,只牽著她的手往下帶,聲音有點難耐:“幫我好不好?”
“好。”
他一只手始終放在她平坦的腹上。
她穿得整整齊齊,而他衣衫不整,偶爾會發出聲音。
她把手指壓到他唇上:“噓。”聲音像把羽毛做的鉤子,“不可以發出聲音。”
他下意識去看兒童床,懊惱地咬了咬唇,他這副樣子……
身邊的女人是個妖精,住在他心窩裡的妖精。
很久後,徐檀兮問他:“你現在喜歡黨黨嗎?”
黨黨剛出生的時候,戎黎有點遷怒他,因為徐檀兮受了很多痛。
“嗯。”戎黎說,“他眼睛像你。”
他愛她,也愛她為他生的孩子。
------題外話------
****
顧美花:感覺好暖,想要戎黎這樣的老公,不知道國——
國家:滾!
顧美花:好吧,還是求月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