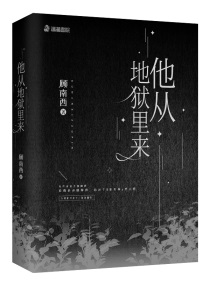高柔理掛了電話:“不好意思,耽誤你們時間了,我今天不做手術。”
七年太久了,久到很多東西都成了習慣,久到何冀北一叫高秘書,她的雙腿就不自覺地走向他。
她到紅山別墅的時候,何冀北正躺在沙發上,背對著門的方向,
“喂。”
她喊了句,他沒有答應。
“喂!”
何冀北睜開眼。
現在連何總都不叫了。
他翻了個身。
高柔理看見他額頭都是汗,唇色慘白慘白的,問他:“你哪裡不舒服?”
他弓腰躺著,手按在腹上:“腹痛。”
“還有呢?”
他悶著聲:“嘔吐,拉肚子。”
“上吐下瀉?”
聲音好低,眼睛也不看人:“……嗯。。”上吐下瀉,還不是流血受傷。
這些年,高柔理把他當祖宗伺候,不僅沒讓他生過病,還把他的身體和胃都養嬌貴了。
這不,他才離了她一天,就把自己搞成這副德行。
“你吃什麼了?”
他生病的時候倒挺乖,汗濕的頭發老老實實地耷著,兩頰發紅,聲音虛弱:“外賣。”
他不做飯,不是在外面吃就是叫餐,之前都是高柔理幫他叫。
他家破人亡之前也是富貴公子,嘴刁身貴,平時在吃的上面,作為秘書的高柔理沒少花心思。
“你點的哪一家?”
“不知道,胡亂點的。”仔細聽,語氣裡有怨氣。
何冀北是個很矛盾的人,刀口舔血的日子也沒少過,早些年在錫北國際闖的時候,受傷流血是常有的事,一身骨頭硬,拳頭更硬,偏偏在吃穿用度上挑剔得很,不僅不糙,還嬌得不得了。
“站得起來嗎?”
何冀北“虛弱”地撐著身子坐起來,嘗試性地站了一下,又坐回去:“沒力。”
一個人打十幾個人的時候,也沒見你沒力。
高柔理覺得自己就是太奴性了,都要辭職了,還管他干嘛。
她把他的手臂搭到自己肩上,扶他起來:“你又攪了我的假期,我都算不清這是第多少次了。”
她覺得養兒子都比養何冀北省心省力。
“這樣吧,你多放我幾天假,等我把以前攢的假全部用光了,再回公司交接。”
流產手術之後她總得要休養吧。
高柔理轉頭,端莊一笑:“可以嗎,何總?”
何冀北只把一點點重量壓在她身上,他唇色很白,生病的樣子和普通人一樣,脆弱又可憐。
“你一定要離職?”
高柔理沒猶豫:“嗯。”
他沒再說話。
到了醫院,醫生檢查之後說是急性腸胃炎,要住院。何冀北被送去病房輸液,高柔理去辦了住院手續,然後打電話去總經辦,把他三天以內的行程全部取消了,其中重要的行程她都全部親自致電,並通知下去,各部門的重要文件要以郵件的形式發送到何冀北的郵箱,並抄送總經辦的sonia,簽字文件則必須送到醫院來。
作為秘書,她確實很專業。
全部安排妥當之後,她回了病房:“住院手續我已經辦好了,公司那邊也給你請了假,沒有其他事的話,我就先回去了。”
何冀北沒說話。
她走人。
她剛到門口,他又叫住她:“高秘書。”
她恢復全能秘書的態度,微笑著問:“還有事嗎何總?”
他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我給你放假,以後假期也不找你,不離職行不行?”
他打了自己的臉,第三次挽留她,不姓何就不姓何吧。
高柔理站在門口,不是平時那副標准的秘書站姿,站得很隨意,穿得也隨意,問得也很隨意:“為什麼這麼不想我離職?”
何冀北沒考慮,答案脫口而出:“除了你,沒人受得了我。”
這個回答意料之中。
高柔理笑了笑:“何總,你終於意識到你有多難搞了。”
她搖頭。
如果沒有孩子,她估計會一直給他做牛做馬。
她愛錢沒錯,但她也愛自己。
她的父母很重男輕女,她像個透明一樣長大,所以她要更加愛自己。
得到答案的那一刻,何冀北臉色就沉下去了:“你走吧。”
他轉身,背對門口。
高柔理是第一個讓他服軟的人,一次就夠了,他不喜歡舔著臉。
“那我就從明天開始休假了。”又恢復到高秘書的語氣,恭敬溫順,“何總,您好好休息,祝您早日康復。”
說完她出去了,還關上了門。
護士還在病房裡,從頭到尾當空氣。
“護士。”
護士問病人有什麼事。
何冀北筆直躺著,手左右對稱放:“幫我把床往左邊挪三釐米。”他又開始龜毛了,“牆上的插座沒有在正中間。”
“……”
護士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
隔音不行,高柔理在外面聽見了,沒辦法,又折了回去。
“何總。”
何冀北身子沒轉,頭轉了,看向門口的方向:“你還回來干嘛?”
高柔理回來給他挪床:“護士小姐,請問這強迫癌還有得治嗎?”
護士面無表情:“准備後事吧。”
何冀北:“……”
高柔理笑得很暢快,語氣也得意:“聽見了沒,何總?”
何冀北看著她,猶如看陌生人:“你以前不這樣。”
過去七年,用一個不太好聽的詞,她言聽計從。
優雅、專業、知性,這是所有人眼中的高秘書。
高柔理今天的褲子跟昨晚一樣,依舊很短、很辣:“我都要離職了,誰慣你啊,以後在外邊差不多就行了,少管別人的頭發跟腰帶。”
她今天的頭發卷得很好看,隨意慵懶,不對稱。
她今天的上衣也很好看,單邊露肩,也不對稱。
何冀北分不清哪個才是真的她,高秘書有時候很聽話,有時候很不聽話,還有時候非常凶,會咬人撓人。最後這個有時候,是在床上。
高秘書是個很奇怪的女人。


![營業悖論[娛樂圈]](/uploads/novel/20240317/9985d76983fd97f0a81dceee3a72fc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