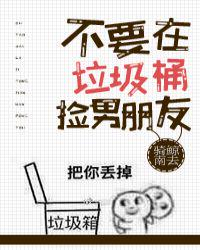原本,他只打算把可疑的鬼衣都留下,再自行摸索查證一番,卻不想靈文隨口一句,給他逮住個驚天大破綻,謝憐一回過味來便將計就計,順著一路詐了下去。最後,竟然炸的靈文片甲不留。
靈文僵立不動。謝憐道:“當然,你可以不承認,但要知道是真是假,也很簡單。只要我現在把那件衣服拿到神武殿去,當著帝君的面讓它變幻一個形態,再問你看不看得出來它變成什麼樣子了,就會水落石出。”
那錦衣仙之前流落人間時吸了五百多人的血,乃是一件陰氣深重的邪物。如果靈文只是擅闖神武殿盜竊錦衣,還沒來得及拿它出去害人,倒也不算罪大惡極不可原諒。可是,靈文是先被點將,後飛升的。錦衣仙傳說流傳起來的最早時間,遠遠晚於靈文被點將的年月。
即是說,靈文是在進入天界供職之後,以神官之身做出的錦衣仙!
本該保衛凡人平安的神官,卻反而誘殺凡人,已該嚴查拿辦,遑論誘殺的這個凡人還是未來的神官,恐怕,這事沒法輕易善了。靈文嘆了口氣,道:“太子殿下,你真是……”
頓了頓,她道:“大概,是我運氣不好吧,這事偏偏攤上了你。雖然今日這靈文殿裡只有我們兩個人,你我也有幾百年的交情了,不過,我想,如果我請求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你多半也不會答應的,接下來應該是勸我去神武殿自行請罪是嗎?”
謝憐也嘆。他和靈文雖然已結識數百年,一直是公事往來,雖不曾深交,但二人關系還算不錯,即便是在剛剛第三次飛升、人人嘲他是個破爛仙人的時候,靈文對他也不曾有分毫怠慢,相反,頗多照顧。偏生這錦衣仙的任務攤派到了他手上,最後查了個水落石出,上報不是,不上報更不可能。
謝憐由衷地道:“我也是運氣不好。”
靈文抱起了手臂,搖頭道:“殿下,你這個人吧……有時候很聰明,有時候又很不聰明;有時候很心軟,有時候又鐵石心腸。”
頓了頓,她道:“那件衣服,現在到底在哪裡?”
謝憐道:“在我手上。之後我會親自送到神武殿去。”
靈文點了點頭,似乎沒話說了。謝憐又道:“所以,你能告訴我,為什麼那錦衣仙穿在郎螢身上會不起作用嗎?”
靈文道:“我大概能猜到。不過,如果殿下想知道答案,可否先答應我一個請求?”
謝憐道:“你說。”
靈文道:“能讓我看看嗎?錦衣仙。”
謝憐一怔。靈文道:“給我一天時間就行了。畢竟,我要是去神武殿自行請罪了,恐怕就沒機會看了。別誤會,我不是要動什麼手腳,只是,你昨日說他顯形了,我真的很吃驚。”
她搖了搖頭,目光微微渙散,道:“……這麼多年了,我還從沒看到白錦顯形過。”
謝憐道:“那位年輕將士,原來名字是叫做白錦麼?”
靈文仿佛才回過神,道:“哦。是的,不過,一般別人都叫他小白。”
謝憐道:“小白?聽起來……”有點像在叫一條狗,又有點像叫一個白痴。靈文笑道:“就是你現在想的那個意思了。白錦這個名字是我給他取的,別人從來不這麼叫,所以也沒幾個人知道這個名字。不過,你要是這麼叫他,他會很高興的。”
在錦衣仙的傳說中,那青年愛慕的女子對待那青年的方式,只令人覺得殘忍可怖,要不是有刻骨恨意,要不就是天生冷血。然而,靈文提起那青年時,口氣卻十分隨和,既無柔情,也無恨意,只道:“行嗎?如果殿下你怕我逃跑,不如用若邪鎖住我。我並非武神,逃不掉的。”
不知為何,謝憐覺得,他應該相信靈文,沉吟片刻,緩緩點了頭,道:“好。”
二人佯作無事的樣子,出了靈文殿。走在仙京大街上的時候,還是照常和其他路過的神官打招呼。靈文神色如常,壓根看不出來她袖中雙手已經被若邪鎖住了。沒走多遠,迎面撞上巡街歸來的裴茗,二人打了招呼,站在路邊寒暄,瞎扯了幾句,裴茗直盯著謝憐,謝憐微微警惕,道:“裴將軍為何這麼看著我?”
裴茗摸了摸下巴,誠懇地道:“不瞞太子殿下,我現在是看到你就心驚肉跳,總覺得誰站在你旁邊好像就會出點什麼事。所以我看到你跟靈文一起走,心跳又加快了。靈文,你最近千萬當心。”
靈文哈哈道:“怎麼會呢?裴將軍不要說笑了。”謝憐卻哭笑不得。某種意義上來說,裴茗的感覺還真准。
回到菩薺觀,遠遠便看到郎螢靠在觀前一棵老樹下,左手漫不經心地轉著掃帚玩兒,一堆掃好的金黃落葉堆在他腳邊。謝憐眯著眼看了一會兒,這才故意放重了腳步聲走過去,郎螢沒回頭,卻一定覺察到了他們的存在,極其自然地改變了姿勢,繼續掃地,轉身一看,似乎才看到謝憐和靈文緩步行來。謝憐輕咳一聲,道:“又在掃地啦。”
郎螢安然受之。靈文看看他們,不予置評,謝憐領著她打開了菩薺觀的門,道:“就在這裡……”
誰知,一打開門他們就看到一個身影蹲在功德箱前,又在鬼鬼祟祟地塞金條,謝憐忙不迭上去把他拖開,道:“奇英,不要再塞了,真的夠了,上次你塞的那些我還沒弄出來呢,已經卡住了。”
靈文點頭道:“奇英殿下好。”
權一真也對她道:“你好。”
菩薺觀的正中央立著一個木架子,架子上掛著一件樸素的麻衣,當然,這只是謝憐眼中所見到的。靈文走上前去,凝望了它一陣,那衣裳毫無反應,她側首道:“二位殿下,我想在此單獨看看,可以嗎?”
謝憐道:“可以。”
若邪捆住了靈文的雙手,她又不是武神,基本上不會出什麼亂子,謝憐還算放心,把手放在權一真肩上,道:“出去吧。”
多少算是解決了一件事,謝憐心情稍稍放松下來了。剛好左鄰右舍送了一圈瓜果蔬菜過來,他便拿去廚房,准備做飯。可謂是百折不撓。幾天下來,權一真似乎已經把他菩薺觀當成了農家樂一樣的地方,上躥下跳,時而爬樹,時而偷瓜,時而摸魚,時而捉蛙。一不留神,謝憐就被他摸進廚房,偷走了一只地瓜。他摸了個空,回頭就看到權一真叼著地瓜溜出去,急急如漏網之魚,忙道:“還沒做好,不要吃!”
然而,就是因為沒做好所以才要趕緊吃,等他做好了就沒法吃了。謝憐搖了搖頭,又看到郎螢走了過來,眯了眯眼,道:“郎螢,有空嗎?來幫忙吧,切個菜。”
郎螢本來要去搶權一真偷走的地瓜,聽謝憐發話,二話不說就過來幫忙了,抄起砧板上的菜刀,摁著白菜,一刀一刀切得認真。謝憐看了看他,轉過頭去,一邊淘米,一邊隨口道:“郎螢啊,到咱們菩薺觀裡來過的神神鬼鬼,你也見識過不少了吧?”
一個個的都稀奇古怪的。郎螢在他身後道:“嗯。”
謝憐道:“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啊:如果讓你來選,你覺得,這些神神鬼鬼裡面,哪一位是最英俊的?”
郎螢悶頭切菜,似乎在思索。謝憐輕輕挑眉,道:“說呀。照你心裡的實話說就是了。”
於是,郎螢答道:“你。”
謝憐笑道:“除我以外的。”
郎螢道:“紅衣服的。”
謝憐忍笑忍的要內傷了。
他嚴肅地道:“嗯,我也是這麼覺得的。”
頓了頓,謝憐又問道:“那你覺得,哪一位最厲害?”
郎螢還是答:“紅衣服的。”
謝憐再飛速接著問:“哪一位最有錢?”
“紅衣服的。”
“哪一位你最欣賞?”
“紅衣服的。”
“哪一個最傻氣?”
“綠衣服的。”
這些問題接的如此緊密,他居然改口得十分及時,可見思維之敏捷,反應之機靈。謝憐道:“嗯,看樣子你還蠻喜歡穿紅衣的那位哥哥的,他的名字,叫做花城,記好了。這麼說,你覺得他很好咯?”
不知不覺間,郎螢的刀似乎快了好幾倍,道:“非常好。”
謝憐道:“那麼,有空的話,你覺得是不是該再請他來我們這裡做客呢?”
郎螢道:“嗯。當然。必須的。”
謝憐道:“我也是這麼想的。可是,他的下屬說,他最近很忙,一定都在忙著做非常正經的事,我想還是不要去打擾了。”
這一句後,郎螢“哢哢”的切菜聲突然重了好幾分,謝憐則扶住灶台,忍笑忍得腹筋抽搐。權一真的頭忽然從窗外探了進來,咬了一口地瓜,看了兩眼,對郎螢道:“你切的這麼碎,不好吃了。”
郎螢道:“嗯?你說什麼?”
謝憐回頭一看,豈止是碎,簡直是碎成渣渣了,輕咳一聲,道:“哎呀,真的,你的刀功太差了。”
“……”
把一大堆亂七八糟的配料都倒進了鍋裡,謝憐拍了拍手,決定就這樣讓它們煮一個時辰,出了廚房,看了看靈文,還老老實實待在觀內,他便繼續干活,從柴堆裡翻出一塊稍大的木牌,到村長家借了筆墨,坐在門口,一手拿木牌,一手執筆出神。郎螢也走了過來,謝憐抬頭,溫聲道:“郎螢,你識字嗎?可會寫字?”
郎螢道:“會。”
謝憐道:“那你的字如何?”
郎螢道:“一般。”
謝憐道:“沒關系,能看清就行了,再幫我個忙吧。”
他把木牌和筆都遞給了郎螢,微笑道:“咱們觀裡一直沒有匾額,不如,你來寫一個與我?”
“……”
在謝憐的催促下,郎螢拿起了筆。那小小一支筆在他手裡,仿佛重於千斤,無論如何也揮動不得。
好半晌,他似乎認輸了,放下了筆和木板,繃帶後,傳來一個無奈的聲音:“……哥哥,我錯了。”
這聲音根本不是郎螢,分明就是花城,只是比以往更為清脆,是個少年的嗓子。謝憐抱著手臂靠在一邊牆上,看他掙扎了這許久,終於投降,實在忍不住了,笑倒在地:“三郎真的是好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