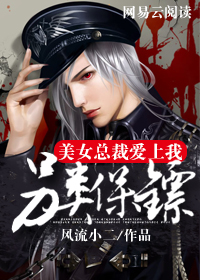可能是他這個人本生長的還是小帥小帥的,因此做了酒店的門侍,負責幫客人開車門,拎行李。
不過白聖的處境,沒有想像中的好。
酒店的老員工,經常變著法子的欺負他。他原本不是個願意忍耐的人,但目前他家裡的情況不太好。
父親重病,雖說不是什麼立馬要命的病,卻是沒有錢就要命的病。
為了生活,他只能夠忍受著同事的欺負,客人的羞辱,將自己的最嚴放得最低,苟且偷生罷了。
做門侍的有好幾個,經常有豪車停在門口,白聖還來不及上去接待,就被同事搶先一步接待。
畢竟開豪車的客人,都特別大方,會給他們不少的小費。
像打車過來,開一般車子的客人,就不會那麼大方了,小費最多就是五塊十塊的。
要是開著跑車,帶著女人的客人,那就更大方了,通常都是一百,要是運氣好的,有可能得到好幾百。
他們最喜歡接待的,還是那種爆發富,在女人的面前,最喜歡充面子。尤其還會,經常讓他們幫忙買點東西,剩余的錢,都會讓他們自己收著。
這樣的客人,白聖也想接待。
可是他是新人,老員工都排擠他。那些經常來的客人,也不熟悉他,根本不讓他接待。
偶爾有個陌生潛力客人,也被同事搶了。
即便被搶了客人,白聖也也沒法子反抗。這兩年來,他已經吃過許多虧。
像他這樣沒背景,無權無勢的小人物,遭受了委屈,除了忍著,就只能夠忍著。要是逞一時之能,得到的結果只可能是被開除。
父親的病一直都需要錢,要是再被開除,白聖就找不到比這裡更好拿小費的地方了。
去做其他行業的服務員,一個月三四千塊,根本不夠給父親看病。
因為父親的病,他賭不起,也沒有時間去賭,只能在這裡苟且著。
在他的心裡,也期待著,自己能夠有一飛衝天的時候。但是現實往往是殘酷的,他已經漸漸的放下那種不切實際的夢想。
唐果是打車來的,還帶著一個行李箱,裡面裝了不會少東西,很重。
畢竟,她是來接觸白聖的,才不想要另外的應侍生接待她。
車子停在酒店門口的時候,她往酒店的門口看了眼,便發現門的位置等待著不少應侍生。
唐果來的時候,她很確定,這些人都往她這裡看了眼。
距離有些遠,酒店門口的玻璃還有些反光,所以客人基本是看不到那些應侍生目前的臉色。
白聖看到又是一個打車過來,就明白這是他的活兒,身邊的同事絕對不會和他搶。
通常這種打車過來的客人,小費少不說,行李還可能很笨重。
但白聖一點都不嫌棄,他巴不得多來點這樣的客人,就算三塊五塊哪怕一塊也行,所謂積少成多,就是如此。
一天來個這樣的客人幾十上百個,他也有一筆不菲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