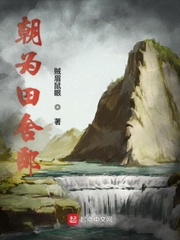第28章 微月夕煙往事遙
景炎二十六年,六月中旬,風惜雲班師青州王都,百姓夾道迎接。
回到王都後,君臣們自有一番休整。
六月裡,天氣炎熱,正是酷暑難耐之時,王宮各殿室裡雖放了冰盆,但效果也不大,更遑論室外驕陽暴曬,幾乎能將人的皮膚烤下一層。
青蘿宮裡卻飄出一陣笛聲,絲絲縷縷清揚若風,令人聞之心神一靜,減了幾分燥熱。
服侍青王的女史六韻步上台階時,正聽到這清暢的笛聲,暗想這位蘭息公子吹的笛聲倒是可與寫月公子的簫音一比,只可惜……想至此,她嘆口氣,然後斂心收神,走入宮內。
青蘿宮的內殿裡,豐蘭息佇立窗前,橫笛於前,雙眸微閉,行雲流水般的笛音正輕輕溢出。
直到他一曲吹完,六韻才上前行禮,“奴婢六韻見過蘭息公子。”
豐蘭息睜開眼眸,一瞬間,六韻只覺得殿內似有明珠旁落,滿室生華,可也只是一瞬,那光華便斂去,如同明珠暗藏。
豐蘭息微微一笑,“姑娘來此何事?”
“主上請公子前往淺雲宮一去。”六韻恭敬地答道。
“哦。”豐蘭息點頭,淺笑依然,“多謝姑娘,還煩請帶路。”
“不敢。”六韻依然神態恭敬,“公子請隨奴婢來。”
豐蘭息抬步,跟隨著六韻前往淺雲宮。
淺雲宮是風惜雲做公主時居住的宮殿,待她繼位後即搬到了鳳影宮,淺雲宮裡只留了些灑掃之人,是以十分安靜。
豐蘭息踏入前殿,抬眼打量了一番,不愧是風惜雲的住處,殿內的裝飾擺設極其簡單,但又不失大氣,像它的主人。
耳邊傳來腳步聲,輕盈得仿佛走在雲端,這樣的腳步聲他不會認錯,知道是風惜雲來了,不由轉頭望去,一見之下,唇角不由自主地勾起一朵歡喜的微笑。
今日的風惜雲身著一襲水藍色長裙,布質柔順如水,腰間系一根同色的腰帶,顯得纖腰盈盈不及一握,長長的裙擺剛及足踝,裙下一雙同色的飛雲繡鞋,黑發披垂,再以白色綢帶束於尾端,素顏如玉,不施脂粉,唯有額間雪月如故,這樣的風惜雲,飄逸如柳,素雅如蓮,柔美如水。
“找我何事?”豐蘭息的眼神語氣不自覺地便帶出溫柔。
風惜雲微微一怔,然後道:“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兩人走出淺雲宮,再穿過長長回廊,繞過花園,便到了一處宮殿前,宮殿不大,位於淺雲宮的正後方。
“微月夕煙?”豐蘭息看著宮前的匾額,再側首看看風惜雲,“是出自‘瘦影寫微月,疏枝橫夕煙’此句?”【注1】
“嗯。”風惜雲目光迷蒙地看著匾額上的字,仿佛是看著一個久未見面的人,想細細看清它的容顏,想看清時光賦予它怎樣的變化。
匾額上的四字,只是墨跡稍稍褪色,筆風纖細秀雅,字字風姿如柳。
“這宮殿是按寫月哥哥畫的圖建成的,那時候他才十歲。”
聞言,豐蘭息眸光一頓,目光又落回匾額上,“是那個被稱為月秀公子的風寫月?”
“除了他,這世上還有誰配得上月秀二字!”風惜雲步上台階,伸手輕輕推開閉合的宮門,抬步跨入。
豐蘭息跟在她身後,跨過門檻,一眼望去,饒是見多識廣的他也不由驚奇不已。
宮門之後,首先入目的是懸於廊前的月白絲縵,長長柔柔地直垂地面,門外的風湧入,舞起絲縵,仿若拂開美人蒙面的輕紗,露出秀雅的真容。
絲縵之後,並非氣宇闊朗的殿堂,而是一個廣闊的露天庭院,院中花樹煥然,兩旁樓宇珍奇,令人耳目一新。
以庭院為中心,左右兩旁各有宮殿,都以長廊連接成環,那些宮殿小巧精致,幾乎只有平常宮殿的一半大小,其屋頂形狀更是迥異於尋常宮殿。有的線條曲折優美,形如五色花朵;有的圓潤潔白,如同珍珠;還有的狹長,像條小舟;更有的看起來像飄浮著的雲朵……十分新奇漂亮,倒像是那些神話傳說裡的奇宮玉宇。而且每座小宮殿前都有匾額,上面有的書“花潔眠香”,有的書“心珠若許”,有的書“小舟江逝”,有的書“雲渡千野”……皆字跡秀雅,顯是與宮前的匾額同出自一人之手。
而庭院裡的鮮花都是芍藥花,此時花開明媚,灼灼其妍,白的、粉的、紅的、紫的、綠的……叢叢朵朵,點綴於長廊宮室間,清香陣陣,蝶舞翩翩,再加上絲縵飄舞,這裡仿佛是隔絕世外的仙園。
“他說他為長,我為幼,所以他居左,我居右。”
在豐蘭息還在為這庭院驚嘆時,耳邊響起風惜雲的輕語,側首看她,便見她一臉淺淡卻真實、歡快的笑容,這樣的笑,自她回到青州後已罕有出現。
他心中一動,“這裡是?”
“你小時候住在什麼地方?”風惜雲轉頭看他,卻不待他回答又自顧道,“這裡是我與哥哥一塊兒長大的地方,這些小宮殿就是我們小時候居住的地方。”
說話時,她的臉上帶著一種他從未見過的溫柔,目光柔和而溫情,有些歡喜,有些自豪,又有些傷感地看著這裡的一樓一閣,一花一樹。只因為風寫月嗎?因為這裡是屬於她與風寫月兩個人所擁有的?
“你留在這裡。”
正在豐蘭息想得出神的時候,耳邊又聽得風惜雲的柔柔低語,回神時便已見她飛身落在庭院的正中心。庭院的正中心,有約兩丈見方的地面鋪著漢白玉石板,鋪成一個圓形,仿若天墜圓月,但細看便可看見石板上刻有微痕,看起來又像個棋盤。
風惜雲立於庭中,閉上眼睛,靜立片刻,仿佛是在回想著什麼,片刻後,她開始移動,腳尖輕輕地點在地面,身子隨著步伐飛躍旋轉,纖手微揚,衣袖翩然,仿佛在跳舞,又仿佛是以人為棋子在下著一盤棋,但見她越走越疾,越轉越快,水藍的裙裾旋轉飛揚,仿若一朵水蓮花柔柔蕩開,那樣的輕妙悠婉。腳尖輕輕地點著,但每一下都實實在在地點在地上,有咚咚響聲,倒似是和著舞的曲,而風惜雲在飛舞時,臉上笑容越綻越開,顯然十分開懷,仿佛是在重溫兒時的游戲。
約莫過了一刻,風惜雲停步,然後躍開落在一旁。
轟隆一聲!庭正中的地面開始振動,接著石塊緩緩移動,而風惜雲顯然早已知情,只是靜靜等待。
不過片刻,石塊不動了,庭正中露出一個約兩米見方的洞口,洞口下方隱約可見台階,延伸至地下。
“敢跟我來嗎?”風惜雲回首看一眼豐蘭息。
“這裡是通往黃泉還是碧落?”豐蘭息問,腳下一點,人已立於風惜雲身旁。
“黃泉。”風惜雲挑眉,“蘭息公子敢去嗎?”
“有青王在,黃泉碧落又有何區別。”豐蘭息一笑,然後抬步領先走去。
看著那毫不猶疑的背影,風惜雲神情復雜地嘆了口氣,然後也抬步走下。
台階很長,一級級走下,光線越發黯淡,氣溫也變得陰涼,聽著足下空曠的回音,恍惚中真有一種去往黃泉的感覺,兩人不約而同地側首看了對方一眼,目光相遇時,淺淺一笑。
約莫走了半刻,終於走至台階盡頭,腳下是長長的通道,通道兩旁的石壁上,每丈許即嵌一顆拇指大小的夜明珠,珠光閃爍,照亮通道。
“走吧。”風惜雲率先抬步。
兩人又走了約莫一刻鐘,通道到了盡頭,前方是一道封閉的石門,石門的上方刻著“瓦礫窟”三字。
“知道裡面是什麼嗎?”風惜雲看著那三字便笑了。
“世上金銀如瓦礫。”豐蘭息道,目光落在那三字之上,側首看著風惜雲,語氣中有著調侃,“青州風氏似乎一直有著視榮華富貴如糞土的清高。”
“哈哈……”風惜雲輕笑,“你似乎不以為然。”
“豈敢豈敢。”豐蘭息神情誠懇,語氣倒是恰恰相反。
風惜雲也不以為意,飛身躍起,手臂伸出,在“瓦礫窟”三字上各擊一掌,然後盈盈落地。
轟隆隆……沉重的石門緩緩升起。
“請蘭息公子鑒賞青州風氏所藏的瓦礫。”風惜雲微微側身。
“恭敬不如從命。”豐蘭息也不禮讓,抬步跨入石室,霎時,眼前光芒閃耀,刺得他的眼睛幾乎睜不開。
眨了眨眼睛後,才是看清,石室非常之寬廣,其內幾乎可以說是金山銀丘,珠河玉海,還有那不計其數的古物珍玩……即算是出身王室、坐擁傾國財富的豐蘭息,此時也不由睜大了眼睛。
“你說這些比之幽州國庫如何?”風惜雲看著他的表情笑道。
“比之幽州,十倍有余!”豐蘭息長長嘆息著,轉頭看著惜雲,“歷代以來,青州風氏似乎也並無雄霸天下之意,卻何以將如此之多的金銀珠寶貯於此處?”
“雄霸天下?”風惜雲冷誚地笑了笑,目光從豐蘭息身上移向那些珠寶,“在你心中,似乎財富、兵力只與爭奪天下有關。”
豐蘭息移步走至堆集成山的黃金前,抬手抓了一把金葉,然後張開手,看著金葉自掌中撒落,“因為我斂財練兵,只為天下。”
“哦?”風惜雲眉頭一挑,“難得你這回倒是坦白了。”
“對於江山玉座,我從未隱瞞過我的意圖。”豐蘭息淡淡掃一眼風惜雲。
風惜雲嘆口氣,目光落回那些金銀珠寶,“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要將這些藏於此處,我父王不知道,我祖父不知道……這原因大約只有第二代青王——也就是鳳王的兒子知道,‘子孫後代,凡國庫盈余皆移入地宮’的詔諭是他下的。”
“啊?”豐蘭息聽了也是滿臉驚訝與疑惑,“你們真就聽從他的話做了?”
“你看到這些不就知道了。”風惜雲看著也嘆氣,“每代裡除了災急之時動用了一些外,積了幾十代的財富全在這裡,真是白白便宜了你。”輕描淡寫裡,她便已將這地宮裡的金山玉海送了人。
盡管進入地宮後,豐蘭息便已知風惜雲之意,可此刻親耳聽得,心中依是不由得一熱,只是他們慣不會那套感恩戴德的,所以他也只是微微一笑,若春風繾綣,眉梢眼角自有柔情瀠洄。一笑後,他低頭故作沉思狀,然後道:“難道是令祖知道今日我要用到,所以早早預備下了?”
“呸!你想得倒美!”風惜雲聞言反射性地便嗤笑他。
“不是早算到了就好。”豐蘭息頓擺出一副松了口氣的模樣,“從來只有我算到別人要做什麼,若被別人算到我要做什麼可不好。”
“哈……”風惜雲禁不住笑出聲,“你這狐狸,原來最怕的就是被別人算到啊。”
這一聲“狐狸”是脫口而出,兩人一個怔住,另一個卻暗自歡喜。
“那你說會不會跟鳳王的早逝有關?”豐蘭息再猜測道。
風惜雲沉吟,“鳳王是當年七王之中最先薨逝的,以年齡來說可算是英年早逝了,而且是死於朝覲之時,她薨後第二年,王夫清徽君也追隨而去……”她說著瞟了眼豐蘭息,“你為何這樣猜?”
豐蘭息沉默了一下,似乎有些猶疑。
“喂!”風惜雲催他。
豐蘭息看她一眼,才頗為無奈地道:“這話也只與你一人說。我以前在我住的宮裡想要挖個藏身的地室,結果挖到個玉盒,盒裡裝的是先祖昭王的札記……”他看著風惜雲高高挑起的眉頭,苦笑道,“你也別問我為什麼昭王的札記會埋在地下,我也不知道。”
“你肯定偷看了昭王的札記。”風惜雲鄙夷地丟了個眼神。
札記大都是個人的日常記事,有些可以公開,但有些是非常私密的,更何況是昭王的。不過……她捫心自問了下,要是她發現了鳳王的札記,會不會看呢?這念頭一起,她就知道自己肯定也會看的。
“我看之前又不知道是昭王的札記,看了後才知道的,但既然已經看了,挽也挽不回了,不如全部看了。”豐蘭息神色裡沒有一絲羞愧,倒是坦蕩得仿佛他只是看了本只他一人能看的書,“當時年紀小,看後也沒放在心上,時日久了幾乎都忘了這事,直到後來……”他語氣一頓,看著風惜雲,目有深意。
風惜雲一怔,腦中一轉,便明白了,“是當年你我在帝都皇宮的凌霄殿看了那些畫像後,你便又去重看了昭王的札記?”
豐蘭息點頭,“昭王的札記倒也不算多,只有四十七片,只不過每一片都與鳳王有關。”
豐蘭息又沉默了,他雖對於看了先祖的札記無愧,但要來細談先祖札記的內容卻頗感心虛,於是只含糊道:“都是些他們的舊事。”
“什麼舊事?”風惜雲這會兒心裡就如貓抓似的,只恨不得自己也能看一看那札記才好。
豐蘭息瞟她一眼,道:“你我也相識多年,若有人問你,你我之間有些什麼事,你如何作答?”
風惜雲頓時啞口。
豐蘭息見她不追問了,暗自松了口氣,道:“那札記裡有一片,看時間是最後一片,記的是鳳王死後,昭王極為悲痛,寫下‘鳳隕碧霄,吾雖生猶死。昔曾誓約,同福禍共生死,然根孽同鑄,何偏害鳳凰?月殘魂斷,煢煢獨影,人鬼相吊,哀以無絕。’這麼幾句。”
豐蘭息一念完,風惜雲人也呆住了。
“然根孽同鑄,何偏害鳳凰。這一句顯然有蹊蹺。”豐蘭息道。
風惜雲沒有說話。其實這片札記短短幾句話,何止這一句蹊蹺,其中還證實了另一件事。想著,她不由望向豐蘭息,目光觸及他額間的墨玉,頓時心頭劇跳。
她與他各擁有一片除了顏色不同外,形狀玉質都一模一樣的彎月玉飾,這些年裡也曾疑惑過,只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此時對照這札記上的話,再想想這些都是祖傳之物,心中便有了答案。
不知這兩片玉飾合在一起時,是不是就是一輪圓月?這樣想著,她心頭便有些歡喜,卻更多的是酸澀悲傷。
豐蘭息見她久久不語,看她神色,便有些明了她的心思,一時亦是情思紛亂,復雜難理。
半晌後,風惜雲先回神,“算了,先祖們的事都隔了幾百年了,誰知道是怎樣的。今天帶你來,是讓你知道這些東西的所在,日後你要如何用,自己安排。”
豐蘭息點了點頭。
風惜雲的目光越過那一堆堆金銀珠寶,落向東面石牆,牆上掛著一幅畫,她遙遙看著,腳下一動,似想走過去,卻又猶疑著。良久後,她終於還是移步慢慢走過去,等至牆上,她定定望著那幅畫。畫上日月共存,正畫的是月隱日出之時,天地半明半暗,而日與月之下還畫著兩個模糊的影子,似因天光黯淡而看不清那兩人的面貌,整幅畫都透著一種陰晦抑郁。
她看了半晌,然後伸手,指尖撫過畫中的那兩個人影,微微一嘆,然後揭開那幅畫,便又露出一道石門。
豐蘭息不由也走了過來,見那石門左側刻著“瘦影寫微月”,右側刻著“疏枝橫夕煙”。
風惜雲看著石壁上的字發呆,看了半晌,才輕聲道:“他總是說,他是寫月,我便應該是夕煙,所以他總是喚我夕兒,從不喚我惜雲,弄到最後,父王干脆就用夕兒當了我的小名。”她一邊說著,一邊伸出雙手,指尖同時點住“月”與“夕”兩字,然後石門輕輕滑動,一間石室露了出來。
步入石室,頂上嵌著四顆雞蛋大小的夜明珠,照得室內如同白晝,而這間石室裡卻沒有金銀,左右牆壁上掛滿畫像,畫像下依牆立著長案,案上還擺了些東西。左邊全是男子畫像,右邊全為女子畫像,仔細看去,便會發現這些畫像幾乎就是畫中女子與男子的成長史。
“這裡一共有二十四幅畫像,我的十二幅,寫月哥哥的十二幅,我的從四歲開始,寫月哥哥的從六歲開始。”風惜雲的聲音柔軟異常,帶著淡淡的傷感,“每一年生辰時,我們都會送對方一件親手做的禮物,並為對方畫一幅畫像,曾經約定要畫到一百歲的,可是……”
豐蘭息移步,目光左右掃視,打量著畫像裡的人。
右邊第一幅畫裡,四歲的小女孩圓圓胖胖的,手中抓著一只小木船,皺著眉頭,瞪著眼睛,似是在說“快點,不然我就把這只木船吃了!”,畫功細膩,眉眼間傳神至極。在那幅畫像下的長案上,就擺著女孩手中那只小木船,只算形像,做工甚為粗糙,似乎出自一個笨拙的木匠之手。
左邊第一幅畫裡,六歲的小男孩,眉清目秀,手中正握著一朵紫綢扎成的花,臉上的神情有些羞澀,那雙秀氣的眼睛似乎在說“怎麼可以送男孩子綢花!”,畫像下的長案上,擺著那朵已經褪了色的紫綢花,歪歪斜斜,顯然扎花者的手藝並不純熟。而畫這幅畫的,筆風粗糙,而且很粗心,墨汁都滴落在畫像上,好在只是落在男孩的臉旁,沒有落在臉上,唯一慶幸的是神韻未失,堪能一看!
右邊第二幅畫,五歲的小女孩子似乎長高了一些,穿著淡綠的裙子,梳著兩個圓髻,看起來整整齊齊,干干淨淨,只是袖口被扯破了一塊,手中抓著的是一柄木劍,臉上的神情十分神氣,仿佛在說,“我長大了以後,肯定天下無敵!”
左邊第二幅畫,七歲的小男孩也長大了些,眉眼更為秀氣了,長長的黑發披垂肩上,實是一個漂亮的孩子,手中抓著一朵紫色芍藥,是以男孩的神情頗有幾分無奈,似乎在說“能不能換一件禮物?”,但顯然未能得到同意,畫像的人更是特意將那紫芍畫得鮮艷無比。
……
一幅幅畫看過去,男孩、女孩在不斷長大,眉眼俊秀,神情各異,氣質也迥然不同。
女孩的眉頭總是揚得高高的,眼中總是溢著笑意,似乎這世間有著許許多多讓她覺得開心和好玩的事兒,神情裡總是帶著一抹隨性與調皮,似只要一個不小心,她便會跑得遠遠的,飛得高高的,讓你無法抓住。
男孩則十分斯文,每一幅畫裡,他都是規規矩矩地或坐或站,只是他似乎一直都很瘦,黑色的長發也極少束冠,總是披垂在身後,眉目清俊秀氣,臉上略顯病態,衣袍穿在他身上,總讓人擔心那袍子是否會淹沒了如此消瘦的他。
隨著年齡的增長,作畫之人的畫技也日漸純熟,形成各自不同的風格。
畫女孩的,筆風細膩秀雅,從一縷頭發到嘴角的一絲笑紋,從一件飾物到衣裙的皺折,無不畫得形神俱備,仿佛從畫像便能看到作畫之人那無比認真的神情,那是在畫他心中最寶貝最珍愛的,所以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瑕疵。
而畫男孩的,則一派大氣隨性,仿佛作畫時只是拈筆就來,隨意而畫,未曾細細觀察細細描繪,只是簡簡單單的幾筆,卻已將男孩的神韻完全勾畫出來,顯然作畫之人十分了解男孩,在她心中自有一個模印。
豐蘭息的目光停在女孩十五歲那張畫像上,這也是女孩最後一張畫像,畫中人的面貌體態與今日的風惜雲已差別不大,而且她身上的裝束與今日一模一樣,亭亭立於白玉欄前,欄後是一片紫芍,面容嬌美,淺笑盈盈,人花襯映,相得益彰,只是……她的眼中藏著的一抹隱憂也被作畫之人清晰地捕捉進了畫裡。
而男孩——十七歲的少年長身玉立,清眉俊目,氣質秀逸,已長成了難得一見的美男子,只是眉目間疲態難消,似是大病未愈,體瘦神衰,身著月白長袍,腰系紅玉玲瓏帶,同樣立於白玉欄前,身後也是一片紫芍,人花相映,卻越發顯得花兒嬌艷豐盈,而他弱不勝衣,病骨難支,只是他臉上卻洋溢著歡喜的笑容,眼中有著淡淡的滿足。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為對方作畫,也是最後一次一起過生辰,第二天,他就去了。”
豐蘭息凝視著畫像時,耳邊響起風惜雲低沉的輕語,他側首回眸,見她不知何時站到了他的身旁,靜靜地看著畫中的少年,臉上有著淡淡哀傷。
“我們青州風氏是大東朝王族裡最為單薄的一支,從先祖起,每一代都只有一名子嗣,即算偶有生得兩或三名的,不是在襁褓中早夭便是英年早逝,總只能留下一人承繼血脈與王位。到了父王這一代,雖生有伯父與父王兩人,但伯父伯母都早早離世,只遺下寫月哥哥一子。父王繼位後,母後也只生我一個,雖納嬪嬙無數,卻再無所出,所以到我這一代,青州風氏只有我與寫月哥哥兩個。”
風惜雲移近兩步,伸出手,指尖輕輕撫著畫中的少年。
“說來也巧,我與寫月哥哥同月同日生,他剛好長我兩歲。他無父無母,而我……父王政務繁忙,而母後則……所以我們倆自小就親近,哥哥十分聰慧,才華卓絕,我所學裡幾乎有大半傳自於他,只可惜他身體羸弱,長年藥不離口,否則……今日的四公子裡應有他的一份,而我亦不用做這女王,依舊可以逍遙江湖。”
風惜雲說著,臉上浮起淡淡的笑,眼神裡也流露出追憶之色,顯然是回想起了與兄長的往事。
“記得有一年六月,我們才過生日不久,又迎來了父王的四十壽辰,不但各諸侯、鄰國都派來使臣賀壽,便連帝都也派了人來,所以父王壽誕那日,宮中大擺宴席,十分的熱鬧。那天,作為儲君,我需陪伴父王左右,接受各方的恭賀,只是公主的朝服太過累贅,而且我也不肯安安分分地傻坐著,所以一早趁著哥哥還沒醒,便使喚了人把公主的朝服給哥哥穿上,然後自己換了哥哥的衣裳扮成了他。哥哥因體虛,夜間難入睡,早上卻難醒,等到他清醒時,衣穿好了,頭發梳好了,我再懇求一番,哥哥向來寵我,也只能無奈答應。”
說到此處,風惜雲輕輕笑了起來,眼中波光流轉,明亮異常,似乎是又看到了那日與她異妝相對的兄長。
“我與哥哥是兄妹,本就長得像,那日父王諸事繁忙,也沒有發現。所以中途我裝作疲累了,父王向來憐惜哥哥,忙打發人送我回去休息。中途我悄悄溜出王宮,因為是父王的壽誕日,所以王都裡的百姓也在慶賀著,八方奇藝,四方珍玩,人如潮湧,到處都是好玩的好看的,比在王宮接見使臣要有意思百倍,我玩得不亦樂乎,哪裡知道哥哥的苦處。他身體羸弱,六月裡天氣又熱,穿著厚重的朝服,悶得難受,又跟在父王身邊接受各方拜賀,言行舉止間不能有分毫出錯,以免失儀,所以頗為緊張,心裡更是一直擔憂被識破時我要挨父王的罰,這時間一長,他的身體哪裡支持得住,結果就暈倒了。”
風惜雲說著忍不住輕輕嘆息,臉上也浮起自責,“那日,我後來果然是被父王重重責罰了,結果也因此讓‘惜雲公主體弱多病’的謠言傳開了。”她轉頭,目光望向十歲時的畫像,“也是自那時起,我便生出了去外面看看的念頭,先是常常溜出王宮在王都裡到處游玩,過得兩年我便想走到更遠的地方去看看,父王雖疼我,卻肯定不會答應,所以我只把打算告訴了哥哥一個,哥哥卻支持我。他說我將來是要繼承王位的人,是要肩負青州安危與百姓生計的人,本就應看盡天下風光、熟知民間疾苦,才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豐蘭息一直靜靜地聽著,神色靜然,目光柔和。
“因為有哥哥的疼惜與成全,所以才有了江湖上恣意快活的白風夕;也因為有哥哥的包容與教誨,才有今日可駕馭臣將的風惜雲。”她移步走至風寫月最後一張畫像前,目光眷戀地看著畫中淺笑溫柔的兄長,“哥哥是把他想做而不能做的全都交給了我,所以我雖一人身,卻是兄妹一起活著。”
豐蘭息的目光掃過案上的那些手工制作的禮物,大多都簡樸粗糙,可此時,他卻覺得這些比外面那金山玉海更重更貴,這樣的禮物啊,有些人窮其一生也收不到一件!
他伸手取過案上的那只小木船,是風寫月做給風惜雲的第一件禮物,笨拙得幾乎不像一條船,撫過木船身上的刻痕,他輕輕嘆息,“孤獨的青州風氏又何嘗不是最幸福的王族。”
這聲嘆息,沉重卻又冰涼。風惜雲不由轉頭,望向豐蘭息,見他正將手中的木船輕輕放回案上,姿態小心,似乎怕弄壞了。
放好木船,豐蘭息抬首,幽深的墨眸第一次這樣清透,卻如同覆了一層薄冰,可一眼見底,目光卻是那樣的冷,“青州風氏每代都只有一位繼承人,雖然孤單了些,卻不會有手足相殘、父子相忌的殘忍與血腥。你們若得到一個手足,必是珍惜愛護,即算不久會失去,但曾經的溫情還是會留下。”他移步,走近風寫月的畫像,看著畫中風寫月那種溫柔滿足的笑容,忍不住伸出手去輕輕碰觸,喃喃道,“至少這樣的笑容,我從未在我們雍州豐氏身上見過,即算是在我們年幼時!”
那句話,若巨石投湖,重重地砸在風惜雲的心頭,看著豐蘭息冰冷的雙眸,看著他似停在畫上的指尖,剎那間,一股心酸自胸膛間蔓延開來。
“手足之情,我此生已不可得。”豐蘭息終於收回手,移開目光,回首之際,卻瞅見了風惜雲望著他的目光,頓時一呆,心頭驀然悲喜相交。
兩人目光相視片刻,風惜雲先轉身走出石室,“外面的金銀你自可搬去,只是這石室裡的東西不要動。”
豐蘭息跟著她走出石室,“你為何不將這些帶走?”
石門前,風惜雲最後望了一眼那些畫像與禮物,輕輕搖頭,“睹物思人,徒增傷悲。我好好活著,哥哥自然也開懷。這些東西燒了我舍不得,埋了我覺得髒,所以就讓它們永遠留在這地宮裡吧。”
說完,她封了石室,轉身離開,豐蘭息沒有說話,默默跟在她身後。
兩人出得陰暗的地道,再見天日朗朗,環顧庭院,豐蘭息不由感嘆道:“若說地宮是黃泉,那這座宮殿便是碧落。”
風惜雲微微一笑,然後合掌啪啪啪啪四響,瞬間便見四道人影飛落,低首跪於地上,“臣等拜見主上。”
風惜雲微抬手,示意四人起身,“今後,這地宮裡的東西,除我之外,雍州蘭息公子可隨意使用。”
“是!”四人應道,隨即抬首望向豐蘭息。
那刻,豐蘭息只覺得八道冰冷的目光,如同實質的刀般,帶著凜冽的鋒芒掃來。
“你們退下吧。”風惜雲揮揮手,那四道人影便如來時般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豐蘭息回首看著那慢慢閉合的地宮,忽然道:“這些我暫時不會動的。”
風惜雲側首看他,“為何?”
“因為我現在還不是雍州的王!”豐蘭息的話音未有絲毫感情,目光遙遙落向天際,“我明日就回去,有些事也該了結了。”
注釋:
【注1】陸游《置酒梅花下作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