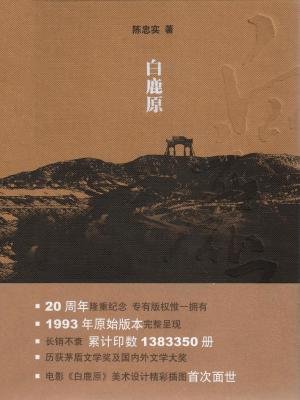商議完畢後,其中一個穿白大褂的醫院領導掏出口罩戴在臉上,推開手術室的門走了進去。
眾人誰也不言語,等著這個人出來回報。
等了幾分鐘,這人快步走出門來,來到張高松身前,將口罩摘下來,恭敬而又愧疚地說:“張省長,手術進行得很順利,令郎手腳傷處都沒什麼大礙,斷筋已經接續上了,陰一莖再植手術也正在進行中,如果不出什麼意外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不過……”張高松臉色陰沉的看著他,等他把話說完。這個人看了看四下,見所有人都望著自己,心中非常為難,心說自己怎麼就那麼倒霉,被派去打聽這種消息,這要如實說明情況,肯定會被這位首長遷怒啊,有心不說,卻也不行,只能硬著頭皮說:“不過……不過被剪斷的陰囊已經無法再植,恐怕……恐怕……”
張高松深吸了一口氣,道:“把話說完。”這人暗嘆口氣,道:“恐怕以後會徹底失去生育能力。”張高松聽到這話,身子一個側歪,好懸沒摔倒。
他秘書眼疾手快,急忙出手把他扶住,同時質問那人道:“為什麼陰囊無法再植,那陰……一莖不是可以再植嗎?”那人哭喪著臉說道:“陰一莖可以再植是因為斷口平整,受創表面未被接觸,減少了被感染的可能性,具備再植條件,可是陰囊……落地時是受創面著地,而且睪一丸全部沾地,已經被污染,不……不可能再植了。”那秘書道:“洗一洗消消毒不行嗎?”
他這話說完,發現在場所有醫院領導醫生都看向自己,那表情就像是看白痴一樣,就知道自己這個外行說錯話了,忙垂下頭去,悻悻的不敢再說什麼。
張高松定了定神,道:“請貴院醫護人員竭盡所能,救護我的兒子,我張高松感激不盡。”眾醫院領導受寵若驚,急忙客氣一番。
張高松對秘書道:“給靖南市公安局長徐建水打電話,讓他去東海路派出所等我。”秘書點頭答應下來,從公文包裡摸出電話薄,翻找了一通後,給徐建水打去了電話。
那幾個醫院領導緊張不安的看著張高松,生怕他遷怒到自己等人頭上。
張高松沒理會他們,對女兒道:“瀟瀟,你陪你媽在醫院,等你弟弟手術完畢,我去趟派出所。”他女兒點頭道:“嗯,你去吧,媽這有我,你放心吧。”
張高松拍了拍她瘦削的肩頭,抬頭對那幾個醫院領導微微一笑,很有風度的說:“讓你們見笑了,你們都回去忙吧,影響你們正常工作,很對不起。”
那幾人這才松了口氣,如蒙大赦,跟他客套一番後快步離去,就好像屁股後面有日本鬼子追著似的,要是不盡快跑掉,就會被干掉。
張高松目送這些人遠去,臉上笑容迅疾全部收斂,換上一副陰沉的神情,對秘書道:“走,去東海路派出所。”
張高松聽得老臉火辣辣的,只氣得喉頭發甜,都要吐血了,恨不得第一時間趕回省第三人民醫院,把張子豪那個小畜牲從手術室裡揪出來,狠狠打他幾個嘴巴,特麼的,別說自己本來就信他可能確實引誘了人家老婆,就算不信,有這個女孩子的筆錄,也得信了,沒瞧見這女孩子也是被他引誘打算搞一宿情的嗎?這簡直就是人證物證俱在啊。擦,他自己**無行也就罷了,竟然也害得他老爹自己堂堂省長在眾人面前跟著丟臉,而且是在這小小的派出所裡當著區區一個副所長丟人現眼,真是氣死我也!
徐建水見張高松沉著臉不說話,就對這個副所長問道:“抓捕嫌疑人有眉目了麼?”蘇副所長道:“事發突然,所裡警力又不太夠,所以暫時……”徐建水皺眉道:“把話說完,暫時怎麼了?”蘇副所長道:“暫時正在按程序辦理。”徐建水皺了皺眉,橫他一眼,問道:“立案了嗎?”蘇副所長點頭如小雞吃米:“立了立了,出警後第一時間已經立案。”徐建水道:“把案子轉到市局,這件事你們以後就不要插手了。”蘇副所長大喜,道:“好,好,我馬上就辦理案件交接手續。”
徐建水當然知道他為什麼這麼高興,因為此案涉及到省長公子,若是破了案抓到凶手還好,但那也算不得什麼功勞,畢竟破案抓人是警局本來的職責,就怕案子破不了凶手也抓不到,那樣顯得無能也就罷了,就怕省長天威雷霆發作下來,他小小一個派出所副所長怎麼吃受得起?鄙夷的看了他一眼,自己心頭卻也蒙上一層陰影。這個案子,自己之所以主動扛下來,自然是向這位首長示好,若是破案以後可以趁機向他表功,即便他不在山南省做官,也能提攜自己一二,可就怕,自己也破不了此案,那就等於是自攬麻煩了。
走出派出所,張高松冷著臉說道:“這個蘇副所長,業務不精,態度不行,也配當所長嗎?”徐建水愣了下,不知道他為什麼遷怒到那個小小的副所長頭上,但還是附和著說:“他能力是有問題,看來有必要離開領導崗位反省一下。”張高松嗯了一聲,道:“建水,咱們也算是老朋友了,這次我不跟你客氣,鬥膽提出兩點要求。”徐建水忙恭敬的說:“您說。”張高松道:“一,盡快把人抓到,我給你三天時間;二,抓到人以後,不許碰他們,給我秘書打電話,我自有安排。”徐建水聽他給出了期限,暗裡發愁,臉上卻不敢表現出絲毫的不滿,道:“老書記您放心,我一定盡全力爭取盡快破案。”張高松斜眼覷著他,道:“你今年多大了?”
徐建水心頭一喜,身子弓得更厲害了,道:“五十二了。”張高松道:“還很年輕嘛。未來有什麼打算?”徐建水道:“我也沒什麼大出息,這輩子也就是在公安系統內混了。還請老書記多提攜。”張高松淡淡地說:“山北那邊公安廳最近會騰出一個常務副廳長的位子來,這件案子你給我辦好,你這個靖南市委常委提為正廳級的常務副廳長不是問題。”徐建水大喜,道:“老書記您放心,這件案子我一定親自主抓,這三天我就是晚上不睡覺,也要把那三個凶手抓捕歸案。”
張高松緩緩點了下頭,又長嘆口氣,往車裡走去。
張子豪凌晨四點才從手術室裡被推出來,在這之前,句曉軍三人已經回到青陽,見到劉安妮,並從她手裡領取了報酬。
劉安妮在原來許諾的報酬基礎上,多給了三人每人二十萬,她可能也已經預感到,自己這次凶殘的報復會讓張子豪那個當省長的老爸瘋狂報復回來,要是被他抓到句曉軍那兩個手下的任一個,自己可能就會被供出來,於是吩咐給句曉軍,讓那兩個參與動手的兄弟出外躲一陣避避風頭,有多遠走多遠,等風頭過了再回來,至於句曉軍本人,出於對他的絕對信任,就讓他留在青陽本地,每天該干什麼還是干什麼。
句曉軍自己也並不擔心會被省城警方追查過來,因為他在動手之前已經做足了反偵察工作,譬如在跟蹤確定張子豪每日行蹤的時候,所開的車前後全部裝上了套牌,這樣一來,就算被神通廣大的警察調取街頭路口攝像機的監控錄像時發現,也絕對發現不了車的信息資料,連車的身份都搞不定,又怎麼會找到自己等人頭上來?再譬如,昨晚動手的時候,三人都戴了帽子口罩,他自己還特意戴了一副茶色墨鏡,不管是張子豪還是路人都認不出他們的面目,因此就算警方跟張子豪或者目擊者嘴裡詢問,也問不出什麼。
這一夜,注定有人歡喜有人愁!
在省第三人民醫院的高干特護病房裡,張高松第一次見到了遇襲之後的兒子張子豪,見他臉色慘白,口唇也有些發青,明顯是身體裡大失血的表現,容顏憔悴,神情迷茫而悲傷,活像是吸毒成癮的癮君子,雙臂雙腿都被固定住,手腕腳腕上捆綁著厚實的繃帶,繃帶上可以看到斑斑血跡,與他身上蓋著的雪白的被子相互輝映,令人觸目驚心,至於他下邊要害處的傷,自然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