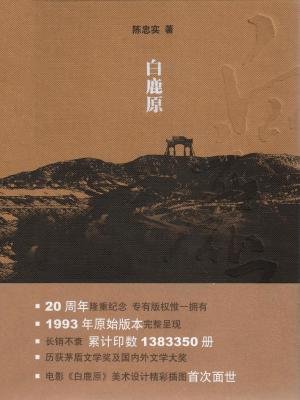麥子收罷新糧歸倉以後,原上各個村莊的“忙罷會”便接踵而至,每個村子都有自己過會的日子。太陽冒紅時,白鹿原的官道小路上,莊稼漢男女穿著漿捶得平展硬崢的家織布白衫青褲,臂彎裡挎著裝有用新麥子面蒸成的各色花饃的竹提盒籠兒,樂顛顛地去走親訪友,吃了喝了諞了,於日落時散散悠悠回家去。今年的“忙罷會”過得尤其隆重尤其紅火,稍微大點的村莊都搭台子演大戲,小村小寨再不行也要演燈影耍木偶。形成這種盛況空前的熱鬧景像的原因不言而喻,除了傳統的慶賀豐收的原意,便是平息了黑娃的農協攪起的動亂,各個村莊的大戶紳士們借機張揚一番歡慶升平的心緒。
俟到賀家坊的“忙罷會”日,賀耀祖主持請來了南原上久負盛名的麻子紅戲班連演三天三夜,把在賀家坊之前演過戲的大村大戶壓倒了苫住了,也把原上已經形成的歡樂氣氛推到高潮。這是一年裡除開過年的又一個輕松歡樂的時月,即使像白嘉軒這樣嚴謹治家的大莊稼主戶,也表現出十分通達賢明的態度。日頭還未落下原去,白嘉軒站在院庭裡宣布:“今個喝湯[1]喝早些。喝了湯都去賀家坊看戲。我在屋看門。”他又走出大門走進牲畜圈場,對剛剛背著一籠苜蓿回來的鹿三說:“三哥今黑你去看戲。我來經管牲口。麻子紅今黑出台唱的是拿手戲《葫蘆峪》。”鹿三推讓說:“你去你去,你也愛看戲喀!”白嘉軒說:“我跟麻子紅已經說妥,給賀家坊唱畢接著到咱村唱,咱白鹿村的會日眼看也就到了嘛!咱村唱起戲來我再看。”鹿三把綴著一串串紫色花絮的苜蓿從籠裡掏出來,碼齊摞堆在鍘墩跟前。白嘉軒揭起鍘刀刃子,鹿三跪匐下一條腿,把一撮撮苜蓿攏起來喂到鍘刀口裡去。白嘉軒雙手壓下鍘刀,哢哧一聲,切斷的苜蓿齊刷刷撲落到腳面上,散發出一股清香的氣味,從土打圍牆上斜泄過來的一抹夕陽的紅光照在主僕二人的身上。鹿三接著給水缸裡挑滿了水,然後推了幾車曬干的黃土墊了圈,再把牲口牽回圈裡,拌下一槽苜蓿,拍打了肩頭前襟後背上的土屑到前院屋裡去喝湯。鹿三是個戲迷,逢著哪個村子唱戲,甚或某戶人家辦理喪事請有吹鼓手為死人安堂下葬唱亂彈,他都要趕去看一場聽一回過一過戲癮。牛犢念書不開竅,整日價跟著鹿三犁地種莊稼務弄牲畜,也就跟著鹿三染上了戲癮。喝畢湯以後,暮色蒼茫裡鹿三咂著煙袋,胯骨旁邊跟著牛犢走出白鹿村看戲去了。
白孝文也是個戲迷。白鹿原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無論貧富貴賤都是秦腔戲的崇拜者愛好者。看戲是白孝文唯一的喜好唯一的娛樂。白孝文已經被確立為白鹿兩姓族長的繼任人,他主持修復祠堂領誦鄉約族規懲罰田小娥私通的幾件大事樹立起威望,父親白嘉軒只是站在後台為他撐腰仗膽。孝文出得門來從街巷裡端直走過去,那些在蔭涼下裸著胸膛給娃娃喂奶的女人,慌忙拉扯下衣襟來捂住了奶子躲回屋去;那些在碾道裡圍觀公狗母狗交配的小伙子,遠遠瞧見孝文走過來就立即散開。白孝文開始替代族長父親到那些弟兄們鬧得不可開交的家庭裡去主持分家事宜,到那些為地畔為牆根為豬拱雞刨打得頭破血流的族人家裡去調解糾紛。他居中裁判力主公道敢於抑惡揚善,決不兩面光溜更不會恃強凌弱。他說話不多卻總是一句兩句擊中要害,把那些企圖在弟兄伙裡撈便宜的奸詭之徒或者在隔壁鄰居之間耍弄心術的不義之人戳得翻腸倒肚無言以對。他比老族長文墨深奧看事看人更加尖銳,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剛剛出山的太陽。他的形像截然區別於鹿兆鵬,更不可與黑娃同日而語。他不摸牌九不擲骰子,連十分普及的糾方狼吃娃媳婦跳井下棋等類鄉村游戲也不染指,唯一的娛樂形式就是看戲。白孝文喝畢湯先禮讓父親去看戲,聲言由自己看門兼侍弄牲口。白嘉軒朗然說:“你去看去。你叫你屋裡人也去,天熱睡不下喀!”白孝文再到上房問奶奶去不去,然後又問母親去不去,奶奶和母親既然都不去,他就再沒有去問自己的屋裡人。他拿了一把竹皮扇子出門上路了。
賀家坊的戲樓前人山人海,濃烈的旱煙氣兒攪和著汗酸味兒在戲台下形成一個龐大的氣團,令人窒息。戲樓兩邊的台柱上掛著兩個盛滿清油的大碗,碗沿上搭著的一條粗捻上冒著滾滾油煙,熾紅的燈火把台子上的演員照得忽明忽暗。本戲《葫蘆峪》之前加演折子戲《走南陽》,被王莽追趕著的劉秀慌不擇路飢渴交困,遇見一位到田裡送飯的村姑,戲劇便在劉秀與這位村姑之間展開。劉秀此時沒有了皇帝的架勢純粹是一個死皮賴娃,不僅哄唆得村姑向他奉獻出籃子裡的蒸饃和瓦罐裡的麥仁湯,而且在吃飽喝脹有了精神之後便耍騷使拐調戲起村姑來了:“今日裡吃了你半個饃,我封你昭陽半個宮。”劉秀唱著許諾著就伸手去摸村姑的臉蛋兒。“今日裡吃了你兩個半個饃,我封你昭陽坐正宮。”劉秀唱著許諾著又撩起腰帶摔打到村姑的前襠裡。麻子紅出演村姑,天生的嬌嫩甜潤的女人嗓音特富魅力,人們已經忘記了他厚厚的脂粉下打著摞兒的大小麻窩兒,被他的表演傾倒了。村姑對劉秀死乞白賴打諢罵俏動手動腳的騷情舉動明著惱暗著喜噘嘴拒斜眼讓半推半就實際上好的那個調調兒,麻子紅把個村姑演得又稚又騷。台下一陣陣起哄叫好打呼哨,小伙子們故意擁擠著朝女人身上蹭。白孝文站在台子靠後人群稍微疏松的地方,瞧著劉秀和村姑兩個活寶在戲台上打情罵俏吊膀子,覺得這樣的酸戲未免有礙觀瞻傷風敗俗教唆學壞,到白鹿村過會時絕對不能點演這出《走南陽》。他心裡這樣想著,卻止不住下身那東西被挑逗被撩撥得瘋脹起來。做夢也意料不到的事突然發生了,黑暗裡有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那個東西。白孝文惱羞成怒轉過頭一看,田小娥正貼著他的左臂站在旁側,斜溜著眼睛瞅著他,那眼神准確無誤明明白白告示他:你要是敢吭聲我也就大喊大叫說你在女人身上耍騷!白孝文完全清楚那樣的後果不言而喻,聚集在台下的男人們當即會把他捶成肉坨子,一個在戲台下趁黑耍騷的瞎熊不會得到任何同情。白孝文慌恐無主,心在胸膛裡突突狂跳雙腿顫抖腦子裡一片昏黑,喊不敢喊動不能動,伸著脖子僵硬地站著佯裝看戲。戲台上的劉秀和村姑愈來愈不像話地調情狎昵。那只攥著他下身的手暗暗示意他離開戲場。白孝文屈從於那只手固執堅定的暗示,裝作不堪漚熱從人窩裡擠出去,好在黑咕隆咚的戲場上沒有誰認出他來。那只手牽著他離開戲場走過村邊的一片樹林,斜插過一畛尚未翻耕的麥茬地,便進入一個破舊廢棄的磚瓦窯裡。
鑽進破爛的磚瓦窯白孝文才感到真正的恐懼。磚瓦窯,大土壕,豬狗貓。他和他懲罰過的白鹿村最爛髒的女人竟然鑽進豬狗貓交配的齷齪角落裡來了,一旦被某個拉屎尿尿的人察覺了就不堪設想其後果。他很自然地想到逃跑,逃離破磚窯一踏上大路就萬事大吉了,和這個女人多在一會兒都潛伏著毀滅的危機。他轉過身抬腳就跑,腦門碰撞到低矮的窯門上也顧不得疼了,剛跑出窯外幾步,田小娥就在後邊大叫起來:“來人喲,救命呀,白孝文糟蹋我哩跑了……”白孝文嚇得雙腿發軟急忙收住腳,立時聽不見她喊叫了。跑不了了!這狗東西把人纏死了!白孝文猛地轉過身又走進破磚窯的門洞,掄開胳膊抽了田小娥一記耳光。田小娥卻順勢抱住他的胳膊,不還手也不反抗揚起頭瞅著他的臉,低聲嗔氣地說:“哥吔你打,你打死妹子妹子也不惱。”瓦罐似的磚窯頂口泄下朦朦的星光,田小娥的眼裡透出兩束亮晶晶的光點柔媚動人,一縷奇異的氣息刺激他的鼻膜,凝聚在胳膊上拳頭上的力量悄悄消溶,兩條胳膊輕輕地垂落下來。田小娥說:“哥呀,你看我活到這地步還活啥哩?我不活了我心絕了我死呀!我跳澇池我不想在人世栽了。我要你親妹子一下妹子死了也心甘了!”白孝文的心開始顫抖,斥責道:“你胡唚亂呔些啥!”田小娥說:“哥呀你正經啥哩!你不看看皇帝吃了人家女子的饃喝了人家的麥仁湯還逗人家女子哩!”說著揚起胳膊鉤住孝文的脖子,把她豐盈的胸脯緊緊貼壓到他的胸膛上,踮起腳尖往起一縱,准確無誤地把嘴唇對住他的嘴唇。白孝文的胸間潮起一陣強大的熱流。這個女人身上那種奇異的氣味愈加濃郁,那溫熱的乳房把他胸脯上堅硬的肋條熔化了。他被強烈的欲望和無法擺脫的恐懼交織得十分痛苦。在他痛苦不堪猶豫不決的短暫僵持中,感覺到她的舌尖毫不遲疑地進入他的口中。那一刻裡,白孝文聽到胸腔裡的筋條如鐵籠的鐵條折斷的脆響,聽見了被囚禁著的狼衝出鐵籠時的一聲酣暢淋漓的吼叫。白孝文咂住那美好無比的舌頭,雙手攬住了田小娥的後腰,幾乎暈昏了。
白孝文忘情地吮吻著,覺察到她的手在摸索著解開他衣襟上的布圪塔紐扣,她又抓住他的右手而且導引到她的腋下,示意他解開她腋下斜襟上的紐扣。他摸住一個個綰結的布紐圪塔解脫紐環兒,順手揭開大襟,把她裸開的奶子摟到他同樣裸開的胸膛上,幾乎迷醉而跌倒下去。他已經無法控制渾身湧動著的春情,第一次主動出擊伸手去解她的布條褲帶,慌亂中把她拴著的活扣兒拉成了死結,干脆從褲帶下把褲腰拉下去。小娥光著身子把磚窯裡未燃燒的麥秸扒攏到一起,再鋪墊上自己的衫子,便躺下去。星光從磚窯頂口泄到她的身上,她靜靜地躺著等待他。白孝文急忙解開褲帶抹脫褲子,剛趴到她的身上就從心底透過一縷悲哀,他的那東西軟癱下來。小娥問:“哥你咋咧?咋是這樣子?”孝文喪氣地說:“我也不知道。”他無奈爬起來重新穿上褲子。小娥也坐起來摸衣服穿。白孝文擋住小娥穿衣服的手興奮地說:“好咧好咧又好咧!”小娥摸了一把就再躺下去。白孝文剛剛解下褲帶抹下褲子,就更加悲哀地說:“咋搞的咋鬧著哩?又不行了?”連著反覆穿了脫了三四次褲子,都是勒上褲子就好了解開褲子又不行了。小娥問:“哥呀你有毛病?”白孝文說:“沒有沒有,向來也沒出過這情況兒。”到他再次不甘就此失敗趴上她的身時卻轟然一聲泄了。田小娥卻柔聲安慰他說:“哥呀你甭難受。你逢七到我窯裡來我等你。”
白孝文重新來到賀家坊戲台下。《葫蘆峪》正演到熱鬧處,台下一片靜默。白孝文小心翼翼地插進人窩裡,卻怎麼也聽不進去看不下去,哐哐啷啷的梆子聲鑼鈸聲失去了魅力令人心煩。他心不在焉地站了一會兒又退出人窩,干脆回家去了。清爽的夜風撫拂著他的臉,腦子裡浮現著田小娥那光亮的胸脯和大腿,鼻腔裡殘留著那身體裡散出的奇異的氣味兒,相比之下,自己那個婆娘簡直就是一堆粗糙無味的豆腐渣了。甭看都是女人,可女人跟女人大不一樣。他走進白鹿村村口時開始懊悔,離家門愈近愈覺心底發虛。他硬著頭皮走進街門時感到一種異樣的氣氛,他的豆腐渣似的女人急慌慌走到院中,看見他失聲叫道:“哎呀你才回來……土匪打搶了……”白孝文像當頭挨了一棍差點栽倒,立即奔進上房,父親白嘉軒躺在奶奶的炕上呼吸微弱,連呻喚都很艱難,冷先生正在桌子上的油燈下配制藥膏。孝文像從火灼的熱炕上跌入冰窖,眼前一黑栽倒在腳地上不醒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