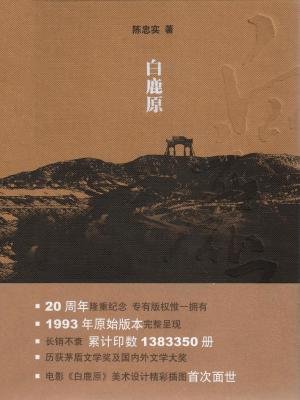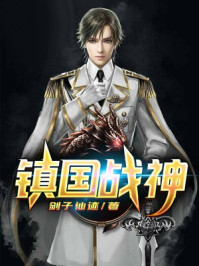那天早晨,郭舉人指派黑娃到十裡外的潘家村去捉一對鴿子,那是老交情潘老大送給郭舉人的一對棕紅色的鳳冠頭兒,回來錯過了飯時。李相和王相已經吃罷飯上地去了,黑娃一個人坐在玉蘭樹的蔭涼下等待小女人端來饃飯。長工吃飯不准進入廚房自拿自舀,這也是郭家的規矩。小女人站在廚房門口說:“鹿相,你稍微等一下下兒,飯涼了我給你熱一下再吃。”黑娃有點緊張,只剩下他一個人就有一種莫名的緊張,裝出無所謂的口氣說:“不怕不怕,不用熱了不用熱了!這熱的天,吃涼飯才好哩!”小女人卻說:“天熱倒是熱,冷飯還是不敢吃。你甭急,稍等一下下兒……”風箱響起來,房頂的煙囪冒出一股藍煙。黑娃坐著等著,心卻無端地一陣陣跳。小女人端著木盤走到玉蘭樹下,把一碟辣椒和一碟蒜泥放到青石桌上,一個竹編的淺籃裡壘著四五個饃饃也放到石桌上,小女人戴著鏤花銀鐲的光潔白淨的手腕就一次又一次伸到黑娃眼前。小女人轉身回到廚房又端來了小米稀飯。黑娃看見她省去了條盤,雙手托著走來了,黑娃連忙站起去接。四只手交接在一只黃色大碗上。黑娃的手指觸到了鉤在碗底上的小女人的手指。那一瞬間,黑娃的心就猛地跳彈起來,竟然不敢看她的眼睛。她似乎毫不在意,叮囑說:“鹿相,你款款吃。吃好。出門在外,飯要吃好。”黑娃吃不出飯的滋味,蒜不辣,辣子也不辣了,饃饃嚼著就像是一團泥巴。他的喉嚨淤塞,胸腔憋脹,頓然沒有一絲食欲了。小女人又走到玉蘭樹下,把一盤腌漬蒜苔放到石桌上說:“你看你看,我忘了給你擱菜了。”黑娃卻站起來:“算咧算咧!我不吃了。”小女人眼裡露出驚疑不定的神色:“你只吃了一個饃?米湯也沒喝,這是咋咧?”黑娃淡淡地說:“我……我不餓。”小女人殷切地說:“咋能不餓?早起到這會兒啥也沒吃呀……”黑娃就誠實地說:“肚裡剛才進門時還餓得慌慌哩,不知咋弄的這陣又吃不下。”小女人溫和地說:“許是路上受了熱。天多熱!你一會兒餓了再來取饃吃噢!”黑娃盯一眼小女人,僵硬地點點頭,轉身就要走了。小女人卻問:“鹿相,俺家掌櫃的說沒說你下來做啥?”黑娃說:“掌櫃的說來,不叫我到地裡去了,叫我照看槽上的牲口,也叫我歇歇腿兒。郭掌櫃人好。”小女人就如意地笑笑:“你來回跑了二十多裡路,這熱的天!歇是該歇的。你給我再絞一擔水,我洗衣裳呀!”黑娃就轉過身走到井口上:“好好好!絞十擔八擔也不費啥!”黑娃雙手上下控制著轆轤,啪啦啦轉著綻開井繩,然後絞動拐把,轆轤吱呀響著,繃緊的井繩一圈一圈纏在轆轤上。黑娃慶幸能有單獨和小女人在一起的機會,心裡潮起向小女人獻殷勤的強烈欲望。他絞起一桶水來,歡悅地問:“二姨把水擱哪兒?”小女人在廂房裡說:“就擱在井台上,我一會兒提。”說著,一只手拎著洗衣盆,一只手提著搓板,從竹簾裡出來了。下磚頭台階的當兒,小女人腳下一拐,摔倒了,木盆在院庭的磚地上滾得好遠。小女人跌坐在台階下,起了三次才勉強站起來,手扶住牆卻移不開腳步,輕聲呻吟著。黑娃連忙把第二桶水絞上來,跑到跟前問:“二姨,你咋咧?崴了腳腕子是不是?”“怕是岔住氣了。”小女人疼痛不堪地蹙著眉頭,“哎喲疼死了!”黑娃站在旁邊不知所措,小女人的痛苦使他心疼心焦:“咋辦呀?二姨,我去叫掌櫃的。”小女人強忍著搖搖頭:“你扶我進去躺一會兒就沒事了。”黑娃就攙住小女人的胳膊,扶她走上台階,揭開竹皮簾子,剛蹺腳進廂房門坎,小女人又“哎喲”一聲,幾乎跌倒。黑娃忙搭上另一只手,攬住小女人的腰。小女人借勢扒住黑娃的肩膀,雙手從後肩和前胸摟住黑娃的脖子。黑娃幾乎是肩背著她往炕前挪步。黑娃渾身燥熱,心似乎已經跳彈到喉嚨口了。他蹺進這個廂房的門坎時,就緊張得腿肚發抖。那溫熱的胸脯貼著他的腰,那柔軟的頭發蹭著他的脖頸,他已經渾身痙攣。他扶她坐到炕邊上剛松開手,她又“哎喲”一聲,幾乎從炕邊上翻跌下來。他急忙抱住她,她的胸脯緊緊貼著他的胸脯,黑娃覺得簡直要焚毀了。他一用勁就把她托起來,輕輕放到鋪著竹篾涼席的炕面上,他感到她摟扒著的手臂依依不舍地松開了。他慌忙抹一把汗,對小女人說:“二姨,你好好歇著,我飲牛去呀!”小女人歪過頭說:“我的腰裡有個老毛病,不小心就岔住氣了,疼死人!你給用拳頭捶幾下就好了。”黑娃遲疑片刻就又走到炕邊,問:“二姨,你說捶哪兒?”小女人用手指著腰肋下說:“就這兒。”黑娃就攥起拳頭輕輕在她手指的地方捶擊。小女人呻喚一聲:“哎喲!太重了!”黑娃就更輕一點叩擊。小女人怨怨艾艾地說:“黑娃你真笨!你輕輕揉一揉。”黑娃就松開拳頭,用手掌撫摩起來。小女人穿著一件白色細格洋布衫,比家織的粗布衫兒綿軟而光滑,溫熱的肌膚透過薄薄的洋布傳感到黑娃粗硬的掌心,胸腔裡便漲起洶湧鼓蕩的潮水,他想跳上炕去把她壓扁擠碎,又想一把揪起她來摟住。但他卻壓抑著種種念頭輕輕問:“你好點了沒有二姨?我該飲牛去咧。”小女人說:“好了好得多了。你再揉一下下就全好了。”黑娃就繼續揉撫著。他看一眼小女人仰躺著的隆起的胸脯,小女人迷離的眼睛異樣地瞅著他說:“黑娃,你日後甭叫我二姨了,你該叫我姐姐……娥兒姐。”黑娃忙說:“那不亂了輩份兒咧?你家郭舉人我叫大叔,怎麼能跟你叫姐呢?”小女人挖一眼他說:“你真是個瓜蛋兒!有旁人在場,你就還叫二姨;只有你跟我在一搭時,你叫娥兒姐。記下記不下?”黑娃似乎心領神會了一個信號,一個期待著的又是令人驚悸的信號,他的頭發似乎倒提起來,手臂抖顫,喉嚨憋得說不出話,只好點點頭。小女人就悄著聲說:“你試著先叫一聲姐……”黑娃咬著嘴唇,自覺血已湧上臉膛,顫著聲叫道:“姐吔——娥兒姐——”小女人聽著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從炕上翻坐起來,撲進他的懷裡。黑娃雙臂緊緊摟抱著小女人,那個美好的肉體在他懷裡抖顫不止。他不知道怎麼辦,一股無法遏止的欲望催著他把她死死地箍抱到懷裡,似乎要把她納進自己的胸膛才能達到某種含混的目標。她的雙臂箍住他的脖子,渾身卻像一口袋糧食一樣往下墜。他就這樣緊緊地摟著她,不知道還應該做什麼。她突然往上一躥,咬住他的嘴唇。他就感到她的舌頭進入他的口腔,他咬住那個無與倫比的舌頭吮咂著,直到她嗷嗷嗷地呻喚起來才松了口。她痴迷地咧著嘴,示意他把她咬疼了,卻又把嘴唇努著迎上來,暗示著他的嘴唇。他在這一瞬間准確無誤地解開了那個啞語式的暗示,就把舌頭伸進她的嘴裡。她的咂吮比他更貪婪更狠勁,直到他忍不住也嗷嗷嗷地呻喚起來,她卻仍舊咂住不放,只是稍微放松了口。她同時就倒下去,背倚在炕邊上,把他也墜倒了,壓在她的身上。這當兒,他的渾身像遭到電擊一樣,一股奇異的感覺從腹下潮起,迅即傳到全身,他幾乎承受不住那種美妙無比的感覺的衝擊,突然趴在她身上,幾乎要融化成水了。那種美妙的感覺太短暫了,像夏天的一陣驟雨,他一身松軟一身疲憊一身輕松,喉嚨裡通暢了,胸腔裡也空寂了,燥熱退去了。他有點懊悔,站起來說:“二姨——噢——娥兒姐,我該飲牛飲馬去了。”小女人跳起來猛地抱住他,又深深地在他的嘴上親了兩口:“好兄弟……”
院庭裡很靜,正午的陽光從玉蘭樹濃密的枝葉間隙投射到磚地上。兩只盛滿水的木桶擱在井台上,洗衣盆扣在牆根下,顯得很凌亂。黑娃把木盆拎起來放到井台下的滲坑邊上,那是小女人往常洗衣服的地方。看看庭院裡沒有任何異常的變化,他撩起布衫下襟擦擦臉上的汗,就走出了這個空寂安謐的院子。他一走進牛棚馬號,順手掩插了門板,撲通一聲仰躺在大炕上,緊張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來,心似乎這會兒才穩定在原來的位置上。他躺了一下就翻起身抹下褲子,這才看見褲襠裡濕了一大片。他迅即系好褲子,把濕了的地方打個褶窩到裡頭,然後就動手去解韁繩,拉上騾馬到澇池去飲水。
他忍著,到了午飯時,李相和王相汗流浹背地從地裡回來了,根本想不到黑娃已經發生的美妙的秘密,只是帶著明顯不飾的忌妒說:“黑娃,你狗崽子比郭掌櫃的干兒子還牛皮!你跟掌櫃的遛馬耍鵓鴿……”黑娃嘿嘿嘿笑著不無得意:“這怪誰呢?掌櫃的硬叫我陪他遛馬,給他捉鵓鴿,我敢不去嗎?”三個人就走進院子去吃午飯。黑娃瞧著小女人用木盤端來了鹽碟辣碟醋碗和蒜罐兒,就不由得心跳;看見她戴著銀鐲的手腕,就回味到握著時的那種溫柔和細膩;瞧見她顫動著的胸脯,就異常清晰地感到貼著時的痴迷和消融。小女人誰也不看,轉身又用木盤托來了三只大碗,碗裡盛著冒過碗沿兒的涼皮。這是暑熱的天氣裡最可口的面食了。小女人放下碗就回廚房去了。黑娃嚼著涼涼的面皮,還是察覺到了李相和王相沒有察覺出來的變化,小女人走路的步子輕盈了,兩只秀溜的小腳麻利地扭著,胸脯上的那兩團誘人的奶子就顫悠悠彈著,眼睛像雨後的青山一樣明澈,往日裡那種死氣沓沓的神色已經掃蕩淨盡。
吃完午飯回到馬號,三人就躺下來歇晌。李相賊氣地說:“這個二婆娘今日個比往日不一樣,大概舉人昨黑個把她弄受活了,你看今日個走路都飄手飄腳的!”話說完就拉起鼾聲。王相也傻笑一聲就齁齁睡著了。黑娃卻睡不著。
整個一個後晌,黑娃和李相王相在播種最後一塊包谷地。他有點神不守舍,吆犁犁歪了犁溝兒,點種又把不住稀稠。長工頭竟破口罵起來:“黑娃,你崽娃子丟了魂了不是?”黑娃不在乎地笑笑。愈接近天黑,他愈變得不可忍耐,直到吃罷晚飯,他也找不到單獨和小女人說話的機會。三人吃了晚飯,抹著嘴起身走出院子時,小女人說:“黑娃,你把泔水桶捎過去。”黑娃心裡得救似的喜悅,從灶房裡提了裝滿泔水的木桶回到馬號,用泔水飲了牛,再把桶送過來,對著正在洗鍋刷碗的小女人說:“娥兒姐,我黑間來。”
黑娃開始實施他後晌種包谷時反覆琢磨過的行動方案:“李大叔,我今黑到王莊尋我嘉道叔去呀。讓他回家時給我捎一雙鞋來。”長工頭李相毫不在意地應允了。黑娃到王村找著嘉道叔叔,確實說了讓他捎鞋的事,又閑諞了半夜在郭家熬活兒的事,感激嘉道叔叔給他尋下一個好主家,並說郭舉人瞧得起自己,讓他陪他遛馬放鴿子的快活事,嘉道高興地叮囑說:“這就好,這就好!人家待咱好咧,咱也要知好,凡事都多長點眼色,甭叫人家先寵後惱……”黑娃應著,早已心不在焉,看看夜深人靜,告別嘉道叔回到將軍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