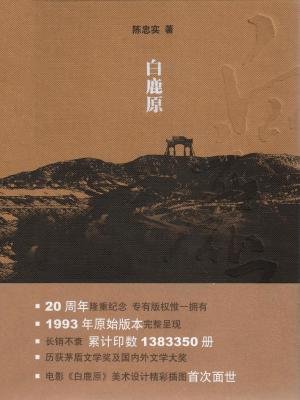白鹿村的“忙罷會”彌散著濃厚的悲愴氣氛。農歷七月初三是會日,麻子紅的戲班初二晚上就敲響了鑼鼓家伙,白孝文通前到後主持著這場非同尋常的演出,忙得奔來顛去。鹿子霖端坐在戲台前角,側著身子對著台下,頭上綰著的那一圈白色孝布,向聚集在台下來自十裡八村的男人女人顯示著悲愴也顯示著強硬。初三的午場戲開鑼以後,白嘉軒來到戲台下,掀起了一陣喧嘩。白嘉軒拒不聽從家裡任何人的勸阻要到戲場上來,顯然不是戲癮發了而是要到鄉民聚集的場合去顯示一下。孝文用獨輪叫螞蚱車子推著父親走進戲場,屁股下墊著一方麥秸稈編織的蒲團兒。男人女人們圍追著車子,想親睹一眼從匪劫中逃生的德高望重的族長,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都向他拋出最誠摯的問候:“白先生好咧?”白嘉軒平靜地坐在蒲團上,雙手扶在小車車頭的木格上,臉色平和慈祥,眼神裡漾出剛強的光彩。他不回答追逐著他的熱誠的問候,端直坐著被孝文推到戲台底下,完全是想來過一過戲癮的樣子。他坐到戲台下看戲這個舉動本身,已經充分顯示了他的存在和他的性氣,臉色和言語上再不需要任何做派了。白嘉軒看見田福賢走上戲樓坐在鹿子霖旁邊,和鹿子霖說了兩句什麼話,倆人一起走到台口向他伸出了手,邀請他到戲樓上就坐。白嘉軒說:“看戲可就興坐在台子下頭才看得好!”
白嘉軒頭戴一頂細辮兒草帽,進入了劇情。午場一般都是短折子戲,晚場才拉開本戲,麻子紅得知白嘉軒晌午要來看戲,有意改換原先的安排出演《金沙灘》,把白鹿村悲愴的氣氛推向高潮。白嘉軒特別喜好楊家將的戲,腰傷和褥瘡的疼痛也為之減輕了。他的眼角掃到了台角上鹿子霖的舉動,鹿子霖正向田福賢介紹一個渾身戎裝的軍人。那軍人謙和地笑著伸出右手,田福賢也伸出右手。戲台下的莊稼人被那種新奇的握手動作所吸引,竊竊議論著那個臉色紅潤器宇不凡的軍人。白嘉軒終於從嘈嘈的竊議聲中逮住一個熟悉的名字:鹿兆海。他不由地心裡一震。田福賢在演員進入後台的過場中走向台前:“鄉親們,這位是鹿鄉約的二子鹿兆海,剛剛從保定陸軍學校畢業,在國民革命軍裡任排長。這是咱白鹿原上頭一個國民革命軍人。”鹿兆海立正之後一個舉手禮,隨之又彎腰連鞠三躬。這是一個真正的軍人,在白鹿原鄉民眼裡和心中第一個留下嶄新印像的軍人。白腿子烏鴉兵無異於土匪,白鹿倉保安隊的團丁怎麼看都更像一伙子笨手笨腳的莊稼漢。鹿兆海戎裝整潔舉止干練,臉色紅潤牙齒潔白,尤其是神態謙和彬彬有禮,就把軍人和土匪明朗地劃清了界線。
這個站在戲樓上向父老鄉親們敬禮又鞠躬的軍人,謙和的微笑下面掩飾著難以排解的痛苦,他和白靈的婚戀發生了意料不及的裂變。鹿兆海走進皮貨鋪子,嗅到一股熟悉親切的毛皮的熏臭。他的到來使皮匠夫婦驚詫愣呆。他羞怯地微笑著把手裡提著的京津糕點孝敬給白靈的二姑和二姑夫,一直等到關門就寢時分,白靈才走進門來。窄巴的鋪店作坊無法提供一個能使他們傾吐熱烈思念的地方,倆人便向皮匠夫婦告辭出門,剛剛拐過街角躲開站在台階上的皮匠夫婦的視角,鹿兆海就緊緊攜住了白靈的手,猛然把她攬到胸前。白靈就伏在他的懷抱裡,不由自主地呻喚出來:“兆海哥!人想你都想死了……”
兆海和白靈偎依著踱過縱橫交叉的小街小巷,在一塊開闊的場地上停住步,倆人都不禁啞了口陷入回憶。這是他倆拋擲銅元的地方。白靈牽著兆海的手,示意他在磚砌的花壇上倚坐下來,貼著他的耳根說:“兆海哥,我和你一樣了。”兆海不經意地問:“你啥和我一樣了?”白靈悄悄說:“我也入了共產黨,和你一樣了。”兆海不由地“啊”了一聲就愣住了,猛然抓住白靈的雙臂:“我已經退出共產黨入了國民黨了……你怎麼正好跟我弄下個反翻事兒呀?”白靈聽了也愣呆在那兒說不出話。兩個久久思念的情人很快清醒過來,便陷入辯論色彩濃烈的爭執之中,誰一時也說服不了誰,各自低下頭摁著手瞧著腳下的土地。一枚銅元當啷響了一聲在地上轉了一圈停下來,倆人嘻嘻笑著蹲下來猜謎。現在回憶那個朦朦月光的夜晚,不再輕松不再歡愉而令人痛苦。“這樣好嗎?你再想想,後日晚我們在這兒再見面。”兆海說。這一提議得到白靈的呼應:“兆海哥,你也好好想想,我盼著後日晚見你時……能得到我想得到的話……”白靈已經喉噎,猛然抱住兆海說:“我等著你的好消息啊兆海哥……”
鹿兆海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他們拋擲銅元的那塊街巷空園裡,沒有等到白靈卻等見了哥哥兆鵬。懸賞緝捕的共產黨要犯一身商人打扮,渾身抖動著的綢衣綢褲,悠哉游哉地搖著一把折疊扇子,走到弟弟跟前時眉毛一揚嘴唇一嘬,做出一個不要驚訝的暗示,親昵地攀著弟弟的肩膀離開了:“走吧別等了。她來不了托我來了。”兆海不悅地說:“她說好來怎麼不來了?剛入了共產黨就得下不守信義的毛病了!”兆鵬說:“你剛剛揣上國民黨證就口大氣粗起來了?告訴你,她擔心你不會改變才沒來。她說她來了要是倆人都不改變怎麼收場?她珍惜與你的感情才不來。她要我來勸你,盼著再見到你時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好兄弟,你有啥話跟哥說吧!”兆海痛苦地嘆口氣:“完了。到此為止。”兆鵬說:“兄弟,沒有完。在我看,一切尚未開始,怎麼就完了?你太悲觀!”兆海說:“我已無法改變。我指望她作改變。她委托你來,就證明她不會改變了。她要是會改變,你也不必來找我了,你肯定是她的領導吧?”兆鵬說:“你們兩個都指望對方改變,可以坐下來好好談談,心平氣和地談談,不要一見面先逼對方改變自己的信仰。暫且談不到一塊也不要緊,等三年兩年也未嘗不可,三兩年裡大家都經見得更多了,判斷和認識是非的能力也提高了,也許就會發生變化。”兆海說:“那好吧!你告訴她,我後天想回鄉下看看父母,只能待一天。回來後部隊就要開拔了。”兆鵬說:“白靈一定要見你一面,讓我跟你約定時間。既然你後日要回原上,你們明晚會面吧?你說在哪兒方便些?”兆海說:“算了不見了。既然誰也改變不了誰,見了也沒個好結果,反倒叫人難受。你告訴她,我等待她的話。”
兆海從原上探視回到城裡,改變了和白靈不再見面的打算,當晚又一次找到皮匠的鋪子。白靈以為兆海有了轉機而欣喜,當即和兆海走出二姑的鋪店,倆人又轉到那個拋擲銅元的園子裡。白靈動情地說:“我以為再見不到你了哩!兆海哥,你也太倔了,一回談不攏二回連面也不見了?真有點國民黨翻臉不認人的通病!”兆海卻火起來:“算了吧白靈!我不說遠處的事,你回咱原上走走看看吧!共產黨在原上搞了一場啥樣的革命你去看看吧!兆鵬用下一杆子啥人你打聽打聽一下吧!鹿黑娃賀老大白興兒田小娥之流盡是一幫死貓賴狗,憑這些人能完成國民革命?他們懂得革命的一分意思嗎?他們趁著革命的風潮胡成亂整,充其量不過是荒年災月飢民‘吃大戶’的盲動……”白靈的那一縷溫情頓然冷寂,忽閃閃躥上一股火氣,她的強盛的氣性迅速恢復,迅即作出反應:“兆海哥,一年多不見,你長了身體長了知識,也長了不少的貴族口氣啊!”兆海說:“你用列寧的理論判我為貴族並不過分。列寧就是把窮人煽動起來打倒富人消滅富人,結果是富人被消滅了窮人仍然受窮。兆鵬學蘇俄在白鹿原上煽動窮漢打倒財東,結果呢?堂堂的農協主任鹿黑娃墮落成了土匪,領著土匪搶銀元,刀劈了俺爺又砸斷了嘉軒叔的腰杆子……作為農協主任沒有達到的目的,當了土匪卻輕而易舉地達到了。你叫我還能信還能再入共產黨嗎?黑娃們干不成共產黨的革命可以當土匪,我可不行呀!”白靈說:“你聽沒聽到賀老大怎麼死的?你聽過你見過把人從高空蹾下來的蹾刑嗎?共產黨就要發動被壓迫者推翻壓迫者,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兆海說:“我們走著瞧吧!看看誰的主義真正救中國。”倆人不歡而散。思想上的尖銳對立,減輕了他和她感情上的依戀,分手的時候遠不及第一次那樣沉重如焚。
鹿兆海緊走幾步又停住腳,回過頭去,看見白靈也站在那兒佇立不動。他走過去對她說:“我明天就要開拔了……”她已忍不住滾下淚珠來:“兆海哥……我還是等著你回來……”
【注釋】
[1]關中人把晚飯通稱喝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