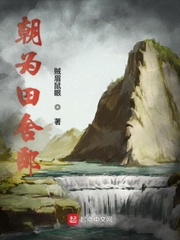聞時回頭一看,車內空空蕩蕩,一片死寂。
仿佛前來送葬的從來只有他們兩個,其他都是錯覺。
四周彌漫著陳舊的灰塵味,皮質座椅像擺了很多年,皴裂斑駁。聞時撐著座椅扶手站起來,卻蹭了滿手鐵鏽。
“我剛剛沒扛住,打了個盹,結果一睜眼就這樣了。”夏樵哭腔更厲害了,“聞哥我害怕……”
聞時目光掃過他“梨花帶雨”的臉,沒吭聲,徑自扶著椅背往前車門走。
“別走!聞哥你別走,等等我,等等我!”夏樵似乎生怕落單,連忙跟上來。
聞時卻沒有等他的意思,順著階梯下了車。
車外還在下小雨,淅淅瀝瀝的。聞時把連帽衫罩上,正要繼續邁步,夏樵連忙抓住他的肩,驚恐地問:“你要去哪兒啊聞哥?我、我不敢亂跑。”
“哦。”聞時終於應了一句,停下步子轉過頭,就見夏樵腳還在車裡,只探了上半身出來,臉上沾了幾點雨,落在眼角的疤上。
“你跑不跑關我什麼事?”聞時看著那個極淺的疤說,“你又不是人。”
那個從車裡探出來的夏樵陡然僵住,輕聲說:“聞哥你什麼意思?我沒聽懂。”
聞時指了指眼角說:“疤點反了。”
空間再次陷入一片死寂。
聞時跟“夏樵”對視片刻,伸手摁了一下門外的緊急開關,大巴車門嘎吱一聲拉平,把那探身出來的玩意兒夾在了門縫裡。
“夏樵”:“……”
等他沿著路往前走,身後便只剩下虛渺的尖叫。
這條路很平直,兩邊樹木高低疏密一模一樣,根本看不出是在往上走,還是往下走。仿佛根本沒有盡頭。
聞時卻沒管,只顧往前走。
這種又窄又寂靜的環境,就像無人長巷。他走了一會兒,連腳步聲都有了回音。
然而沒過多久他便發現,那回音跟他不同步了。
他當即停步,“回音”卻還在繼續,越來越快、也越來越近……
就在身後!
聞時轉身的同時,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
“誰?”他定睛,看到了又一個夏樵。
這次的夏樵痣和疤都沒問題,最重要的是人很鮮活——見面就開始哭,肝腸寸斷的那種。
聞時經驗豐富,一眼就看出他是真的。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夏樵發不出聲音。
他嘴兩邊被人畫了線,像延長的笑唇,一直拉到耳根,又被打了兩個叉,即滑稽又詭異。
這是拿香灰畫的,偶爾也有人能用枯枝。畫活了能禁這個人的言,相當於把嘴巴封了,讓他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誰干的?”聞時皺著眉,從路邊找了點濕泥,給他把那兩條線抹了,“行了,能說話了。”
夏樵抽噎兩下,果真有了聲音。他愣了兩秒,接著癱滑在地,拍著腿嗷嗷哭罵:“畜生啊——”
“究竟誰給你封的?”聞時問。
夏樵還沒開口,就有人替他回答:“我給他畫的。”
聞時抬起眼,就見謝問不知何時跟了過來。
他手裡拿著一截枯枝,掃撥著擋路的藤莖,免得那些沾了泥水的葉片蹭到自己身上。講究得有點過分。
聞時一看見他,臉拉得老長。
謝問走到近處,不慌不忙地解釋道:“我是半路撿的他,叫得太慘太大聲了,慌不擇路抱著頭亂跑。這種環境下哪能這麼鬧,我就順手給他畫了兩道算是幫忙。”
這人說話慢聲慢調,放在平時,可以形容一句“風度翩翩”。但這種時候,尤其在夏樵和聞時眼裡,只加重了那種難以捉摸的危險感。
謝問依然是笑,仿佛脾氣極好。他看了一眼夏樵,又問聞時:“不說謝謝也就算了,還罵我。他是你弟弟,你管不管?”
謝問又道:“看我干什麼,哪句有錯?”
夏樵想辯駁幾句。但不知道為什麼,被謝問眸光一掃,他就像被大妖盯住的下九流小妖,只剩下慫。
比起夏樵,聞時就明白多了,他很清楚謝問的話是對的,這種環境下確實不能哭叫。
就好比他剛剛在車上碰到假“夏樵”,如果當場嚇瘋反應激烈,可能會有更多那樣的東西冒出來,一不小心就永遠困在那裡了。
當然,清楚歸清楚,他就是不想附和。
謝問料到他會是這種反應,也不生氣。
主路上沒有那些枝枝蔓蔓擋路,謝問把枯枝丟回樹叢,對聞時說:“不管就不管吧。有濕巾麼?我擦擦手。”
濕巾又是什麼東西?
聞時心裡納悶,嘴上卻說:“沒有。”
謝問:“那你有什麼?紙巾也可以,能弄干淨就行。”
聞時從長褲口袋裡掏出打火機,蹦出一句:“燒了最干淨,要麼?”
謝問愣了一下,盯著打火機沒說話。
片刻後,他忽地轉頭笑起來,只是笑了兩聲便受了風,很快轉成了悶咳。一般人咳上幾聲,臉色總會泛紅,他卻沒有,依然是病懨懨的白。
聞時腦中忽然冒出一個沒頭沒尾的想法,他覺得像謝問這樣蒼白又病歪歪的人,穿白衣大概挺仙的,穿紅衣……恐怕就是惡鬼相。
謝問四下掃了一圈,在前面找到一處快枯竭的山泉,借著細弱水流洗了手。
夏樵總算緩過氣來,戰戰兢兢地跟緊聞時。他們跟謝問沒有並肩,隔著幾步的距離,朝同一個方向走。
夏樵問道:“聞哥,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聞時:“這叫籠。”
“籠?”夏樵好像聽過這個說法。
他想了很久終於想起來,還是從沈橋那兒聽來的。
沈橋說:這世上人人都有憾事、人人都有心結,有大有小。有些很快便解了,有些怎麼都掙不開放不下,時間久了就會把人捆縛住。靈相上最深最重的怨煞和掛礙都來源於此。
人突逢大病大災或者壽數終結的時候,靈相總是不穩,於是那些怨煞掛礙會反客為主,形成一個局,這就是籠。
如果恰巧有倒霉的人經過,很容易被牽連著帶進籠裡。
對普通人來說,不小心進了別人的籠,那就是白日撞鬼。
但對判官來說,就是該干活了——除穢消業清是非,叫醒籠主,然後送他干干淨淨地出去。
“那、那我們現在去哪?”夏樵又問。
聞時說:“找籠心。”
“籠心是什麼?長什麼樣?”
聞時辨識著方向,說:“一般是建築。”
說話間,前面的謝問忽然抬了一下手,指著不遠處的矮山說:“我看到了,山後面有房子。”
他熟門熟路,顯然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聞時有些驚訝,但很快又想起來,謝問的名字雖然從名譜圖上劃掉了,但好歹比夏樵強。
……只是水平恐怕不怎麼樣。
聞時和夏樵加快步子。謝問還是老樣子,不慌不忙的。於是他慢慢從領先幾步,變成了落後一截,也沒有要趕上來的意思。
聞時很快繞過矮山,來到了房屋前。
那是一座90年代的自建房,兩層,樓前有青石圍牆,抱著一個不大的院子,有兩棵樹叢院牆裡探出來。
“這房子……”夏樵打量一番,喃喃說:“小時候老區那邊好像都是這種房子。”
“老區?”
“嗯。”夏樵點點頭,“我們以前還在那邊住過呢,不過現在這種房子都沒了,拆完了。”
這房子憑空出現,突兀而孤獨地站在山坳裡,小雨帶著蒙蒙霧氣,環繞著它。
“這就是籠心?然後呢?”夏樵有點怕,這種老屋總透著一股莫名的死寂,他並不想離得太近。
……
可是架不住他哥想。
“然後?”聞時說:“然後當然是進去。”
夏樵咽了口唾沫,心說你怕是想我死。
“裡裡裡面會有人麼?”夏樵又問。
這次回答他的不是聞時,而是謝問:“你覺得裡裡裡面的會是人麼?”
聞時:“……”
這人顯然有病,都這種時候了,還有心情開玩笑。
夏樵當場就被這個玩笑嚇哭了,問聞時:“一定要進嗎?”
聞時剛張口,謝問就笑著說:“也可以我們兩個進去,你在外面等。”
“???”
夏樵哭得更慘了。
聞時頭疼。
夏樵斟酌兩秒,覺得還是一個人呆在外面更可怕。於是問聞時:“那要怎麼進?直接推門嗎?”
謝問:“好主意,你去推推看。”
聞時:“……”
他忍無可忍,指著謝問說:“你閉嘴。”然後勉強耐著性子對夏樵解釋道:“推門不行,動靜越小越好,最好不要打擾到房子裡的東西。”
“怎麼可能不打擾?”夏樵腦子裡已經演上了——他們如何如何翻進屋,然後一轉頭,對上一個近在咫尺的青白鬼臉。
“就是可以。”聞時耐心告罄,實在懶得解釋。
但看到夏樵那副慘相,又蹦出一句:“想辦法附在別的東西上。”
判官入籠有時被動、有時主動,但進籠之後做的事情大差不差,他們會借助一些東西,盡可能悄無聲息地到籠心裡面去。
多數會選擇掛畫、照片或者鏡子這類東西,跟人能產生聯系,方便附著,也方便觀察屋子裡的情況。
等到弄清籠主是誰,心結是什麼,他們才會動手幫忙。
夏樵一臉驚恐:“附?活生生的人怎麼附在別的東西上?”
謝問偏過頭,悄聲告訴他:“誰跟你說我們現在是人?”
“????”
夏樵一口氣進去,再沒吐出來。
生人入籠都是虛相,如果受了驚嚇,現實往往會大病一場。夏樵估計是跑不了了。
聞時摸了摸口袋,有點煩。
以往他只要出門,身上一定會帶點東西,比如香灰、蠟油、棉線、黃表紙之類。今早被謝問惹得頭腦不清,居然忘了,渾身上下只有一個打火機。
這要怎麼把人弄進屋裡?
他不爽地悶了一會兒,終於想起來,謝問勉勉強強也算個判官,雖然被劃了,但好歹有過名字。不同分支派系總有些不同的辦法,沒准呢。
於是聞時問:“你有辦法麼?”
謝問“唔”了一聲,“也不是完全沒有。”
聞時懶得聽他扯東扯西,干脆道:“那你來。”
“確定?”謝問順手從旁邊折了三根枯枝,然後衝聞時伸出手。他攤開的手掌薄而干淨,指骨又直又長。
聞時看著那只手,忽然陷入一瞬間的愣神中,垂在身側的手指蜷了一下。
謝問說:“打火機給我。”
聞時捏了捏手指關節,掏出打火機遞過去。
他看謝問點了枯枝,順手插在泥地裡……這些手法比起張家,倒是跟傀術更近一點。
“先說好。”謝問抬眼看向聞時,提醒道:“你應該聽過我那些傳言?我也就會點簡單把戲,水平有限,復雜的做不來。是你主動讓我幫忙的,記住這點,出了差錯不准賴到我頭上。”
他還是帶著笑,說完五指一攏,三根枯枝相撞的瞬間,聞時眼前一黑。
那個剎那,聞時是後悔的。
但當他再睜開眼,發現自己身處在某個房間中,應該是入了籠心,他又覺得謝問的水平還可以。
他沒有輕舉妄動,而是掃視了一圈。這應該是個孩子的臥室,除了床以外,地面鋪著軟質防摔的塑膠毯,印著90年代那種卡通圖案。
角落有小木椅,以及散落對方的積木玩具。顯然房間主人對積木興趣不大,肉眼可見落了一層浮灰。
聞時感覺自己在某個櫃子的高處,只是不知道是照片還是畫,如果有鏡子能看一眼就好了。他剛想找一下夏樵和謝問在哪,就聽見房間門外傳來了吧嗒吧嗒的腳步聲。
應該是一個拖著拖鞋的小孩。
果不其然,下一秒,房間門被打開,一個穿得像公仔的小男孩跑了進來。
籠裡的人往往不是常人長相,五官中的某一點會格外突出,其他則很模糊,就像人的記憶一樣。
這個小男孩突出的地方是眼睛,極大極黑。
他跑進房間又突然停住,然後就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直勾勾地盯著虛空中的某一點。那雙漂亮的眼睛也因此變得有些詭異。
他在原地站了片刻,忽然毫無征兆地歪過頭,朝聞時的方向看過來。
聞時立刻聽到了極輕的抽氣聲,證實了夏樵就在旁邊,只是沒敢說話。
下一秒,那個鬼氣森森的小男孩收回視線,他吧嗒吧嗒地跑回門邊,忽然衝樓下叫道:“我房間裡好多人。”
聞時:“……”
沒多久,一個拖沓的腳步順著樓梯上來了,聽起來年紀不小,是個老人。
從聞時的角度居高臨下看過去,可以看到老人灰白色的發頂,因為背有點彎,看不到他的臉。
老人看到空蕩蕩的房間,先是很輕地嘆了口氣,然後摸著小孩的頭問:“那些人都在哪裡呀?爺爺眼睛花了,要找一會兒。”
小男孩伸手直指聞時的方向:“那邊!”
老人終於抬頭看過來……
他沒有臉。
聞時感覺旁邊有東西哆嗦了一下,然後緩緩下滑。不出意外,應該是夏樵嚇昏過去了。
但他很納悶,往下滑是怎麼回事???畫框也好,照片也好,都不是這麼個滑法吧?
謝問究竟把他們弄到什麼玩意兒裡了?
就在聞時疑惑的時候,夏樵整個滑了出去。
就聽“噗”的一聲輕響,他眼睜睜看著一個穿著粉裙子的人偶娃娃掉在了地上,臉朝地。
聞時:“……”
緊接著,那個沒有臉的老人彎腰把穿著粉裙子的夏樵撿起來,拍了拍灰,擱在床上。他摸了摸小男孩的頭,看著聞時這邊說:“你說的人,就是你這些洋娃娃麼?”
聞時:“……”
這些……
洋娃娃……
聞時一陣窒息,就想知道兩件事:
一、他這個娃娃穿不穿裙子。
二、謝問在哪裡,請他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