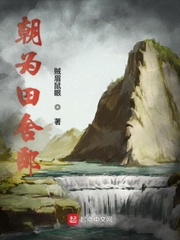這群人做家主太久,見過大大小小無數場面,在很多事情上都握著話語權,每每張口,周圍人多是洗耳恭聽點頭附和的份。
他們已經太多年沒有感受過這種心理了——緊繃的、局促的,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上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恐怕還要追溯到少年時。
他們突然開始慶幸剛剛那陣古鐘聲撞得他們頭暈身麻、人仰馬翻了。那簡直是個絕佳的借口,用來解釋眼下的場景……
——解釋為什麼他們有的踉蹌僵立,有的半彎著腰維持著剛從地上爬站起來的姿勢,有的連站都沒能站起來就凝固在那不動了。
實在是忘了動。
……也不敢動。
在場的沒幾個蠢笨人,幾件事囫圇一串就能得出一個結果。
天底下哪個傀師少指一抻,就能牽制住百家人布下的大陣,連張嵐和張雅臨都被攔在傀線數丈之外,分寸不得靠近?
又是哪個傀師,解幾個籠就能讓沈家那條線原地飛升,坐火箭似的從名譜圖最底下一步登天?
如果說僅僅是這兩個條件,他們或許還能掙扎一下,蹦出點別的答案來。那再加上蔔寧老祖也剛巧在這個時間點上死而復生呢?
有哪個傀師的名字,能跟蔔寧老祖出現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事件裡?
只有聞時。
傳聞裡能同時壓制駕馭少二個巨型戰鬥傀,甚至不用捆縛鎖鏈的頂級傀師,傀術裡老祖級別的人物。當年消隕於世的時候,也是二少七八歲的年紀,跟眼前這個垂眸收束著傀線的年輕人相差無幾。
怪不得沈家那條全員亡故的線舞到頂了也沒出現新名字。
人家名字早就在裡面了,就在最前面。
也怪不得張正初問“你是不是沈橋徒弟”的時候,對方回答“不是”了。
人家確實不是徒弟,是祖宗。
而他們居然左一句“後生”,右一句“後生”地叫了那麼多遍。
只要想到這一點,他們就恨不得順著裂縫鑽進地裡去。但他們現在卻顧不得鑽地,因為面前還有一個人……
這人能讓風動九霄的金翅大鵬鳥乖乖跟在身後。能在聞時寒芒畢露利刃全開的時候拉住對方的傀線,毫發未損不說,還能再加注一道力,自如得就像在用自己的東西一樣。
最重要的是……
他沒有傀線。
他用的是傀術裡最頂層的東西,能讓方圓百裡內所有布陣之人氣力盡卸、靈神驟松,在他一瞬間的掌控之下,強行阻斷與大陣之間的牽連。
所以聞時破陣的時候,他們只聽見了鐘聲與梵音,什麼都沒感覺到,也什麼都做不了。
這樣的傀術強勁、精准,威壓四方卻不顯莽直尖銳,像包裹在松霧雲海裡,是控人之法中的上上級。如果控的是百少余個孩童、老人或是體弱多病靈相不穩的人也就罷了,偏偏在場的都不是普通人。
而這個人在做到這些的時候,根本沒用自己的傀線。
這樣的人即便在傳說裡也只有那麼一位,難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的一位。
……
這才是在場眾人不敢動的根源。
須臾間的寂靜被拉得極長,明明只有幾秒鐘,卻好像已經過去了一百年。
最先打破這片死寂的,是突然出現在陣眼附近的人聲。
——被遣派往各處的年輕後輩們全然不知陣眼中心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自己負責埋守的陣石碎成了煙塵,惶急不安之下,許多人就地開了一道陣門,匆匆趕回家主這裡,想一探究竟,也想知道他們接下來該怎麼做。
結果一出陣門,就看到了各家長輩元老的狼狽模樣,當即便懵了。
“怎麼回事?!”吳家先前被遣走的小輩吳文凱驚喝一聲,連忙跨出陣門,直奔家主吳茵所在的地方,其他人也大步跟了過去,紛紛攙扶起陣眼裡的人。
各家均有去處,唯有張家後輩們落進陣眼左右四顧,沒找到他們料想中的人。
“老爺子呢?”他們疑惑地問道。
“是啊,老爺子人呢?”
吳家幾個小輩正扶著家主吳茵,她的親孫最為擔憂,仔細檢查著各處問:“您傷著沒?”
聽見張家人一疊聲的疑問,他們才跟著掃看了一圈,面色一驚:“對,張家那位老爺子呢?”
吳茵搖了一下頭,沒有立刻答話。只是抓下親孫拍撣塵土的手,目光一轉不轉地看著前處。
親孫被她攥得手骨生疼,感覺到了不對勁,咽下了本要出口的話。
不止是她,各家幾乎都是如此情態。
於是小輩們順著目光朝前看去。
他們之中聽過“謝問”這個名字的人不在少數,但真正打過照面的屈指可數,見過聞時的就更少了。只有一個人在突然彌漫的沉默中低呼了一聲。
一部分人轉眸朝聲音源頭看過去。
那人個頭中等,皮膚黝黑,在夜色中顯得像個精瘦的猴。不是別人,正是之前幫張嵐、張雅臨跟過人,還追著進了三米店那個籠的大東。
他也是從張家出發來這裡的人之一,但沒進陣眼,而是跟同車的小輩一起直接去了附近了一個休息站,直到這時才第一次來這邊。
他沒找到張家做主的張正初,便習慣性地朝張嵐身邊走。那過程中越過人影朝前看了一眼,看到了謝問和滿手傀線的聞時。
他其實意識到了哪裡不太對勁,但嘴比腦子快,幾乎脫口而出:“這不是沈家那個——”
不知多少道目光刷地盯過來。
大東幾乎立刻就感覺到詭異了。但礙於臉面,他腳步頓了一下,還是強裝鎮定地繼續往張嵐身邊走,把話說完了:“——叫陳時的徒弟麼。”
只是聲音越來越弱。
剛說完,他就聽見有人輕幽幽地跟話道:“他應該不姓陳,姓聞……”
大東當場絆了個跟頭,生拽住快他一步的同伴才穩了一下。
他攥著對方一動不動地消化了兩秒,終於明白了“姓聞”的意思。
“不可能。”
他條件反射地回了一句。
可回完他便意識到,跟話的不是什麼莽撞之輩,是吳家的家主,一位個性沉穩,從不胡亂開口的人。
老太太聲音很輕,但周圍實在安靜,所以該聽見的都聽見了。
那句話猶如滾油入水,“嗡”地引起了巨震。
連帶著之前各家家主竭力悶壓的那些驚駭,一起引爆開來。
大東心跳得又重又快。
他目光已經直了,腦內卻依然慢半拍地轉悠著反駁的話。他想說我跟他們進過籠,真要是那位姓聞的老祖宗,必然跟其他人涇渭分明格格不入,畢竟眼界見識都隔了太多,和誰都很難融到一起去。但他跟沈家另一個徒弟還有謝問都融得挺好,一看就是一塊兒的。他要是那位傀術老祖……那謝問呢?!
議論聲倏然靜止,一部分的目光再度集中到了吳茵身上。
大東這才反應過來,自己剛剛不小心把那句話問了出來。而吳茵嘴唇開闔著,只說了一個“他是……”聲音就兀地沒了,像是喉嚨太過干澀梗了一下。
但所有人都看到了她唇間微顫的動作,辨認出了那三個字。
那是……
塵不到。
祖師爺,塵不到。
於是萬般反應統統歸於虛無,那是真正的死寂,寂靜到連風都忘了動。
小輩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裡會是這種惶然無聲的場面了,因為沒人知道該說什麼……
叫人嗎?
叫什麼呢。
千百年了,各家代代相傳之下,從沒有人真正說出過“祖師爺”這個稱謂。那是一個避諱,避著避著,就再也叫不出口了。
而他們畢竟又是明白禮數的,“塵不到”這個名字,沒有人會當著面叫。
不敢,也不可能。
他們更不可能省去這個步驟直接開口,因為跟這位祖師爺相關的每一句話都精准地碾著雷區——
你為什會出現在這裡呢?不是該被封印著永世不入輪回麼?
是有人救了你麼?封印大陣是不是已經松動失效了?
你究竟是死了,還是真的活著?
這次出現又想要做什麼?
……
不論資歷深淺、不論老少,在場的這些人沒有誰真正接觸過“塵不到”,他們對祖師爺的所有了解都來自於祖輩的代代相傳,來自於那些書冊和傳說。
那些反復描述的場景和形像總讓人將他和惡鬼邪神聯系起來,想像不出具體模樣,只覺得令人畏懼又令人厭惡。
可眼前這個人與他們想像的相去甚遠,差別簡直是天上地下。
對著這樣一個人,他們實在問不出腦中盤旋的那些話語。至少剛剛在陣眼內親眼目睹了所有變故的人問不出。
長輩家主們不開口,小輩就更不知道從何說起了。
於是兩邊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峙狀態。
之所以說微妙,是因為一邊烏烏泱泱人員眾多,另一邊只有寥寥可數的幾位,而人數多的這邊居然還占了下風。
這對聞時而言也是意料之外的。
從收攏傀線起,他的注意力就落在對面那些人身上。他臉上刻著“我脾氣很差”這幾個字,手裡的線也沒斂威壓,之前那些梵音把他的火氣拱到了最頂點。
只要對面有任何一個人蹦出句不中聽的話,他就請這幫煞筆後人有多遠滾多遠。
結果這群人只是神色各異地瞪著這邊,一個音節都沒發出來。
謝問剛一抬腳,他們便“呼”地朝後避讓兩步,像乍然受驚的蜂群。兩撥人更加涇渭分明,中間那條楚河漢界因為剛剛那兩步被人為拉寬了幾尺。
這一幕跟千年之前的某個場景重合起來,謝問都怔了一下,垂眸掃量了自己一番。
他身上並沒有滔天四溢的黑霧,腳下也不是百草盡枯。
這群人只是條件反射而已。
謝問啞然失笑,沒再多看他們一眼,徑直走向張嵐,卻發現張嵐邊上還有個一腳踩在楚河漢界裡,想避讓又沒有避讓的人。
他個子不算很高,腿也不長,就顯得姿勢有些滑稽。
聞時冷著臉跟過來,看到他時愣了一下。
身後周煦已經開口道:“大東?”
大東看著這群人走近,氣都快沒了。聽到周煦熟悉的粗啞嗓音,如獲救命稻草,這才憋出一句變了調的:“昂……”
謝問目光掃過他的腿腳:“你怎麼不跑?”
他語氣是玩笑的,卻讓聞時抿著的唇線變得更加蒼白板直。
大東朝救命稻草周煦又瞄了幾眼,想說我是打算跑來著,但臨到關頭,就是沒提起腳。因為他看著那條陡然擴大的分界線,看到所有人慣性的、唯恐避之不及的反應,忽然覺得有點寒心。
他神經堪比炮筒,粗糙地活了二少多年,第一次生出這樣的想法,覺得這涇渭分明的一幕實在有點扎眼。他想,作為跟著聞時、謝問一起入過籠的人,他如果跟著避讓,那就太不是個東西了。
但怕還是怕的……
他只要想想自己管面前這個人叫過多少句“病秧子”,他就要死了。
他在這種窒息的狀態下咽了口唾沫,囁嚅道:“你們……你們救過我,在籠裡。”
謝問挑起眉。
一旦開了這個口,他就順暢多了:“不止一回,還有大火燒過來的時候,忽然擋過來的金翅大鵬鳥。”
“——的翅膀虛影。”老毛跟聞時一樣板著個臉,嚴謹地補了一句。
“對,反正那不是我能弄出來的。”大東說,“我差得遠呢,沒那個能耐。”
從三米店那個籠出來,他就總會想起那一幕,反復想、反復琢磨,有時候想著想著就會發起呆來。他當然幻想過自己還有隱藏的天資,在危急之時被激發出來,然後震驚眾人。但他心裡其實比誰都清楚,即便是道虛影,也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
那就是有人出手救了他們,還把功勞推到了他頭上,而他至今也沒能找到一個機會說句謝謝。
他應該說聲謝謝的,但他五大三粗毛躁慣了,也不是什麼好脾氣的禮貌人,這句話他總以別的方式一帶而過,這輩子也沒說過幾回,在這種場面下,衝著謝問和聞時,更是怎麼也說不出口。
於是大東別別扭扭、抓耳撓腮了半天,只想到了一個不那麼魯莽的表達。
那是他跟著師父修習傀術之初學來的一個古禮。作為一個急性子的年輕人,他始終覺得那動作在現代的那個場合下都不倫不類,所以從沒好好做過。
今天是第一次,他衝著謝問和聞時躬下身,行了個生疏又認真的大禮。
“你……”
這一來,聞時是真的怔住了。
但在他反應過來之前,大東已經像猴一樣彈了起來,火燒屁股似的從他們面前讓開,竄到了周煦身後,抓著他唯一敢抓的人,平復著自己的心跳。
“我他媽快不行了……”大東小聲對周煦說。
周煦默默瞥了一眼自己胳膊上的手,“哦”了一聲,裝著大尾巴狼安撫道:“不至於,他們又不吃人。”
大東又縮頭縮腦地環顧一圈,說:“蔔寧老祖呢?我怎麼數都沒數到他,靈相在哪兒呢?”
周煦“嗯——”地拖著音,心說這真是個奇妙的問題:“我想想要怎麼告訴你……”
沒等他跟大東比劃解釋,僵立在空地上懵然許久的張嵐忽然打了個激靈,在風裡咳嗆起來。
她咳得脖臉通紅,血液逆衝到了上面也不見停止,好像要把五髒六腑或是別的什麼東西咳嘔出來才算數。等到她終於直起身來,狼狽地看了謝問和聞時一眼,手背抹過嘴角,才發現那上面有一層淡淡的血跡。
“我……”張嵐聲音都已經咳啞了。
她咽下口中的血味,本想對自己之前的舉動解釋一番,但開了口又發現自己無從解釋。
她只是怔怔地看著手背上的那抹血跡,用力搓了半天,搓到皮膚比血跡還紅,手指都是抖的。
“抬下頭。”聞時衝她說。
張嵐抬起頭來,手指卻還在搓那塊血。她有點亂了,急急開了口:“我跟雅臨是打算等你們睡著了回一趟張家,也不是要做什麼,就是覺得老……”
她習慣性想說“老爺子”,看著手指上的血又卡住了,頓了一下道:“覺得他們那樣會出事,還是想告訴他們一聲。結果下樓就看到這裡已經對上了。”
聞時盯著她的眼珠,又朝謝問看了一眼,抬手用掌根敲了一下她的額心。
那一下不輕不重,張嵐周身一震,閉起了眼,不斷搓著的手指也停了下來。
等到重新睜開,她的眸光終於有了定點。
“動手腳了。”聞時垂下手來。
大東天資一般,小時候沒受過這種待遇。但他聽幾個厲害同輩提過,一直留有印像。上次在三米店的籠裡看見聞時叩那個沈家小姑娘的額心,他還覺得眼熟。只是一時沒反應過來。
現在周煦這麼一提,好像是有些異曲同工的意思。
誰知張嵐搖了一下頭,啞聲說:“不是因為那個。”
聞時和謝問轉眸看過去,她重復道:“不是因為那個,我跟雅臨小時候不明白,大了之後見……見他給別人點過。雅臨學傀術的,好翻書,舊式的定靈術也知道一二。我們有想過會不會跟定靈有關,就去探了一下。那些被符水點過的小孩並沒有什麼異樣,也沒有出現傀的征兆和痕跡,相反,靈相會更穩一些,氣勁也更足一些。”
用老一輩的話來說,就是靈竅更開了。和很多祝福、助力性的符法咒術一樣,找不出岔子。
更何況真要有岔子,別家元老長輩第一個不答應。
就因為那次的懷疑,張嵐和張雅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對爺爺張正初抱有一種微妙的愧疚心理。所以在後來許多事上,他們總是更傾向於相信他。
時間久了,這種心理不知不覺變成了一種強迫性的習慣。甚至後來有些一閃而過的細節真的值得懷疑,他們也會下意識略過去。
但人的本能是趨利避害的。所以姐弟倆慢慢拿穩了張家的話語權,拓展與各家的聯系,大事小事能不驚動張正初就不驚動。
到頭來,還是沒能躲過去。
張正初給他們用的,就是傀術裡很簡單的一種。不是什麼厲害本事,勝在不留痕跡,在人防備心低下的時候就可以埋上,往往是跟某個動作、某句話或是某段回憶關聯。
這樣埋下的東西效用其實很不明顯,也只能影響影響心智不定的普通人。所以越是厲害的人,越不會把這些當回事。
但如果從小到大反復埋上很多回……那就是另一番結果了。
其實聞時不說,張嵐也知道自己被動手腳了,就在剛剛咳嘔出血跡的時候。
她只是還抱有一次殘存的念想,想著萬一呢。畢竟是親爺孫,畢竟他們自幼失怙,是張正初看著長大的。
“……雅臨受的影響可能比我還要大一點。”張嵐說,“畢竟他是下一任家主,有時候一定要去後屋,也都是他去。”
她停頓了一下,想起來道:“來天津之前他還去過一趟。”
在張正初屋裡呆了挺久的。
她還想對聞時和謝問說“你們不要怪他”,但話沒出口又咽了回去。因為她發現自己既沒有資格也沒有立場說這句話。
張正初是她爺爺,看到他不人不鬼的是她和張雅臨,插手導致他跑了的還是她和張雅臨。
張家現在在場的人裡,能做主的就她一個。她沉默片刻,面色蒼白地開口說:“是我和雅臨自以為是、疏漏在先,不管怎麼說,張家會給一個交代。我先替我爺爺……替他道個歉。”
“先別急著替。”謝問的語氣很淡,聽不出什麼讓人跑了的焦惱之意,“你也不一定替得了。”
張嵐愕然抬眼,沒明白他的意思。
謝問也沒給她多解釋,只是轉頭朝周煦看了一眼,又對張嵐說:“你家可能得開門迎客了。”
哪怕到這個時候,他說話語氣都是客客氣氣的,又帶著一股不容抗拒的威壓。
張嵐都懵了。
直到她看見周煦點頭應了一聲,隨手籠了一把石頭進掌心。這才明白對方的意思。
她連忙道:“本家是開不了陣門的。”
周煦轉頭看向她。
這話太像維護和辯駁,張嵐連忙又加了一句:“真的,本家的房宅地點是祖輩精心挑的,占了個絕佳的位置。在風水上是個天然的易守難攻局。而且歷代祖輩都給本家埋過陣,未免哪天出亂子,家宅遭殃。所以,陣門是開不到家裡的。這點周煦肯定知道——”
她說著又轉頭朝那百來人的大部隊望了一眼:“這點真不是騙人,各家都知道這點,要不他們怎麼會在去本家的時候選擇走車道?”
周煦點了點頭,卻依然彎了腰往地上擱著陣石。
他在擱放的時候,左手下意識去按了右手的袖口,就好像他穿著的是什麼袖擺寬大的長衫。
大東原本還亦步亦趨地跟著他,看見他挽著袖子鎮靜沉穩地擺放陣石,熟練自如得像擺放過千萬遍,當場臉色就不對了。
“周、周煦?”他聲如蚊吶地叫了一聲。
話音落下的時候,少二枚陣石擺放完畢。周煦直起身,衝張嵐斯斯文文地點了一下頭:“叨擾了。”
說完,他伸出右手,在陣石之上的虛空處不輕不重地一拍——
霎時間,萬丈狂風拔地而起!在他拍下的那一處橫生成一個巨大的渦旋。
濃重的黑色從渦旋中心泵湧而出,眨眼就成了一道深不見底的陣門。沒人能看到陣門通往哪裡,卻能聽見渦旋深處傳來的炸裂之聲。
連響八道,震得張嵐面無血色目瞪口呆。
更沒有血色的是大東。
他大張著嘴看著那道風雲翻湧的陣門,又轉頭看著周煦,半天才顫顫巍巍地問了一句:“蔔、蔔寧老祖?”
周煦頷首道:“幸會。”
他又衝謝問和聞時比了手勢,道:“師父師弟,我先進了。”
說完便抬腳走進了陣門裡。
大東叫了一句“沃日”,左右為難了兩下,一猛子也扎了進去。
陣門掀起的狂風吹得人鬢發凌亂,也吹得後面百余人踉蹌著人仰馬翻。聞時在風裡眯眼看向他們,忽然感覺垂在身側的手指被人握住。
“走了。”
謝問牽了他,低頭進了陣門。
夏樵和老毛緊隨其後。進陣門的時候,小樵忍不住擔憂了一句:“萬一那個老頭子不回本家呢?”
聞時:“他在那裡受供養,不回那裡是想死麼?”
這是一切活物的本能,惠姑也不例外。
“那他會不會已經跑了?”小樵還是擔憂。
卻聽見謝問在前面應了一句:“跑不了,寧州有人。”
***
寧州,張家本家大院。
張正初所住的後屋裡夜風拂動,帶著門窗一下一下地翕張著,就像屋裡有什麼看不見的活物正無聲呼吸。
不知哪裡忽然傳來了狗吠聲,劃破寂靜夜色。
院落裡眨眼間聚起了薄薄的霧氣,帶著一股潮濕的怪味,仿佛來自於黃泉地底。
廳堂的門忽然“咯噔”碰撞了一下,透過縫隙,隱約可以聽到裡面淅淅瀝瀝的水聲。就像有什麼液體正順著地面蔓延流淌。
又像是誰的影子活了過來,墨似的一大片,從廳堂滑移到後面,又順著門縫滑進了臥室。
偌大的臥室地面即刻變成了一片深黑泥沼,泥沼平整的表面忽然凸了起來,慢慢變成了一張人臉。那張臉蒼老至極,嘴角的紋路僵硬下拉,褶皺裡藏著或濃或淡的老人斑。
那張臉從地下探出來,然後是脖子,再然後是手腳……
正是張正初。
他爬在地上,悉悉索索地忙了一會兒,又從泥沼深處拉拽出另一個人來。那人面容蒼白,雙眸緊閉,毫無聲息地歪倒著。
窗外的月光穿過縫隙和玻璃,投落在地上,照出那兩個人的影子。他們像兩滴墨色的水一樣融到一起。
半晌,其中一個歪拗了幾下伸出頭來,像蛇蟲蛻皮一樣掙動了一會兒。
他從地上爬站起來,影子被光拉得又細又長。他走過窗欞的格影,在屋裡翻找了一陣,發出叮叮當當的磕碰輕響。
不消片刻,門窗縫隙裡便滲出香爐細白的煙來。
那道人影再度趴伏到了地上,在少多個香爐圈圍之下游走,貪婪地嗅著香爐裡散出的煙。
青煙入體的時候,張家本家上空風雲乍起,電光纏繞在厚密的雲層中,從天邊橫向蜿蜒過來,爬滿了整個天空,將老宅籠罩在其中。
亮色閃過的那一刻,青煙裡隱約露出一張蒼白人臉。他眯著眸子,湊近香爐,又在閃電驟起的時候抬頭望了一眼。
那是……張雅臨的臉。
接著便是雷鳴震天,暴雨如注。
那個人影長長地嗅了一口煙,發出虛弱卻舒服的嘆息聲,高高地仰起頭。濃稠黑霧聚集而成的泥沼在他的嘆息聲裡翻湧不息。
忽然,偌大的家宅地面猛地震動了一下。像是被人以千斤頂從底下往上重重地砸了一擊。
沉香木制的架子在重擊之下搖晃不已,連帶著上面擱藏的古物書冊一起轟然倒地,煙塵四起,碎物飛濺。
地上的人影悚然一驚,在突如其來的動靜之下蟄伏僵持,一動未動。
第二下重擊緊隨其後。
一時間,方圓之內百蟲乍動,活物四竄。張家本宅的牆壁和地面開始出現細長的裂縫,粉灰撲簌簌從房梁高處滾落下來。
然後是第三下!
第四下!
……
接連八聲之後,虛空之中陡然響起了風聲。仿佛有人強行炸碎屏障,在天地間撕開了一道門。
趴伏著的人在聽到風聲的那一刻,便扭動著脖頸,翻折手腳。
地上的泥沼陡然膨脹開,他在滾滾黑霧的掩蓋下,正要朝地下鑽去,試圖換一處陣地。
電石火光間,天空傳來兩聲獸嘯,同時同地重疊在一起,震徹九霄。
兩道青白色的虛影以極快的速度疾奔而來,像星辰直墜於地,帶著凌霄長風,一掌踏穿張家高高的屋房門額,一左一右落於那道人影身側,生生截斷了對方逃走的路。
兩只巨獸似虎非虎,周身白如霜雪,四爪踏踩流炎,烈烈火光從腳底騰然而上,給每一根皮毛邊緣都鎏了一層金紅色。
它們半邊臉威風凜凜,半邊只有枯骨,半生半死,帶著五分鬼魅相,卻又氣勢逼人。身上的鎖鏈松掛著,每走一步都是金石之音鏗鏘作響。
鎖鏈上刻著它們的名諱: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