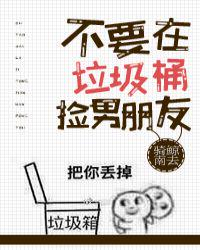第194章 霸道將軍俏軍師(十三)
婁影選了個非常利己又利人的職業,池小池就算天天鑽他帳篷和馬車,都會被底下的士兵認為是勤勉刻苦,日夜不輟。
此刻,兩個人在行進的馬車裡吃草莓。
草莓是用褚子陵的好感值從倉庫裡兌換出來的,只要不取出來,就是無限時保鮮,個頭大,味道也甜,清洗更是不需費心。
婁影體寒,吃了兩個嘗過味道就算了,將草莓蒂摘掉,殷紅漂亮地擺滿了一盤子,一邊看書,一邊時不時抬手,一顆顆地喂池小池吃。
池小池忙著打他幾天沒打的“魔神召喚”,騰不開手。
自那日起,已過去了整整七日。
池小池一覺醒來,也不提昨天一卡把自己拍暈之前的事情,仿佛是忘了個徹底,讓婁影有點懷疑他是不是捎帶手把失憶卡也給用了。
直到婁影不經意瞟了一眼顯示屏方向,發現他在“魔神召喚”裡的id偷偷改了。
不再是“樓台倒影入池塘”,而是池小池。
……規矩又正經得讓婁影想敲他的頭。
不過直到最後他也還是沒舍得,只好塞了顆偏大的草莓到他嘴裡泄憤。
不久後,馬車窗外傳來輕輕的叩擊聲。
池小池將草莓收回倉庫,伸手撩開車簾。
褚子陵騎馬,與馬車並行,彎腰道:“公子,將軍又遣信使回望城了。官道上遇見後,他說將軍有一封信,順道給您。”
“信使呢?”
“馬不停蹄趕回望城了。”褚子陵頓了頓,“看那信使面上神色,該是喜事。”
時停雲一喜,接過信函,還挺俏皮地對他一眨眼:“謝了。”
褚子陵余光一瞥,只見那公子師坐在陰影處,用手背擋著從簾外射來的光,能看出他眉頭微蹙,不很高興的模樣。
褚子陵心裡不由一跳,拿捏得當地露出了三分懼意:“公子師,我馬上離開。”
受時停雲蔭護多年,褚子陵從未跪過三個時辰之久。
那一天,雨水淅淅瀝瀝地落了一整夜,膝蓋上的皮膚吸飽了水,被泡得發白,地上的石子異常粗糲,磨得他膝蓋鑽心地疼。到現在,他膝上的傷還未痊愈。
傷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從未受過這等直白的侮辱。
褚子陵自是不能白白受了這侮·辱的。
於風眠既是有意針對於他,他便對於風眠表現出十足的畏懼、退避,既遂了他的意,又叫他找不到其他理由來對自己做些更出格的事情。
而他若是硬要找茬,那更好。
他褚子陵在軍中不是籍籍無名之輩,又出身平民,與不少將士都談得來,而姓於的頂了一個公子師的虛銜,但說白了,不過是曾遭發配的罪人,無半寸軍功傍身,平白得了榮華,又因著體弱,只能坐馬車前行,軍中已隱有不滿之聲。
只要自己多多示弱,無需多說什麼,自會有人替他不平。
這聲音若是傳到公子耳中,要麼公子回護,引起底下將士不滿,生出芥蒂,要麼是日久天長,公子對於風眠產生不滿。
不管釀成了哪一種後果,都與他無干。
他一不在背後嚼舌,二不顯出不滿,處處周到,任誰也挑不出錯來。
然而於風眠只是伸手擋了擋光,沒有理他,只顧倚在軟枕上看書,仿佛褚子陵都不值得他多瞥上一眼。
時停雲放下了車簾。
回過神後,褚子陵的心卻不自禁地狂跳起來:
這就是他的機會了!
從鎮南關到望城,他們押運著糧草輜重,行軍速度緩慢,起碼要二十五日。加急的快馬需得三日,將軍府豢養的一羽好鴿子,快的兩日,慢的兩日半就能飛抵。
現下,是他動手的最好時機!
等抵達邊城,他再想找機會給時驚鴻下·毒,那便難了。
時驚鴻乃是南疆心腹大患,非殺不可,而且,只有他死了,時停雲才有上位之機。
時停雲的機會,便等於是自己的機會。
想到這裡,他把目光投向前方,那位脊背筆直的十三皇子正低頭,一邊馭馬,一邊單手握著一本兵書看,看被微風拂起的卷冊封面,正是昨天閑談時,時停雲推薦給他的那本書。
褚子陵不得不承認,此人與於風眠一樣,都是不在他計劃中的變數。
但他仍是粲然一笑。
變數利用得好了,就是棋子。
就算多了一名十三皇子,那又如何?
一個一無威信,二無兵權的少年,哪怕武藝超絕,若是逞能冒進,也是個死。
畢竟戰場之上,弓矢不長眼,可不會認他是皇親國戚,還是平民百姓。
在他構想的功夫,車簾又被撩開了。
車簾後是時停雲喜形於色的臉:“阿陵,取紙筆來。”
褚子陵很聰明地沒有在公子師面前詢問他有了什麼喜事:“是。”
不外乎是邊關勝仗之類的事情。
他不關心南疆那邊死了多少人,也不關心北府軍這邊有多少傷亡,他只希望,在自己的計劃推進到最緊要的那一步時,南疆的局勢不要太差。
他取了紙筆和小桌案來,捧入馬車中,又取了小木筒來,在外等候。
時停雲回信向來快,不過小半時辰,內裡便傳來擱筆聲。
“信筒。”
褚子陵依言呈上。
時停雲待墨跡稍干,把紙張卷細,塞入小信筒,又合上扭蓋:“印章。”
說到此處,時停雲抬眼,注意到褚子陵額上的一層薄汗:“算了,你這一趟趟的,跑著也累,你找到印章後,用火漆印將信封好,便用信鴿送出去吧。”
褚子陵心中猛然一喜,心髒砰砰跳了起來。
這麼順利嗎?
他本打算在敲上火漆印後,在有·毒的印泥上再滾一圈,哪怕印記模糊些也不打緊,反正鴿子有時在路上歇腳飲水,或趕上雨天,也難免會把火漆弄花些。
沒想到時停雲竟會將蓋章的事情交給他做……
還未等他想完,馬車角落裡突然冷冷地響了一聲:“停雲。”
褚子陵心一寒。
於風眠……
誰想於風眠道:“莫要喜形於色,穩重一些,方能為將士們做好表率。你來,同我講一講這章書中說了些什麼,你又有何見解。”
說罷,他往褚子陵臉上剔了一眼:
還不去辦事?
褚子陵領命,駕馬離去。
待走出一段距離,他才發現自己手心裡都是汗,將把木筒都沁濕了。
他用袖子擦拭了幾下小木筒表面,第一次沒能掩飾住自己的喜色,嘴角的笑意越來越大。
然而即使如此,褚子陵仍保持了十二萬分的細心。
他沒有拆開小木筒,查看內裡寫了什麼。
他記得清清楚楚,將軍府內的信筒是特制的,筒蓋上有一個內置的小機關,完全蓋上後,小機關便會自動打開,在內裡生成一小片尖木片。
從外面看,是看不出什麼端倪的。但若是合上再開封,與筒蓋接合的筒身上便會留下小小的一道擦痕,無法抹去。
時驚鴻心細,若讓他開啟筒身後,發現了另一道痕跡,定會起疑心。
褚子陵可不想讓千裡長堤潰於一枚小小的蟻穴。
他與專門保管印章的親兵相熟,只說是奉公子命,便如以往無數次那樣,輕而易舉地請出了時停雲專用的圓章。
褚子陵沒有用公子用過的那方火漆塊,而是一個解開了另一個小匣子上的祥雲扣,取出了一方全新的火漆。
同為將軍府特制的火漆,這一塊的色澤、光感、形狀比之另一塊,絲毫不差。
褚子陵點燃火折子。
火焰在他眼眸裡跳躍幾下,火漆的前段開始融化了。
在他有些狂熱的目光下,一滴飽含鴆毒的毒·汁,滾燙地滴落在了小木筒的封口處。
啪。
鮮紅的印章落下,一道烙著“時停雲”三個字的有·毒鈐記,在太陽照射下,散著有些刺目的光。
蓋章是在身側有人的情況下執行的,那親兵一直守在旁邊,絲毫破綻都沒能看出。
褚子陵抬手,打算把弧形圓章遞還給親兵:“有勞。”
結果二人交錯時,褚子陵低頭收起火漆塊,一錯眼,一失手,圓章滾落在地,沾了些黃泥。
褚子陵一驚,抱歉道:“抱歉,我去幫你清洗。”
不遠處便是清溪,他自然地捧了那章去,一點一點把印章上沾著的鴆毒洗去。
他嘴角帶著笑意,一如往常。
傍晚,隊伍駐扎了下來。
聞到飯香時,躲在帳中悄悄給那南疆文官寫信的褚子陵一怔。
……看來,鎮南關那邊,當真是一場大捷了。
果不其然,當夜,時停雲自掏腰包,在旁邊的村落裡買來了羊,烤了二十只羔羊,五十只成羊,分給全部將士。
這點肉食真要分的話,每人也分不到多少,但已是時停雲在短時間內能搜羅來的全部,將士們也不會在意這些,個個歡欣鼓舞。
定遠大捷。
前來攻城的南疆人死傷慘重,五千軍士,無一回還。
“虧得公子師獻策!”時停雲站在高台之上,滿懷欣喜地一指台側頭戴冪籬的於風眠,“南疆人用了填濠之術,悄悄運來木排浮舟,企圖強渡護城河。先生獻計,觀察敵方來向,在城牆下側挖下小洞,趁夜色悄悄注油入河,又趁風勢引火,將來犯之敵燒了個人仰馬翻!”
褚子陵想像了一下那個畫面,笑容微微僵硬在臉上。
這於風眠面上不顯,卻是十足的心黑手毒。
而公子這般大舉慶賀,也在無形中為於風眠在軍中打下了威信。
眾將士有些還沒上過戰場,聞聽喜訊,也將一個“好”字喊得震耳欲聾。
吾國之土地,不讓分毫!
站在台上的池小池在激昂的群情中靜了下來,跳坐在了高台邊緣,望著這群不過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圍著火堆大聲談笑,跳舞,劃拳。
堂堂的火光映亮了他們年輕的臉。
他們可能在未來的某時某刻,會化作戰爭焦土上的無定骨。
池小池惟願他們死去的那一刻,仍做著千秋家國之夢。
他擰開腰間酒壺,喝了一口,視線微轉,在連綿的一片火光中,看見了十三皇子嚴元衡。
嚴元衡像在發呆,與他對視許久,方才略不自然地轉開臉去,邁步欲走。
身後傳來一聲輕浮的口哨聲。
嚴元衡本以為時停雲在叫自己,身體稍轉,悄悄側過視線去,卻發現並非如此。
時停雲早已看向了另一個方向,將酒壺扔給了近旁一個酒壺空了的年輕士兵,旋即跳下高台,朝於風眠跑去。
……竟是看也沒多看他一眼。
嚴元衡心髒一熱,又是一酸,也不知是哪裡冒出的念頭,驅使著他快步向前,站在了那個接了時停雲酒壺的青年身前,指一指黑金色的酒壺:“我可以喝你一口酒嗎。”
那士兵張嘴欲飲,見到十三皇子向他討酒,差點把酒倒在自己臉上。
他受寵若驚,跳起身來,雙手奉上,結結巴巴地請他用。
嚴元衡抱著酒壺,在士兵中坐下,破天荒地問了不少話。
畢竟都是同齡人,士兵們見這十三皇子沒有什麼臭架子,說話雖然文縐縐的,好在不吊書袋,能聽得懂,便也漸漸同他熱絡起來,還撕了羊腿給他。
嚴元衡捏著酒壺嘴兒,抱在懷中一口未飲,也不再提還給士兵的事情。
當夜。
褚子陵將“小心於風眠”一事添寫於信件末尾,確認自己已將向時驚鴻下毒之事說了個明白,便將事前藏好的小木筒取出,放好信紙,將筒蓋扣好,在表面蓋上偽造的弧形圓印,便來到了鴿籠前。
軍帳中巡夜的人仍按往常一般行事,絲毫不受那狂歡的影響。
褚子陵一路避人繞行,來到鴿籠前,取出那只額前有白記的鴿子,在它的足上綁好小木筒。
身後有腳步聲傳來:“誰在那裡?”
褚子陵回頭:“我。褚子陵。”
“是少將軍的近侍啊。”巡夜的隊長不大認識褚子陵,只聽過他的名字,聞聲便放下了心來,“這麼晚出來,有事?”
褚子陵面不改色:“替少將軍辦事。”
巡夜隊長嘆了一聲“少將軍辛苦”,便引著小隊離開,再無懷疑。
褚子陵背對幾人,冷冷地挑一挑嘴角,放飛了手中的鴿子。
鴿子撲棱棱扇動翅膀而去。
在偌大的軍營中,放飛鴿子的聲響不算很大,至少不可能傳到主帳中去。
他撫著腰間那塊對他來說意義非凡的玉佩,直到鴿子消失在他目力所及範圍之內,方抬步往主帳方向走去。
……不過是一場小勝而已。
鎮南關真正的戰事,由他褚子陵而始。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主帳中的兩個人仍未入睡。
池小池問婁影:“他放鴿子了?”
婁影單指輕抵著太陽穴,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只能草草應道:“嗯。”
池小池便不打擾他了。
直到婁影的身體往下軟了軟,垂下手來,長舒一口氣。
池小池忙給他擦汗:“成了?”
婁影閉上眼睛,微微喘著:“放心。那是地磁定位算法的最優解。”
鴿子識途的方法與人不同,是靠微妙的磁場力辨別方向。
婁影能夠保證,在他對磁場的干擾下,褚子陵放飛的兩只鴿子,都會去到它該去的地方。
事已辦成,池小池也放松了不少,拍拍他的肩膀:“我去給你拿吃的。”
送走第一只鴿子,已經耗費了婁影太多的精力,讓他連晚飯都沒胃口吃。
他睡前特意交代阿書,讓他燉一點湯,准備幾碟小菜備著,一定要清淡些。
一只手輕輕抓住了他的袖子:“不用。我不大想吃東西。”
池小池忙著穿鞋:“不吃東西不行。我去給你拿。你想要點什麼?我讓阿書做了幾樣……”
他剛剛起身,腰身卻被一只手臂從背後圈住,一下沒能保持住平衡,跌坐在床上。
耳畔是婁影的聲音。
明明那聲音並無實質,池小池卻有了被那聲音一下下輕觸撫摸著耳朵的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