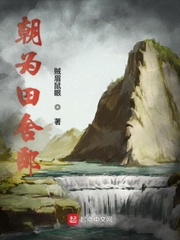葡法兩國贈送的禮物,都存在海港的倉庫裡。
等中國使節團回航的時候,不但要帶走那些禮物,還要帶上兩國使臣隨行。其中,動物是最麻煩的,法國送的馬種、葡萄牙送的羊種,還得專人養上一段時間,肯定無法隨船到處奔波。
馬和羊,都是中國使團主動提出購買的。一聽數量不是很多,兩國王室都懶得收錢,還派遣官員去精心挑選。
再次來到恩典港,海峽對岸便是英國。
“什麼書?”張瑞鳳問道。
宋欽回答:“書名很長,也不曉得是否翻譯正確,叫做《正確思考和發現真理的方法論》。作者是法國名士笛卡爾,他跟陛下一樣,居然創立了解析幾何。他的數學理論,在法國頗受推崇。但他的哲學思想,卻慘遭法國學者圍攻。”
隨船出海的兩院學者有四個,宋欽來自欽天院。
他沿途都不怎麼說話,只觀察記錄地理情況,剩下的時間全在學拉丁文。到了法國,也不去參加宴會,窩在盧浮宮裡學習法文,偶爾帶著翻譯跑去逛書店。
笛卡爾的《方法論》,此時只有法文版,還沒有拉丁文版。雖然問世已經十多年,書中的數學方法頗受追捧,但他的哲學著作卻被貶得一無是處。
船只搖搖晃晃駛向英國,張瑞鳳正好閑著沒事干,就問道:“書裡寫了些什麼?”
宋欽說道:“包羅萬像,有數學、物理等等。真正寶貴的,是闡述如何做學術研究,陛下得到此書必然龍顏大悅。”
張瑞鳳聽不明白:“你講具體些。”
宋欽說道:“比如光學,笛卡爾的研究,跟欽天院的學究,在很多地方都是契合的。其難得之處,是用光學原理闡述眼睛如何視物。我們都知道,眼睛挖出來是球體。笛卡爾認為,眼睛就是一個凸透鏡……張大使可知凸透鏡?”
“咳咳,”張瑞鳳咳嗽兩聲,微笑道,“你繼續說。”
宋欽說道:“將軍們使用的千裡鏡,鏡片便是凸透鏡。在笛卡爾看來,我們每個人的眼睛,都是一部千裡鏡。至於書生近視,皆因凸透鏡出現問題,導致光學焦點產生變化。”
“原來如此,”張瑞鳳不明覺厲,保持微笑道,“你繼續說下去。”
宋欽說道:“笛卡爾的力學宇宙觀,也跟欽天院一些學者不謀而合。笛卡爾甚至更極端,認為除了思想之外,整個宇宙都是機械運動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用力學來闡述。所有動物,包括人類,也受復雜的力學定律支配。更為寶貴的,是笛卡爾提出的,學術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不待張瑞鳳說話,宋欽就侃侃而談:“認識論有三:第一,哲學是一切自然學科的基礎,要求真實可靠。第二,以往的哲學(科學),理論體系有缺陷,甚至源於錯誤的基礎認知。第三,基礎錯誤或不可靠的原因,是確立基礎的方法不正確,甚至沒有方法,所以必須有方法論。張大使可知,這些對欽天院來說有多重要嗎?”
“多重要?”張瑞鳳問道。
宋欽說道:“便如《朱子語類》之於宋明理學。”
張瑞鳳目瞪口呆,他知道皇帝重視欽天院。但如今欽天院的自然學科,還沒有高屋建瓴,也沒有形成嚴格體系。如果真如宋欽所說,那這本《方法論》帶回去,欽天院的學問就能開宗立派了。
宋欽越說越激動,笛卡爾的方法論內容,帶給他醍醐灌頂的感覺。
笛卡爾的方法論四原則:
第一,拋開一切成見,確立理性權威。以理性檢驗一切知識,檢驗標准是清晰明白、無可置疑。
第二,把研究對像,拆分成盡可能細小的部分,直到可以圓滿解決問題。
第三,研究科學,要有次序,由易到難,由簡入深。沒有自然次序的研究對像,要人為的給它定一個研究次序。
第四,研究問題時,要盡可能列舉所有情形。有些問題的答案,適於這個情形,有些適於那個情形。要做到普遍性研究,確信沒有遺漏。
認識論的三點內容,方法論的四個原則,可以說是在給科學研究搭建穩固地基。
不遵循這些,科學就不成體系。
張瑞鳳也聽不懂這些,連忙轉移話題:“笛卡爾既然如此了得,何不發出邀請,帶他回南京面聖?”
宋欽說道:“在下打聽過了,笛卡爾一直住在荷蘭。”
事實上,笛卡爾早就去瑞典了,擔任瑞典女王的私人老師。
瑞典天氣寒冷,他每天半夜就起床,五點鐘給女王上課。每日被冷風吹灌,不幸染上肺炎去世……
身為法國人的笛卡爾,之所以長期定居荷蘭,是他的研究太過驚世駭俗,經常挑戰教會和耶穌的權威。荷蘭那邊信的是新教,稍微要開明一些,不會莫名其妙被燒死。
即便如此,笛卡爾寫完《論世界》(《哲學原理》),也憋了快十年才敢出版。
因為在《論世界》完稿的時候,從意大利傳來一個消息,伽利略由於贊同日心說,被羅馬教廷宣判有罪。
伽利略的人緣很好,沒有性命之憂。被判跪在石板上簽悔過書,另外終身監禁,《對話》必須全部焚燒,其他書籍禁止出版或重印。後來,改終身監禁為居家禁足,一直被軟禁到病逝。
相比於日心說,笛卡爾的《論世界》更為激進,他完全用自然科學闡述宇宙。
笛卡爾還有更離譜的哲學理論:因為我的存在,上帝才存在,世界才存在。
可惜啊,中國使節團只要早來幾年,就能在荷蘭遇到活著的笛卡爾。
除了《方法論》之外,宋欽還買了笛卡爾的其他書籍。
法文書他看不太明白,拉丁文書籍卻能大致讀懂,於是窩在船艙裡繼續閱讀。
此時宋欽閱讀的,便是《哲學原理》。此書原名《論世界》,出拉丁文版的時候,改名叫做《哲學原理》。
書中包含《方法論》的三篇文章,又增添了其他內容,總的論述物質、世界和地球。
為了獲得教會認可,防止自己被禁書,笛卡爾還在序言裡,聲稱上帝是全能的,創造了宇宙的一切。他的任何研究,都源於上帝賦予的思考能力,這種思考能力是不會錯誤的。
但字裡行間,明顯可以讀出,笛卡爾根本不信上帝,他說“有一位上帝”創造一切。
加個“有一位”,耐人尋味啊。
其他使節團成員,都視歐洲為蠻夷之地,骨子裡充滿了鄙夷。但宋欽讀了笛卡爾的書,卻迅速摒棄這種成見,他覺得歐洲還是有大學問家的。
《哲學原理》就讓宋欽很痴迷,雖然書中的一些內容,他並不認可,甚至覺得那是錯的。
但笛卡爾在序言中就說,一切藝術,剛開始都是粗糙的,不過可以被逐步完善。哲學(科學)也一樣,只要有正確的方法,跟著它走,就會遇到真理的東西。
船隊抵達倫敦,宋欽依舊沉迷在書中。
克倫威爾還在跟荷蘭談判,又忙著讓議會移交大權。他暫時沒有露面,也沒准備什麼歡迎儀式,只派遣心腹官員來接待。
彌爾頓也沒來,他雙目失明了,有可能是被氣的。
在倫敦住了幾天,宋欽把《哲學原理》認真讀完。除了思考印證書中內容,他還順著笛卡爾的想法,思考事物的重力到底源於什麼。
雖然皇帝陛下,說重力來自萬有引力,可地球為什麼會產生萬有引力?
研墨,提筆。
宋欽奮筆疾書:“國人著書立說,皆欲高屋建瓴。今之欽天院,學者亦如此。先自圓其說,定宇宙天地之源,再進而研究天文物理。歐洲有大學問者,名喚笛卡爾,其作令吾茅塞頓開。研究學問,何必由大到小?由小致大可也……”
古代的學問家,其實都差不多。
先要確定宇宙觀、世界觀,比如程朱理學,就是無極化太極、太極分陰陽、陰陽氣理演化萬物。有了這個大框架,才能繼續做學問。
趙瀚下令組建的欽天院,同樣也有這種情況。科學家們對“氣理說”產生懷疑,又拿不出什麼新的宇宙觀,於是一邊搞具體研究,一邊爭吵宇宙的誕生和構成。
笛卡爾給了宋欽啟發,為啥一來就要確定這些?
世界觀確實可以有,宇宙是物質的,這就夠了。既然宇宙是物質的,就能慢慢探索研究。如何研究呢?認識論和方法論確定下來便可,一代一代不斷的去完善補充。
寫了一堆詞句,宋欽又寫出三個關鍵詞: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
確定這三個東西,中國科學的發展,才能真正走向系統化、理論化,而不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碰運氣。
僅憑宋欽的這一體悟,此次出使歐洲就已經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