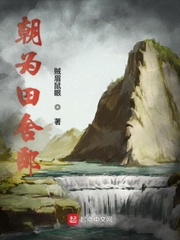哈薩克公主的名字叫“吉別可”,也可翻譯為“姬別克”、“姬別可”,意譯成漢語便是“絲綢”。
她還在襁褓當中的時候,前線傳來父親戰死的消息。接著多個部落叛亂,人人都自稱可汗,甚至有部落直接殺過來。
母親帶著她和三個哥哥,跟少數忠心部眾一起逃亡。
遷徙途中,一個哥哥病死,全家投靠了舅舅。直到大哥年滿十六歲,舅舅借予騎兵三百,又原有部眾數十騎。靠著三百多個騎兵,大哥一步步壯大,如今已擁有五千帳,控制著兩萬多牧民。
對於游牧民族而言,千帳便算大部落,五千帳絕對能虎踞一方。
吉別可穿著一身連衣褶裙,腰帶緊緊扎好,凸顯出略具規模的胸脯。她的十四歲生日,是在哈密渡過的,當時天氣很冷,哈密伯克留他們在城裡過冬。
雪化之後,繼續前行,到河南時已是夏天。
她頭上的皮裘圓帽,也換成了小花帽。帽子周圍有瑪瑙做裝飾,墜下來如同流蘇,她旅途無聊還編了許多小辮子。
吉別可有些想念母親和哥哥,也有些想念草原,更對未知的命運感到忐忑。
從嘉峪關到江蘇,她見識了許多漢人城市,也見識了漢人的鄉村。這些都跟草原完全不同,新奇而又神秘,她不知道漢地人口怎那麼多,多得就像草原上的牛羊一樣。
官船。
李聰踱步走到公主的臥艙,艙門口已經站著兩個哈薩克人。
李聰拱手致意,哈薩克侍衛屈身回禮,並且小心把艙門給打開。
吉別可起身行禮,用蹩腳的漢語問候道:“先生早。”
“公主請坐。”李聰用蒙古話說。
兩個哈薩克侍衛,就站在他們旁邊,防止出現什麼越軌行為。
吉別可翻開小學語文教科書,那是他們在甘肅買的,李聰負責教習公主學漢文。
“就快到南京了,我們今天學禮儀。”李聰說道。
吉別可說:“我們哈薩克人也講禮儀,如果路過一個氈房,看到裡面擺滿了食物,如果主人不在家,就算餓了好幾天,也不能動那些吃的。這是非常失禮的行為。如果家裡來了客人,把好吃的藏起來,只給客人吃普通食物,這也是非常失禮的。客人來到家中,應該先問他吃了沒有,然後為客人准備豐盛的美食。”
這咋都跟吃的有關?
李聰心裡吐槽一句,說道:“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漢家禮儀。以前禮儀非常繁瑣,陛下簡化了許多,但還是應當隨時注意。”
吉別可道:“先生請講。”
李聰說道:“欲學漢家禮儀,當先曉得……嗯,這個該怎麼翻譯才好呢?容我想想。”
李聰不懂得說哈薩克語,平時都用蒙古話交流。而吉別可的蒙古話,也只學了個半吊子。日常用語還行,高級詞彙根本沒法翻譯。
琢磨了好半天,李聰繼續說道:“這世界上有天和地,也有男人和女人。天和男人屬‘陽’,地和女人屬‘陰’,漢話就是這兩個發音。陛下說,陰陽一體,天地是平等的,男女也是平等的。但不論如何,男女也有區別,而且表現在禮儀方面。左為陽,右為陰,因此在禮節方面,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則……”
吉別可前幾個月才滿14歲,半大孩子,聽得似懂非懂。
李聰舉例說:“比如抱拳作揖,男人是左手抱住右拳,女人是右手抱住左拳。如果弄反了,就屬於凶禮,是非常不吉利的。”
吉別可抬起雙手,學著行女子抱拳禮。
李聰又說:“《禮記》有載,日常結發,男子結左,女子結右。雖然民間已經不管這些,但有講究的人家,結發還是會男左女右。宮裡似乎沒有這個要求,不過公主若是能做到,那也是非常有禮的體現。還有平時站立或坐下,方位也應該搞清楚……”
吉別可覺得漢家禮儀真是繁瑣,哪來任多規矩,別說做到了,連記都不好記。
李聰卻教得非常認真,因為他收了貴重禮物。吉別可的兄長,讓他好生教導公主,莫要被南京君臣看輕了。
一直學到中午靠岸吃飯,吉別可心累不已,亂七八糟的禮儀記得她頭疼。
午餐之後,教學再次開始。
吉別可想要偷懶,拿出自己的冬不拉,笑著說:“剛吃過飯,我給先生唱歌吧。”
“不敢。”李聰連忙避讓。
吉別可卻自顧自的彈唱起來,她唱的是哈薩克詩歌《百靈鳥》。大致內容為,一個勇敢聰明的獵人,為了聽到百靈鳥有益的哲理,答應放了已經到手的獵物。
可以理解成,有失才有得。也可以理解成,想要達成目標,必須學會放棄。
李聰側身站著,為了避嫌,不敢直視公主。雖然他聽不懂歌詞,但公主清脆的歌聲,是那麼讓人身心愉悅。
唱完《百靈鳥》,吉別可又唱《告別歌》。
這是哈薩克新娘即將遠嫁,獨自對著家中氈房門框所唱的歌曲,心中的不舍只能對著門框傾訴。
“門前是綠色的大草原,我家的門框,請不要放走我。我不哭泣怎能支撐,悲傷快要碾碎我的心。空中飛翔的是雲雀,它的絨毛松軟似錦。想自己就要離開這裡的草原,心裡是多麼悲傷。再見了,我家的門框,祝你平穩,我親愛的故鄉……”
唱著唱著,吉別可悄然流淚,她想起母親、兄長和那片草原。
李聰瞟到公主臉頰的淚水,猜測應該是想家了,於是默默退到艙門外。
岸邊不知哪家工廠,煙囪正排放著黑煙,這在鄉土中國顯得有些突兀。民間文人分成兩派,一派贊美蒸汽工廠,還說大煙囪帶來了盛世;另一派則暗諷批評,認為工廠破壞了山水田園。
工人們雖然辛苦,但還不算太離譜。
隨著用原始方法提煉石油,煤油和瀝青都已經誕生。但現在開采量還比較少,而且遠在四川、陝西等省,煤油價格到了江南比較貴,資本家可舍不得讓工人點著煤油燈上夜班。
煤氣也已經開始使用,明代工匠就知道如何制取焦煤,副產品煤氣的利用自然而然。
但煤氣燈非常危險,已經毒死幾十人。現在都不敢在屋裡用了,即便使用,也會提前開大窗,大家正在研究如何讓煤氣燈變得安全可靠。
李聰望著遠處的黑煙,突然感覺有些迷茫。
時代發展太快了,每年都有新東西出來,很多人因此感到無所適從。越是知識分子,這種感覺就越強烈,熟悉的環境漸漸陌生了。
特別是那套傳統觀念,越來越遭受質疑,程朱理學的宇宙觀,已經無法解釋新世界。
李聰靠在船舷上,自己打著拍子哼唱起來:“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中狀元,著紅袍,帽插宮花好啊好新鮮……”
《女駙馬》的故事,是趙皇帝講給楚王聽的,楚王請人編成小說連載於《楚王文藝》。
由於精彩離奇的情節,再加上本朝也出了個女進士,這部小說迅速受到各階層追捧。接著,又被改編為話本,以戲曲和說書的形式二次傳播。
李聰的老家在安慶,從小他就會唱采茶戲,也就是黃梅調的前身。
安慶在明代是漕糧彙集地之一,借此變得異常繁榮。如今雖然沒有漕運了,但繁榮的商業運輸,讓地理位置絕佳的安慶更加興盛。
商業繁榮,必然帶來娛樂繁榮。
起源自黃梅縣的采茶戲,在安慶被發揚光大。就像起源自昆山的昆曲,是在揚州被發揚光大一樣。
如今,幾大劇種爭奇鬥艷。
采茶戲在安慶異軍突起,已經正式命名為黃梅腔。
青陽腔繼續壯大,被徽商們帶到各地,這玩意兒是另一個時空的京劇前身。
昆腔(昆曲)繼續在江蘇和浙江流行。
而江西的弋陽腔,擁有一堆勛貴戲迷,已霸占南京戲曲界半壁江山,因此又被稱為“京腔”。
兩岸田野,隨著黃梅調消逝,新的景色映入眼簾。
一艘驛站的快船,運送著文書、刊物和信件,漸漸從官船後面追上來,繼而完成反超,風帆的影子漸行漸遠。
李聰突然開始追憶漢唐,那時候也是盛世,漢唐百姓該有怎樣的生活呢?
李聰不願生活在漢唐,因為他是個四眼仔,沒有眼鏡就丟了半條命。
又過兩日,終於抵達南京。
李聰帶著公主和哈薩克使者,在繁忙的南京碼頭登陸。
這種情況,每年都會發生,南京百姓早就習慣了。
但這次不同,因為吉別可生得美貌異常,周圍的百姓都不由自主看過來。
哈薩克少女,一般不戴蓋頭,更不會把臉遮得嚴嚴實實。
被這麼多人盯著,吉別可有些窘迫,她問李聰:“先生,這裡就是南京嗎?”
“這裡就是南京。”李聰點頭道。
吉別可心懷忐忑,她聽李聰說,皇帝是個大英雄。這雖然讓她芳心暗喜,卻又有些害怕,大英雄往往威嚴而不可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