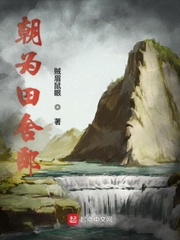第二天中午,梁嘯回到了長安,徑直來到淮南邸。
劉陵伏案而書,不時的停下來想一想。見梁嘯進來,她連忙將正在寫的竹簡捂住,紅著臉道:“不准看!”
梁嘯瞥了她一眼,故意陰著臉。“如果是准備嫁妝,那就沒必要了。”
“什麼?”劉陵臉色大變。“我父王不答應?”
梁嘯沉默了片刻,直到劉陵急得快哭了,他才哈哈大笑。“不是,是你父王要親自趕來操持,不用你答心了。不過,他入朝要天子下詔,所以遲一點。”
劉陵長出一口氣,撲了過來,亮出二指禪。“你敢耍我?”
梁嘯連忙求饒。“別!別!說正事,昨天在霸陵驛,我把嚴助給打了。”
劉陵不解。“你打他干什麼?堂堂列侯,動拳頭打人,也不怕人笑話。”她隨即又竊笑道:“莫非你還記恨他?”
“那當然。我一直記著呢,他把臉都湊上來了,我再不打都對不起他。”梁嘯聳聳肩,一臉義憤。“對了,王太後那邊怎麼說?這次能不能搞死他?”
劉陵收起笑容。“恐怕有些難。”
“為什麼,王太後就這麼願意往自己臉上糊屎?”
“你看你,說得這麼粗鄙。”劉陵伸手擰住梁嘯肋間軟肉,狠狠地扭了半圈。“你是故意氣我麼?”
“疼!疼!”梁嘯誇張地叫道。“我就是不明白,王太後至於這麼用心嗎?”
“不是王太後用心,是田蚡插了一腳。”劉陵松開手,白了梁嘯一眼。“田蚡派張湯去了江都國,應該是去收拾對嚴助、劉建不利的證據去了。”
“張湯?”梁嘯吃了一驚。張湯現在不出名,可是後來卻是大大的有名啊。而他賴以出名的一件大事就是淮南案。怎麼。現在要拿江都國開刀了?“那劉建、嚴助豈不是更悲摧了?”
“過猶不及。如果僅僅是劉建、嚴助,天子也許不會手軟。可是田蚡一插手,反倒難辦了。天子可以舍棄嚴助、朱買臣。更不會吝惜劉建,卻不會主動向丞相府低頭。這次北伐能夠取得勝利。你們這些將士固然有功,難道天子就沒有功?”
梁嘯倒吸一口涼氣。他明白了劉陵的意思。現在不是太皇太後還在世的時候,天子也不是剛剛登基的天子,他不會讓嚴助等人像王臧、趙綰一樣悲劇,因為那等於打他自己的臉。
嚴助、朱買臣等人因上書而得寵,本來就不符合選官慣例,天子因此承受了不少壓力。天子將他們當成對抗外朝的爪牙,打壓的主要目標就是丞相。田蚡想借此機會奪回相權,天子豈能讓他如願。
“這麼說,這次白忙活了?”梁嘯多少有些失望。費了這麼多周折,最後卻因為田蚡而付之東流。
“這倒不至於。”劉陵美眸流轉,笑道:“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讓天子知道擇人不當會帶來多大的麻煩,這便是收獲。”她推了梁嘯一下。“你千萬不要做出落井下石的蠢事,須知不爭之爭方是智者所為。”
梁嘯心領神會。“多謝夫人提醒。”
“去你的。”劉陵嗔道:“還沒成親呢,誰是你的夫人。”
“很快就是了。”梁嘯越想越得意,把自己淮南求親的經過說了一遍。當劉陵聽到梁嘯嚇唬淮南王說她有孕在身時。頓時惱了,拎起一個靠枕就撲了上去。
一場大戰瞬間爆發,直到氣喘吁吁。大汗淋漓才鳴金收兵。
——
田蚡得知嚴助、朱買臣歸來,又得知他們在城外霸陵驛與梁嘯發生衝突,被梁嘯打了一頓,不禁心花怒放。嚴助可不是什麼仁德君子,他吃了虧,肯定會反咬梁嘯一口。如果一來,張湯收集的證據就能用上了。
他耐心的等待著,等天子下詔切責梁嘯,好打著為梁嘯鳴不平的旗號出手。不料。天子一直沒有下詔,他似乎把這件事給忘了。一點反應也沒有。
田蚡按捺不住,只得主動出擊。呈上了嚴助、朱買臣收受劉建賄賂的證據。與此同時,他還讓蓋侯王信到天子面前哭訴劉建強奪父姬,又與其妹劉征臣和奸的惡行,請求天子下詔治劉建不孝、****之罪。
面對兩個舅舅的夾擊,天子勃然大怒,卻又無可奈何。劉建的罪行實在太大,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強奪父奸,和奸胞妹,但凡有點人性的人都干不出這樣的事。如果不予嚴懲,朝廷的顏面何存?
可是,嚴懲劉建,必然牽涉到嚴助、朱買臣。他非常清楚田蚡想干什麼,劉建不過是個幌子,嚴助、朱買臣也只是工具,權利才是他真正的目標。
天子遲遲沒有做出決策。
這時,淮南王劉安的奏疏到京,請求入朝,並主持女兒劉陵的婚禮。
天子答應了。與此同時,他召梁嘯入宮。不用說,這裡面肯定有梁嘯的影子,劉建強奪父姬的那個姬現在就是梁嘯的義妹,就住在梁嘯的家裡。因此,天子認定梁嘯才是背後的真正黑手。
梁嘯奉詔入宮,在承明殿見駕。
天子滿面春風,笑容可掬。“梁嘯,你用了什麼手段,居然讓淮南王答應了你?”
梁嘯一本正經的說道:“無他,唯一腔誠意爾。”
天子瞪了他一眼:“你少在我面前打馬虎眼。我那王叔是什麼人,我能不清楚?他學問淵博,文采風流,劉陵是他的掌上明珠,你卻是個粗鄙少文的武人,相去萬裡,他能輕易松口?快說,你究竟用了什麼辦法。”
“這個……”梁嘯強笑著作了一揖。“陛下若要臣說,得先赦臣之罪,臣方敢說。”
“你還有罪?”天子眼角顫了顫,歪歪嘴。“是什麼樣的罪?有些罪可赦,有些罪卻不能赦。”
“當然是妄言朝政之罪,和誆騙淮南王之罪。”
“呃……”天子松了一口氣的同時,又有些失望。“你的意思是說,你是騙淮南王的?”
“臣給他畫了一個餅。”梁嘯得意的笑了起來。“一個非常大的餅。”
天子好奇心大起。“你快說來聽聽,朕赦了你的罪便是。”
“唯!”梁嘯拱手,將自己獻圖之事說了一遍,只是沒有提淮南王有不臣之心。這種事根本不能說。
天子的注意點顯然與淮南王不同。他沉思片刻,將信將疑。“海外真有如此河山?”
“臣聽人說的,是不是真的有,誰也不知道。”
天子眼神閃動。“那……能派人去看看嗎?”
“當然可以。不過,風波萬裡,比沙漠草原還要凶險萬分,若無萬全准備,恐怕凶多吉少,九死一生。”
天子點點頭,沒有再追問。他明白了梁嘯的意思。這的確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大餅。“你憑什麼認定淮南王會被你這個大餅所吸引?”
“陛下,時至今日,朝廷削蕃之政已經勢在必行,臣能看得到,他豈能看不到?道家講柔弱自持,淮南士馬又不足與朝廷相抗,遠走海外是他唯一可行的選擇。其他諸王就算有這個想法,也沒有這個自信。淮南有門客三千,奇人異士不少,淮南王又是喜歡空談、不知實務的書生,他想必是以為自己有機會的。”
“那你覺得他有機會嗎?”
“若陛下支持,也許有一點可能。如果沒有陛下支持,恐怕……”梁嘯搖搖頭,沒有再說下去。
天子笑笑。“依你之見,朝廷應該支持他嗎?”
“臣鄙陋,不敢妄議。”梁嘯頓了片刻,又道:“不過,臣覺得江都王戰死沙場,求仁得仁,也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天子沒有再說。他明白梁嘯的意思。與其天天防著這些王有異心,不如讓他們去外面折騰。成了,朝廷可以將新得的土地封給他們,大漢的疆域進一步拓寬,又能將他們原來的封國收回,一舉兩得。敗了,那也是他們自己的損失,朝廷最多予以虛名的褒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損失。
比起削藩激起強烈反撲,這顯然是一個更溫和的辦法。
“這是‘避害’,那‘趨利’又如何?”
梁嘯反問道:“陛下,‘趨利’與‘避害’有區別嗎?”
天子愕然,隨即恍然大悟,不禁笑得打跌。沒錯,趨利就是避害,避害就是趨利,原本是一枚銅錢的兩面,豈能截然分開。遠走海外,對淮南王來說也是如此,豈是趨利,又是避害。
梁嘯一臉平靜,只是眼神中帶著幾分得意。天子一邊笑,一邊指著他。“你啊……”他想了半天,卻不知道怎麼說才好,最後說道:“淮南王叔做了一輩子的學問,研究了一輩子的權謀,最後卻被你給騙了。他若是知道真相,只怕會惱羞成怒。”
“呃……”梁嘯咂咂嘴。“他若是知道臣為陛下獻了推恩之策,恐怕就不止惱羞成怒了。”
天子心中一動,連連點頭。沒錯,梁嘯的推恩策一旦實施,不僅是淮南王,恐怕所有的王侯都會將梁嘯視作仇人。要說忠誠,還有誰比梁嘯忠誠?要說能力,還有誰比梁嘯更有能力?別的不說,推恩策這樣的妙計,嚴助等人就沒想到。
看來,梁嘯不僅能領兵征戰,還能內輔朝政,是一個真正的肱股之才。別看他讀的書少,可是處理起實際政務來,比嚴助強太多了。
剎那間,天子有了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