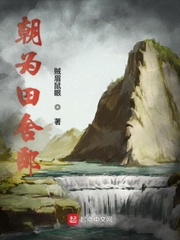“要上去看看風景嗎?”
秦御的聲音響起,顧卿晚收回目光,笑著道:“當然。”
她這還是第一次來,自然是要上去四處看看的。因樓梯都沒建好,陳詠硯幾個明顯也不是走正常渠道上去的,秦御抱著顧卿晚便直接拽著一根繩索,借力幾下,攀上了最高一層。
從方才陳詠硯幾個探頭的窗口跳入,秦御才將顧卿晚放了下來。
李東哲幾個退後了兩步,方便秦御進來,此刻見秦御穩穩落地,李東哲笑著拍手,滿臉崇慕,“二哥身手愈發精進了!”
“這不是廢話嘛,不過小爺看二哥今日格外英俊瀟灑,一定是因為嫂子的緣故!”
陳詠硯附和一句,兩人勾肩搭背的剛晃到秦御面前,秦御便挑唇道:“爺武功是精進不少,你們要不要再見識一下?”
兩人眼眸一亮,“好啊!”
“二哥今日好興致啊!”
於是下一秒,秦御拍了拍兩人的肩膀,接著手一劃,拎起兩人的衣領,便將兩個七尺男兒隔著窗口直接丟了出去!
“啊!”
“救命!”
兩聲尖叫傳來,接著噗通兩聲落水聲,這可是四樓……下頭雖然是清河,丟進水裡,對於沒練過跳水的人來說,那滋味。
更何況,現在天已經很涼了。
顧卿晚都替兩人哆嗦了一下,覺得其實陳詠硯和李東哲也挺無辜的,相信當時兩人買那畫時,她和秦御應該還不認識。
“有人落水了!”
“快救人啊!”外頭喧鬧了起來。
沈擇,“……”
郭棟,“……”
兩人實在鬧不明白這是發生了什麼,就算是陳詠硯和李東哲兩人馬屁拍的不好,也不至於這樣啊。聽說顧卿晚到大國寺住了一個月,難道是肝火太旺?
兩人同時選擇避秦御鋒芒,也不敢瞎求情,跑到了窗口朝下頭看。
下頭的清河裡,陳詠硯和李東哲兩個都已進從水裡冒出了頭來,落湯雞一樣正在水面上掙扎著往河岸游,這會子功夫河岸上已經聚集了幾層行人,對著兩人指指點點的。
顧卿晚也湊了過去,探頭瞧了眼,見兩人頭上的發冠受了衝擊,都不知掉落到了哪裡去,都撲了滿臉雜亂的頭發,狼狽萬分的樣子。
顧卿晚禁不住眨了眨眼,有些同情兩人,見兩人明顯都會游泳,應該不會出什麼危險,顧卿晚才將目光收了回來。
河邊,陳詠硯先從河裡爬了上來,渾身濕噠噠的,顧不上形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抹了把臉上的水。
好容易爬上了岸,撲在地上又咳了一陣,他才拽著陳詠硯,大聲喊道:“二哥為什麼生氣?”
陳詠硯,“啊?聽不見!”
李東哲,“我問你,二哥為什麼生氣?你做什麼了?”
陳詠硯一臉茫然,“你是不是知道二哥生氣的原因啊?快告訴我!”
兩人耳中轟鳴,根本聽不見彼此在說什麼,卻又急於從對方口中知道答案,簡直就像在演啞劇。
瞪大了眼等著滿足好奇心的圍觀路人,“……”
小廝給兩人披了衣裳,攙扶回樓裡。兩人收拾了一番,秦御已攜顧卿晚,和沈擇兩人一同下來。
顧卿晚進來時,就見陳詠硯兩人正裹著衣裳縮著椅子裡用帕子擤鼻涕,瞧見秦御進來,兩人同時露出委屈的表情來,眼睛紅紅的。
那樣子瞧著還挺喜感,顧卿晚沒忍住笑了一聲,想到這事兒也算是自己引起的,她咳了兩聲道:“我出去再四處瞧瞧,你們說話。”
秦御囑咐她別到危險的地方去,瞧著她緩步出去,這才看向了陳詠硯兩個。
見兩人縮著脖子明明很冤枉茫然,卻也不敢質問,心甘情願就受了他的懲罰和怒火,秦御心頭一軟,主動開口,道:“爺剛從顏如玉書肆過來,回頭把你們嫂子的畫像送到王府,這事兒便算過了。”
沈擇和郭棟聞言恍然大悟,旋即用一種近乎看傻子的目光略帶同情的看向陳詠硯和李東哲二人。
沈擇過去拍了拍陳詠硯的肩膀,“勇氣可嘉。”
郭棟拍了拍李東哲,道:“色心不小。”
李東哲卻哭喪著臉,縮著脖子看向秦御,哀聲道:“二哥,我冤枉,我是在顏如玉買過畫像,可我買的是……阿嚏,買的是周首輔家周清秋姑娘的畫像啊。我真沒買過嫂子的。”
秦御聞言雙眸一眯,“周清秋什麼東西?你敢覺得她比你嫂子好看?”
李東哲,“……”
“二哥息怒,我替二哥收拾他!”
沈擇說著,一巴掌重重拍上李東哲的後腦勺,打著那小子頭都偏了偏,抱著腦袋哭道:“我錯了,我錯了!”
陳詠硯吞了吞口水,非常乖覺的道:“回去我就送畫像,二哥息怒,我做錯了,我祝二哥和嫂子日日春宵,天長日久,恩愛不移,情深似海!”
沈擇幾人,“……”
這馬屁拍的還能再響亮點嗎?不過他們發現,秦御還真就吃這一套,臉上表情都柔和了不少。
旁邊李東哲目瞪口呆,他是真想找個地方哭一哭,憑什麼他沒收藏嫂子的畫像,被丟進水裡去還被削了一頓,陳詠硯個坑貨反倒還得了好臉色?這日子,真得查了黃歷出門了!
外頭顧卿晚和陳三老爺說了一會子話,指點了幾處營建的不大正確的地方,秦御便出來了。
天色已不早,顧卿晚和陳三爺道別後,便隨秦御登上馬車回禮親王府而去。
到了禮親王府門前,卻聽侍衛來報,說是宋寧火燒顏如玉書肆被帶到了京兆府去,顧卿晚略有些擔心看向秦御。
秦御卻擁著她神情如常的往二門走,道:“放心吧,那書肆私底下繪制貴女畫像,敗壞人家姑娘清名,宋寧會拿到證據的,京兆府就算不怕禮親王府,也是不敢一下子得罪那麼多府邸,不敢將宋寧如何。”
顧卿晚是覺得人家顏如玉也是正當開門做生意的,雖然有些猥褻吧,但這古代也沒有明文規定就不讓傳播淫穢啊。
宋寧就這麼燒了人家的書鋪說不過去,可現在想想卻是可笑,這可是階級社會,哪裡有什麼道理可講。
那顏如玉也確實太膽大了,那畫像都是被風流的男人們買了去,萬一被旁人看到,傳揚出去就會影響人家好好姑娘的清譽,一個弄不好害得人退婚,甚至毀了一生都有可能。
做的是見不得光的生意,也該受些懲罰,被燒了書鋪已經算是輕的了。
是日夜,顧卿晚被文晴伺候著弄干頭發,坐上床,秦御便迫不及待的將她拉進了懷裡去,從不知什麼地方摸出一本春宮圖來,道:“宋寧留了兩箱子書當證據,從裡頭選了兩本好的來,都不是那什麼真人的,咱們一起看看?”
秦御的聲音低啞帶著某種誘惑,熱熱的呼吸撫上她微涼的脖頸,一個勁兒的往耳廓裡鑽,許久不曾被碰觸的肌膚敏感的躥起一串串電流,引得心房似都顫了的顫。
顧卿晚勾了勾唇,斜睥著秦御,翹起唇角,道:“殿下燒了人家的書鋪,卻還拿人家的東西,不好吧。”
秦御一臉無辜,道:“爺這不都是看你喜歡嗎,不是卿卿說留一箱子書再燒嗎?爺看卿卿好像對這個很感興趣,來,來,咱們一起看。”
他說著興致勃勃的往顧卿晚的腰後墊了一個大引枕,拉著顧卿晚往上一靠,手臂穿過她的肩頭,環著她,將書翻了開來。
顧卿晚瞧去倒笑了,這本春宮圖,注重女子的描畫,上頭的男子就馬馬虎虎了。每張上的女人都姿態撩人,身子赤裸,那男子卻處處遮掩,掛著衣裳。
難為秦御,從哪兒選了這麼本春宮圖來。
想到今日在書鋪,她還沒看仔細就被秦御一掌擋住的那春宮圖,顧卿晚真是啼笑皆非。就沒見過比秦御更能吃醋的人,不過一副畫,又不是什麼旁的男人,倒不准她看!
她翻了兩頁,全是這般只注重女人的,頓覺無趣,似笑非笑的瞥了眼瞧的津津有味的秦御,抬手便一掌也蓋上了那畫中酥胸裸露的女人,道:“不讓我看,殿下自己倒看的起勁,這可不公平。”
她剛剛沐浴不久,臉頰上還沾染著緋紅的水意,一雙明眸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的模樣,簡直勾人心魄。
秦御心神一蕩,抽出被顧卿晚壓著的春宮圖便隨手丟了出去,翻身壓在她的身上,道:“不看就是,爺只看爺的卿卿。”
他說著便去挑她的衣衫,菲薄的唇帶著炙燙的溫度落下,大掌也沿著腰線一路往下撫,氣息有些微亂起來,“也只摸爺的卿卿。”
翌日,顧卿晚醒來,秦御果然已上朝去了,顧卿晚起來梳洗用了早膳便往秋霜院去拜見王妃。
這一個月,王妃允她在大國寺呆著,算是破了規矩的,昨日回府就該來致謝的,只是昨日回來時,天色已不早,禮親王又在秋爽院,故此便拖到了現在。
顧卿晚沒等片刻就被請進了花廳,王妃的態度一如既往的溫和,拉著顧卿晚的話,憐惜的說瘦了,還讓她一會捎些補品回雪景院去。
正說著話,丫鬟向雪進來,滿臉喜色的道:“王妃,王爺去京郊營辦事,路過仙岳樓,想起王妃愛吃那裡鐘師傅做的菜,便讓人將鐘師傅買了回來,說是這樣,以後王妃想什麼時候吃就能什麼時候吃了。”
禮親王妃聞言臉上也有笑意滑過,卻道:“王爺也真是胡鬧,鐘師傅是陳郡王妃專門請人從南方請來的,是仙岳樓的招牌,他怎麼能這麼干,這不是阻人財路嘛,來日可讓我怎麼好再上陳郡王府去?”
向雪笑著道:“這也是王爺對王妃的一番心意。”
禮親王妃點頭,道:“罷了,讓鐘師傅今日准備午膳,然後讓周管事將鐘師傅送回仙岳樓吧。”
向雪應了,福了福身才退了下去。
顧卿晚站在旁邊將這一幕看在眼中,見禮親王妃的氣色紅潤,眉目清亮而嫵媚,雖然臉上笑意略淡,但到底不像之前提起禮親王便神色冷淡的樣子,加上雖然要將鐘師傅送回去,卻也不算拒絕了禮親王的好意,還留鐘師傅做午膳。
顧卿晚便知道這一個月,看來禮親王和王妃的關系倒是緩和了不少。
顧卿晚再度肯定了烈女怕纏郎這條定律,心中暗敲警鐘。
她回到雪景院,就見院子裡王媽媽和江媽媽守著一個老大的箱子,如臨大敵的站著。
顧卿晚目光落在那箱子上,挑眉詢問的看向兩人。
王媽媽上前福了福身道:“這是方才宋侍衛帶著兩個侍衛抬進來的,說是二爺吩咐讓送過來,放下就走了。”
說著,她上前將一串鑰匙拿給顧卿晚。
顧卿晚莫名其妙的接過來,吩咐兩人將箱子抬進了屋,放在內室的八仙桌上。
待兩人退下,顧卿晚將鑰匙交給文晴,示意她打開看看,她自行取了一件常服繞進了淨房。
誰知道她衣裳還沒換好,就聽文晴一聲驚呼,“呀,這……姑娘快來看!”
文晴並非大驚小怪的人,顧卿晚被她嚇了一跳,匆匆走出淨房,就見文晴手中捧著個紫檀木大盒子,正瞪大眼對著裡頭發呆。
顧卿晚走過去瞧了眼,卻見裡頭放著一張張紙,上面蓋著印章還有手印的,她拿起一張來看,略擰了下眉頭,道:“這是房契?”
文晴點頭道:“都是房契和地契呢,姑娘看看,滿滿一匣子呢。”
顧卿晚翻了翻,果然下頭都是,瞧樣子足有五六十張之多。
顧卿晚隨意拿出一張就是一千兩的水田,再拿起一張是東城一座五進院落房契,令還有各地的店鋪房契額,田莊之類的也有不少。
顧卿晚蹙眉,很顯然這些都是秦御的私產,他送這兒來是什麼意思。
她看向木箱裡的其它東西,翻了翻,卻是有賬本,有私庫裡的東西清單,還有三匣子裝的都是銀票,甚至還有幾大串鑰匙。
顧卿晚不過大致看了兩眼,便將東西都丟了回去,蓋上箱子,吩咐文晴道:“鎖上,先叫兩個婆子進來搬開,等著二爺回來再說。”
文晴卻站著沒動,遲疑了一下,道:“姑娘,二爺願意讓姑娘幫忙掌管他的私產,這是二爺對姑娘的信賴和心意,姑娘便接管下來吧。何必……何必和二爺擰著,這事兒對姑娘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就算將來郡王妃進門,咱們不往外說,誰又能知道二爺的私產都在姑娘這裡呢。奴婢保證,奴婢絕不會將此事說出去的。”
顧卿晚聞言卻擺了擺手,走向梳妝台,坐下後,一面拆著頭上的釵環等物,一面道:“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便是掌管著又能如何,上頭的房契名還能變成我的不成?就算是能,天上掉餡餅也未必是好事兒,沒得被砸死。既然不是自己的東西,我費那個勁兒替旁人打理多傻啊?又不是吃飽了沒事兒干。我啊,還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來的可靠安心。”
文晴走過來給顧卿晚通著頭發,蹙眉道:“可是二爺拿給姑娘,那就是姑娘的啊。”
顧卿晚嘆息,不知道該怎麼讓她明白,觀念明顯不一樣,她抿了抿唇,最後只道:“想要拿到什麼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我知道,你是覺得有這些東西,我在這王府中腰杆就能硬起來,多些保障,將來就算郡王妃進了門,手中捏著這些東西,也能抗衡一二。可是這些銀錢之物,我自己就能掙來,我有那心思,還不如打理自己的生意呢。何必替他秦御忙活,有一日,他想要回去了,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再說了,拿人手軟,我可不想委屈自己。”
文晴蹙眉,實在有些聽不明白顧卿晚的話。
二爺將這些東西送過來,怎麼會有一日再要回去呢?再說了,姑娘如今人都是二爺的了,還能怎麼手軟?
顧卿晚瞧著鏡中的自己卻輕嘆了一聲,方才她不過大致瞧了下,箱子裡的東西就已經是難以估價了。
相信她就是憑借著現代學來的能耐,掙個兩輩子銀子,都不可能擁有那麼多的資產。秦御個貨,對經商根本就是一竅不通,人家卻有這麼多的私產,更別提將來還能從禮親王府分到不知多少。
想到自己就算累死,到了秦御這兒,相比之下都只能是個窮人,顧卿晚便滿心的不開心。
不過轉念她又想開了,沒事她和秦御比什麼,銀錢夠用就成了,要那麼多也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是日,秦御回來,顧卿晚問起箱子的事兒,秦御卻道:“爺又不打算娶妻,這些東西,你不管著誰來管?”
顧卿晚白他一眼,道:“你之前讓誰給你管著,那就還讓誰來管啊!”
秦御將她攬在懷裡,搖頭道:“爺不放心讓外人管著,萬一被偷著轉走些,爺也不知道啊。”
顧卿晚不覺呵的一聲笑了,道:“那你就不怕我偷著轉走些?”
秦御失笑,道:“你都是爺的,轉走能轉到哪兒去?轉來轉去,不還是爺的?何必費那個勁兒。”
顧卿晚,“……”
感情秦御是覺得她就是他窩裡的,有點啥,叼來叼去都還在他的窩裡啊。
秦御見顧卿晚抿唇不語,又道:“行了,你就當爺是給咱們未來孩子的,你這個當娘的先替他們保管著。爺去沐浴了,一會子還得去母妃那邊問安。”
他說著起身去了,顯然是打定了主意不肯將東西拿回去。顧卿晚瞧著他的背影,眸光微怔,旋即狠狠甩了甩頭。
到最後,顧卿晚也沒能將那一大箱子東西再送回秦御手中。又過了幾日,便臨近重陽節了,大秦的重陽節是四大祭祀節日之一。
還差幾日,王府中就開始在四處都擺上了菊花盆景,准備花糕等物,王妃也已經安排好重陽的行程,准備到時,帶著全府的女眷到萬歲山登山。
這日,秦御沐休,剛好浮雲堂那邊總算是完工了。一早用過膳,秦御便和顧卿晚一起出了雪景院,准備一起去看建好的浮雲堂。
不想還沒走到花園,便有丫鬟追了上來,稟道:“二爺,鎮海王妃帶著雲瑤郡主來給王妃送重陽糕和菊花酒,王妃讓二爺也過去秋爽院呢。”
顧卿晚聞言挑了挑眉,腳步頓住,瞧著秦御似笑非笑的勾起了唇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