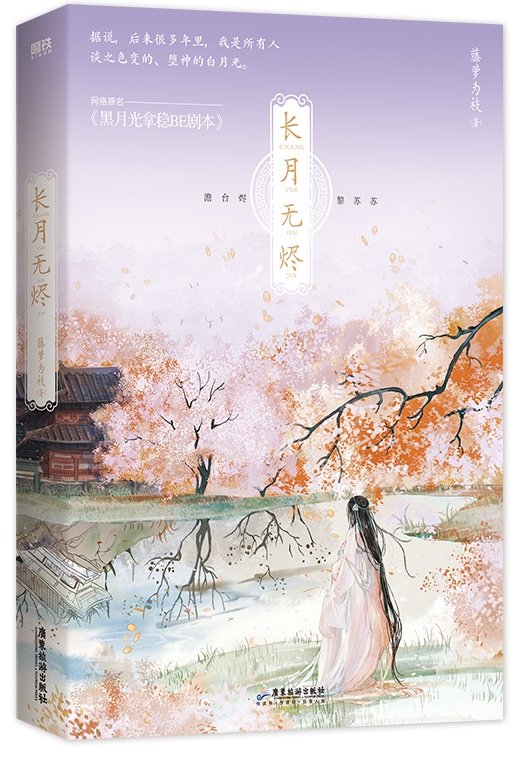房俊一愣:“腊月就已經不見長孫濬的蹤影?”
衛鷹回道:“的確如此,說這話的人乃是長孫家的一個大管事,深得長孫無忌信賴,既然他都不知長孫濬的蹤影,可見必是在長孫無忌的安排下去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房俊沉吟不語。
長孫家雖然威風不如當年,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單只“關隴領袖”這一個身份,便足以碾壓絕大多數的世家門閥。況且長孫無忌這人雖然陰險狠辣,卻絕對不傻,單憑著手中的權力便足以為家族謀取巨大的利益,又何必去做那些蠅營狗苟見不得人的勾當?
即便是有,也不至於讓長孫濬親自去辦。
自長孫衝流亡在外,長孫渙自戕身死,長孫無忌余子之中唯一能夠上得了台面的,也就只剩下長孫濬。
這樣一個極有可能會成為未來長孫家家主的兒子,長孫無忌豈能讓他沾染那些齷蹉實務,壞了名聲?
從腊月至今,已經將近四個月了,跑多遠的路辦什麼重要的事,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猜是猜不出來的,房俊叮囑道:“派人盯著各處城門,以及長安周邊的驛站,一旦發現長孫濬之蹤跡,立即追查其曾去往何處、見過何人、所為何事,不可懈怠。”
“喏!”
衛鷹急忙領命。
這年代但凡出了一趟遠門,都需要文書路引予以通關,尤其是進出關中,來回都要在四關之處報備,只要發現了長孫濬的蹤跡,然後即刻前往四關守備處調出檔案查看,便可知其曾去往何處、幾時歸來。
就算長孫家能夠消除四關守備處的文檔記錄,也可以根據其回京之時間,查出與其一同入關的商賈、旅客,然後一一查訪,查出長孫濬曾經到過何處,然後順藤摸瓜。
*****
令狐家書房內。
令狐德棻自從被武媚娘撓得滿臉桃花開之後,自覺顏面掃地、無顏見人,遂整日裡躲在府中深居簡出、不見外客。起先極其郁悶了一段時日,然後某一日忽然心有所感,覺得自己忙忙碌碌追逐名利,結果到頭來被一個女子撓了幾下,便輕易的將所有功名利祿似乎都給撓沒了,一輩子到頭來,還剩下什麼?
說到底,名利猶若浮雲,紅塵俗世之中隨骨肉而消融,百年之後唯余一抷黃土,生前之生命顯赫,半點不存。
作為一個文人,有什麼辦法能讓自己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即便死後亦會被人們記得,甚至可以余蔭子孫後代?
答案唯有一個,那便是著書立說!
人可以死,骨肉可以腐爛,但是寫下來的著作並不會隨著人死而消失,反而會越來越珍貴。
瞧瞧人家房玄齡,聲名煊赫了一輩子,臨老了致仕歸家,不也編撰了一本《字典》出來,傳諸後世、百代揚名?
自己雖然曾經參與了朝廷編纂的各類史書,卻從不曾有一部是由自己主導、署名,將來的影響力未免差了一些。
於是,他便向李二陛下懇請,由自己獨自編撰《周書》。
貞觀三年,李二陛下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負責撰北周史,卻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未能成書。
令狐德棻到底是當世大儒,被房俊的小妾撓了一頓聲名受損、威望全失,李二陛下也覺得蠻可憐,給老人家找點事情做也能消除郁悶,況且令狐德棻文華顯著,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水平一等一的高,便答允下來,並且命人將太極宮保留的有關於北周的文史典籍盡皆送去令狐家,讓令狐德棻閱讀借鑒。
令狐德棻便將自家的書房擴充了一番,成千上萬的竹簡堆滿了整個書房,整日裡一邊閱讀西魏史官柳虯所寫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沒有完成的周史,以及唐初為了修史而征集的家狀之類文書檔案,一邊伏案疾書,整個人都沉浸在著書立說的成就感當中。
令狐修己用一只手托著一個托盤,另一手先敲了敲門,然後徑自推開,走進書房。
書香墨香,煙塵浮動,頗有一種隔絕塵世、寧靜深遠之意。
進了書房,令狐修己反手將門掩好,以免風刮進來使得父親受了涼,上前繞過一大堆書簡,來到書案前。
令狐德棻正伏案疾書。
雪白的頭發只是簡單的用一根簪子固定,身上披著一件葛布袍子,胡須虯結,整個人形容憔悴、很是邋遢。
畢竟才是二月底,氣溫依舊很低,書房之內又不可生火,很是清冷,一雙握著毛筆奮筆疾書的手都凍得發紅。
令狐修己很是心疼老父,輕輕上前,低聲道:“孩兒給父親沏了一壺熱茶,備了幾塊點心,父親喝杯茶暖一暖身子再寫不遲。”
令狐德棻頭也不抬,只是隨意的應了一聲:“待吾寫完這一章不遲。”
令狐修己不敢再說,將托盤放在書案上,拿起托盤上的茶壺斟了一杯熱茶放在令狐德棻手邊,然後挽了挽袖子,便欲將書案前堆積如山的竹簡清理一下。
“放在那裡別動,否則過後吾找不到。”
……
令狐修己尷尬的摸了摸鼻子,站起身,覺得自己很沒用。
著書立說這種事乃是每一個讀書人都視為至高的榮譽,結果自己學識不足,非但沒法幫助父親,反而顯得有些多余……
便順手抄起一本書簡,坐在書案一側的椅子上,精心品讀起來。
良久,令狐德棻才放下手中毛筆,活動一下手腕,伸了一個懶腰,扭頭見到兒子正在一旁讀書讀得入神,便欣慰一笑,拿起書案上的茶水呷了一口,發現茶水已經涼掉,便倒入一旁的筆洗中,自去提起茶壺又倒了一杯,喝了一口發現仍有余溫,便一口喝掉。
令狐修己驚醒過來,放下書簡,道:“兒子再去給父親重新沏一壺熱茶來。”
起身去拿茶壺。
令狐德棻擺擺手,笑道:“喝茶只是一個心境,茶葉之好壞、水溫之高低,其實並無所謂。此間書如瀚海,為父徜徉其中,深得其樂,便是飲一瓢涼水亦是如飲甘霖,何須在意?”
說著,拈起一塊糕點放進口中咀嚼,又拿起帕子擦了擦手,這才問道:“怎地沒去衙門?”
令狐修己坐在一旁,苦笑道:“孩兒如今在吏部顏面盡喪、威信全失,幾乎成為整個衙門的笑話。早晨去點了個卯,見到並無太多事務便回來了,如今中樞各部都緊鑼密鼓,反倒是吏部無事可做,索性便偷一偷懶。”
被房俊那般折辱,如今他在吏部衙門的時候總是覺得有人在背後對自己指指點點,恣意嘲諷,使他無顏見人。
令狐德棻哈哈一笑,道:“你這娃子倒是在乎面子,當初為父被那武娘子撓了一臉血,一輩子的顏面都丟干淨了,差一點三尺白綾懸於梁上,來一個一了百了……然而後來方才醒悟,其實這人生一世,有太多重要的東西,唯獨臉面之事,連個屁都不算。”
令狐修己苦笑不已。
令狐德棻也知道這種事單憑別人勸說是沒用的,總歸要自己去想明白,這需要時間。
“跑到這裡來,該不是向為父哭訴你如何顏面無存沒臉見人吧?”
令狐德棻喝著茶水,慢悠悠問道。
令狐修己哭笑不得,嘆氣道:“父親何必這般刺激兒子?您這無異於傷口上撒鹽吶……不過兒子或許也能理解父親剛才話語的意思了,畢竟兒子的輩分在這裡,年紀也輕一些,被人打了臉倒也說得過去。就在早些時候,房俊那廝在陛下的御書房中,將趙國公給打了……”
“噗!”
令狐德棻一口茶水噴出,將面前的書稿打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