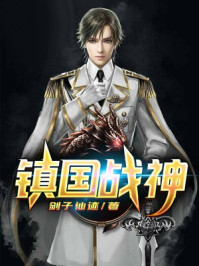除了回到基地的時候,烏蘭諾夫在任何情況下都戴著他的全覆蓋式頭盔,這幾乎是他的招牌形像。然而這頂頭盔並不是為了帥氣和拉風,也不完全是為了增強什麼防御力,它真正的作用是維持一個老兵的生命,以及掩蓋他的可怕真容。
郝仁看到一個樣貌駭人的男人正坐在桌子後面擺弄著某種設備,其臉龐幾乎無法被稱作人類。他大片的皮膚已經消失,露出的肌肉和骨骼中泛著金屬的銀光,一只眼球依靠某些電子線路連接著才不至於掉下來,原本是鼻子的地方只剩下一個帶有閥門的金屬管,從金屬管上接出來的一條軟管則正連接著桌子旁的某個氣瓶,而他的牙齒——那裡只有一排整齊的金屬。
烏蘭諾夫隱藏在頭盔下面的真容就仿佛一個血肉和鋼鐵混合鑄造起來的骷髏頭,詭異而可怖,饒是郝仁已經見識過各種各樣奇詭莫名的東西,在看到這景像的時候都忍不住被嚇了一跳。
“你這是……”他沒法掩飾自己的意外,索性直接問了出來,“怎麼弄的?”
“六十五年前,我在納米之海附近工作,觀察那些納米機群能不能用來開拓太空殖民地,”烏蘭諾夫臉上殘存的肌肉配合著柔性金屬抽動了一下,似乎是想對郝仁露出個微笑,但看上去幾乎比伊扎克斯的笑容還要可怕,“‘主宰’計算機宕機的時候我沒能跑出去,於是我被融化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烏蘭諾夫說著,微微撩開了自己的上衣,郝仁赫然看到衣服下面是一副透明的胸板,畸形的內髒和人造的器官在淡粉色的維生溶液中緩緩脈動著,看上去仿佛從恐怖片中走出來的生化人。
“我是那場災難為數不多的幸存者,而且可能也是活的最久的一個,”烏蘭諾夫指了指旁邊的床鋪,示意郝仁可以隨意落座,“啊,你大概對這些不感興趣——你找我有事?”
郝仁剛剛從烏蘭諾夫的真容和經歷所帶來的衝擊中平復下來,他一下子不知道該說點啥了,略有拘謹地在床上坐下之後才提起自己一開始的目的:“那什麼,我是想問一下……我有事要離開基地的話用跟誰彙報不?”
“離開基地?”烏蘭諾夫聲音中透著詢問,“你要去什麼地方?”
“在附近走走,起碼要知道自己未來的住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郝仁聳聳肩,“而且我也不能一直在這裡打擾你們吧——我不打算加入什麼組織,所以總有一天是要離開的。”
“我了解諾蘭的性格,她恐怕真不介意你一直在這裡住下去,因為她壓根不在乎這個,”烏蘭諾夫沙啞地說著,他的聲音不是從嘴裡發出,而是從喉嚨位置的一個共鳴管中傳出來的,他的聲帶已經在幾十年前變成納米機群的一部分,如今機器代替了他一半以上的生理功能,“但你這麼想也很正常。要出去的話我可以陪你,我暫時沒有任務,而這地方並不太平。”
“不不,不用麻煩你了,我怎麼著也是當過兵的,這點求生技能總該有,”郝仁趕緊擺擺手,“我就是來打聽一下離開基地還要辦什麼手續不——你們這畢竟是個軍事單位。”
烏蘭諾夫啞聲笑了起來:“啊哈……不用這麼嚴謹,灰狐狸沒這麼多規矩,因為諾蘭就是這裡唯一的規矩。只要你不找她的麻煩,就沒人會找你的麻煩。”
郝仁哦了一聲,烏蘭諾夫則順手從桌鬥裡抓出個什麼東西扔給郝仁:“拿上這個,即便你不入伙,灰狐狸的身份也能幫你擋下很多麻煩,在這地方只有背後有兵團的家伙才算是人,沒有身份的人都是工廠裡的‘爐渣’。”
郝仁接住飛過來的小金屬牌,這是個小巧的胸卡一樣的東西,上面用激光蝕刻著一個灰色的狐狸頭像,是灰狐狸佣兵團的標志。在混亂的黑街,人們被森嚴的等級制度支配著,來自零都市的干部和各個兵團的團長是一等人,而背靠兵團的士兵和掮客們被尊稱為“公民”,最下等的則是那些毫無身份,也沒有能力戰鬥的苦力——他們在那些冒著黑煙的工廠中從事繁重的、無法被納米機群代替的粗重活,飽受呼吸道疾病和各種污染的折磨,依靠粗劣的食物和納米機群制成的神經麻痹藥劑來維持短暫的生命,他們被稱作“爐渣”。
如果沒有一個兵團擔保,貿然來到黑街的訪客基本上過不了三天就會被扔進工廠中,能再完整出來的人只有鳳毛麟角。而即便能逃過這一劫,在黑街的貧民窟裡生存下去也不會比在工廠中做“爐渣”容易多少。
這就是文明崩塌之後的人類社會。
郝仁在網上查資料的時候也粗略瀏覽了有關黑街的情報,盡管資料簡陋,他還是大概了解了這個地方的規矩和環境,所以他知道這個小金屬牌其實應該是諾蘭授意給自己的禮物,而且對一個外來人而言,這是一份極其寶貴的意外饋贈。他妥善收起識別牌,好奇地看著烏蘭諾夫:“其他佣兵團也像你們一樣好打交道麼?”
“其他?”烏蘭諾夫呵呵笑了起來,聲音粗劣的仿佛一個破損的老風箱,“你要麼加入他們,要麼被他們扔到工廠裡去,大部分佣兵團同時也干著人販子的勾當。你應該慶幸自己遇到了諾蘭,她是這裡最強硬也最不講規矩的佣兵,她自己訂了規矩,那就是除她之外的所有人都是狗屁——所以只要她認可了一個人,那這個人在黑街基本上就安全了,所有兵團都會給幾分面子的。”
郝仁腦海中閃過了諾蘭的面容,那個有著灰色長發的、始終面無表情的佣兵女孩,她的一雙眼睛給郝仁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像,如今回憶起來,那眼睛中竟仿佛帶著一種無法言喻的疏離和滄桑,就如同一個看破凡塵又超然世界的超脫者在旁觀眾生生死一般。郝仁回憶起這個細節的時候忍不住感覺背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他堅信自己在諾蘭的眼神裡看到了某種理論上不屬於她的東西:“諾蘭……今年多大了?”
“十七歲,或者十八歲——不能再大,”烏蘭諾夫看著郝仁的眼睛說道,“別問更多了,我只知道這些。這地方的大軍閥都對諾蘭極端忌憚,他們畏懼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畏懼她的年紀。據說她十三歲的時候就只身刺殺了兩個佣兵團長,徒手,而且是用最殘酷的方式。或許你覺得自己今天從希頓手裡救了她一命,但實際上諾蘭估計有一百種以上的方法一個人干掉今天遇上的所有伏擊者。”
郝仁目瞪口呆:“她是超人麼?”
“有人說她其實是‘第三代進化者’,只是偽裝成了第一代,也有人說她其實是遠東聯盟覆滅之前制造出來的兵人,你可以去搜搜‘兵人計劃’,說的有模有樣的,”烏蘭諾夫搖搖頭,把調整好的呼吸過濾器裝回頭盔裡,摘掉自己鼻子上的呼吸管之後重新戴上了頭盔,“不過我建議你一個都不要信,也不要去跟諾蘭打聽這些。她平常脾氣很好,但偶爾發火的時候可沒人是她的對手……哈,重新戴上臉的感覺真好。”
烏蘭諾夫戴好頭盔,將上衣裡延伸出來的幾條線路連接在自己的面罩下面,又拉上外衣的合金拉鎖,重新變成一個全封閉的、仿佛摩托車騎手一樣的怪異士兵。他的頭盔為他提供呼吸輔助,並不斷釋放出電信號保證他那嚴重受損的大腦能持續運轉,而他上衣裡面套著的一件護甲則釋放另一套信號來抑制他體內那些殘存的納米機群,以防止那些致命的小東西徹底切斷他的脊椎。這套裝置再加上體內的人造器官共同組成了一副怪異畸形的軀體,它們已經維持了他六十五年的生命,而且只要他的大腦繼續存活,這幅軀體就能繼續生存下去,直到比任何一個人類活的更久。
他為什麼要堅持活到今天?
郝仁看著烏蘭諾夫並不魁梧的身體,知道這個面目全非的老兵肯定還有著更多故事,但他現在還沒到詢問清楚的時候,所以在感謝對方今天告訴自己這麼多事情之後,他離開了烏蘭諾夫的房間。(未完待續。)